庄子哲学中的时空观
作者: 蒋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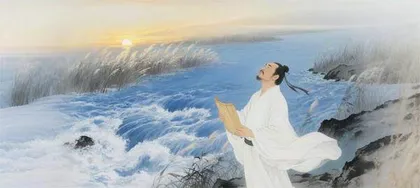
《论语·先进篇》篇有这样一段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在孔子的哲学中,显然以活着的人(生)做主要的重心;对于现实生活以外的问题,诸如“死亡”“鬼神”“宇宙”,则并不是他亟亟探求的对象。儒家的思想也一般侧重于伦理学的架构,严密地构造起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人间秩序,而对幽微冥渺的宇宙论部分较付阙如。
孔子对天道较少讨论,到了战国,在老子与庄子的哲学中得到了弥补。
《老子》首章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摆脱了现实世界人生的经验范围,直接刺探着宇宙生成的冥渺幽微。第二十五章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
这里似乎讨论的是宇宙中不可见的一种动力,绵绵不断,是一切可见的实体万物真正的创造者与推动者。这里所说的“有物”,是比天地更早存在的,它又似乎往复循环着,永无终结。
我们大约可以感觉到一种对无限时空的认识在春秋战国时期萌芽了。老子用“逝”、用“远”、用“返”来形容这不可见、不可捉摸的无限时空。而这“远”“逝”“返”逐渐深入中国人生命的神髓之中,在此后艺术与文学追求的过程里被奉为最高的理想。长卷绘画至北宋,从人物的内容转至山水,那山水的理想,那山水的空间,那卷轴的卷收与展放,便恰恰是老子的“远”“逝”“返”在中国视觉艺术上具体的实践罢。
老子对于这冥渺幽微的宇宙的兴趣,到了庄子更加强烈了,而庄子形象化的寓言,更确切地把抽象的时间与空间观念深植到中国人的生命态度中去,对此后中国艺术形式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庄子《逍遥游》基本上在谈时间与空间给予生命的限制。人所面临的永远不能克服的灾难其实是时间与空间。人不可避免地要被限制在一个时间与空间之中。人类一切的努力无非是要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但是这有时看来十分“伟大”的突破,只要一面对更为辽阔的无限时空,立刻会发现人类还桎梏在一个可怜的有限时空之间,不能自由。
庄子的哲学便是努力引领人们透过对时间与空间的勘破,进入生命绝对自由的境地,他称之为“逍遥”。
庄子《逍遥游》中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十岁为春,八十岁为秋。” “朝菌”是朝生暮死的虫,最为卑微短促的生命。因为朝生暮死,它一生的时间不足以了解“晦”“朔”的概念。这是庄子所说的“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蟪蛄”是寒蝉,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因为它的生命只存在一个季节,因此,对它而言,一年四季“春秋”的时间概念是它无法理解的。
庄子引领我们去认识自然界中生命短促的“朝菌”与“蟪蛄”,当我们正庆幸我们的生命是较长的,当我们正庆幸我们可以在一生中认识许多次“晦朔”与“春秋”之时,忽然,我们被狡猾的庄子一下子提升到一个完全不可了解的时间中去。那楚国南边大海中叫“冥灵”的神龟,一个春天竟是五百年,一个秋天又是五百年。庄子还不放松,又把我们升举到更渺茫的时间中去,远古洪荒中的大椿,竟然以八千年为一次春天,八千年为一次秋天。
庄子每一次让我们经历着生命从短促到漫长,从小到大迅速的变幻,无非是要我们对日常经验的时间与空间做一番脱胎换骨的猛醒罢! 在日常经验中,我们所认识的时间是“秒”“分”“时”“日”“月”“年”“世纪”;我们所认识的空间是“寸”“尺”“丈”“里”“亩”“顷”等等;我们发现,所有的时间都有一个开始,一个结束,所有的空间都有一个范围,一个边界。只要我们认识的时间有一个开始,一个结束,无论这时间是短是长,是“朝菌”或是“大椿”,其结局并没有太多的差别,因为都还在一种“有限”之中,空间也是一样,我们努力去征服更大的空间,如大鹏的起而飞,“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但是,这九万里相对于无垠无涯的宇宙,又算什么呢?
庄子在看来“谬悠荒唐”的比喻中彻底粉碎了我们依靠经验建立起来的知识世界,也同时提供了一个绝对无限的时空,鼓励我们从相对的“长短”“小大”中超拔出来,优游于绝对的无限之中。
其实,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能真正测知时间与空间。时间究竟有没有开始?开始以前是什么?时间会不会结束,结束以后又是什么?空间到了最大究竟有没有边缘,如果有边缘,这边缘之外又将是什么?
一连串的难题困扰着古今中外的哲学家,而一切艺术上的努力也无非是借着不同的方法试图摆脱有限的束缚以达于无限罢。
我们面对一件艺术品,是古雅典的巴特农神殿,或是苏轼的《寒食帖》,都同时在面对一个通过了无数时间劫毁的生命,于是,艺术品本身是暗含着在时间中挣扎的意义的。
庄子设定了时间与空间的无限,发现在这无限中生命才得以自由,也同时发现了在无限中,现实经验中的“小”“大”“长” “短”都可以因为心的自由而随意处置了。因此到了《齐物论》中,他便推出了这样的结论:
“天地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天。” 在最微细的“秋毫之末”看到了天下之大,也可以缩大山为小,在殇折的生命里看到了永恒,而彭祖的长寿倒是早夭的生命了。
在庄子的时空透视中隐藏着那不可言说的生命劫毁的悲哀,而庄子努力抑制着这伤痛,却指给我们可以一笑的豁达。那时空的逍遥自然是一个心的假象,但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齐物论》),此后的中国人也便借着这“无端崖之辞”(《天下篇》),开始了他们既悲辛寂寥又处处充满惊讶与喜悦的心路历程。长卷的收卷、展放,那真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体悟,而那可以独立出来的每一个小小的片断,即便是秋毫之末,也有它自足圆满的可能。每一个“朝菌”或“大椿”注定是那卷收与展放中“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一环,而生命是指向无限的。李商隐的《暮秋独游曲江》诗说“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这既悲辛寂寥又处处充满惊讶与喜悦的生的历程,成为中国艺术一贯的主题。似乎不只是长卷绘画,那演绎不完的章回小说,那绵延不断的组群性的建筑,那长达几百折的戏剧组合方式,都在显示着这庄子指引出的时空无限成为中国艺术追求的永恒远景。
宗白华在《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中说: “中国人不是向无边空间作无限制的追求,而是‘留得无边在’,低回之、玩味之,点化成了音乐。”
其实更确切说,也许中国人已勘透了时间与空间的无限,他不任性地要求时间与空间静止或固定。相反地,他与时间与空间一起优游。
(摘自文汇出版社《美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