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火
作者: 刘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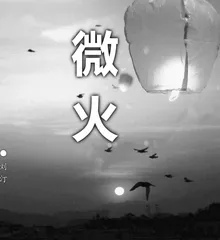
一
你知道,最难的是什么?
无力感?
她哭了。
什么?
那个孩子。
哭,为什么?
她从梦中醒过来,哭声像一首歌。
歌?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林里”
没听过,我只会唱“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我的
.....”
我把她轻轻推进去,按下按钮。我试过,没有任何呼吸,一点也没有。只是,她嘴角的痣忽然不见了。
推到车里?
十岁,一切都小小的,脸蛋是那种高原红,蓝碎花裙子,新的。我撩了一下她的刘海儿,露出光溜溜的额头。
好吧…十岁能记得很多事情。我就记得,我十岁的时候,玩爸爸的打火机,把窗帘点着了。
她不是很明白他在讲什么,大概就是一个女孩,他推她到什么地方还有些碎片,没有呼吸、歌声之类的。这令他几十年难以释怀。他伤害了她?还是,那个孩子是他的亲人?妹妹?女儿?
现在,这个正步人老年的男人,坐在她对面,进行他们的第三次诊疗。她见过许多心理疾病患者,知道他们有时陷入偏执的幻想,但是,与其他同行不同,她并不认为这是坏事。幻想是他们活着的根由,如果没有这个,他们就会陷人更深一层的混乱。那些真真假假、有逻辑或无逻辑的幻想,是他们给自己造的房子,是一个新的世界一对外人来说,那可能就是所谓平行宇宙。
前两次,他们的交谈流畅、顺利,像两个朋友聊天。她一直在寻找缝隙,好深入他自己都未曾发觉的那个世界,缝隙像高铁窗口闪过的树影,难以把握。正当她开始生出挫败感,露出一丝烦躁情绪,他却突然门户大开——
火,火。
微火,冷的火。
“春天在那小朋友眼睛里… ”
他开始发呆,眼睛盯着她。可她清楚,他并没有“看见”她。他陷人回忆或者另一重宇宙。她的工作使得她经常遇到这种情况。这时,她会默默观察,如果发现对方有狂躁的迹象,就摇动一个特制的铃唤醒他们;如果对方只是安静地沉浸于情绪中,像一块铁沉在湖底,她就继续观察一观察头的形状、某一小撮散乱的头发、睫毛长短、脸上的痣或斑块、上牙和下牙是否对齐…这种观察,让她对人这类生物有了新的认知:他们的灵魂大多数时刻都是沉睡的,一生中,醒过来的次数寥寥无几。
对,我十岁时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火灾。
微火在唱歌:“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不,火势不大,但绝不是微火。你用词挺讲究,一般人都说小火、中火、大火。
但是今天,他显得过于安静,仿佛大睁着眼睛睡着了。她明白,那股把他拉向水底的力量,既强大又柔和。他毫不挣扎,完全顺从。
现在,事情变得特别有趣一他在自己的回忆中,因为精神问题,那些场景和事件被重新经历,一切是正在进行的过去时。他已重复过千百万次。同时呢,她也由于他的讲述而沉潜其中。她像游泳教练,跟着他的身体游动,共享同一片水。大部分心理医生都坚信一句话—“讲述即治疗,所谓叙事疗法”,因此,他们总是引导患者变成一个讲故事的人。只有把无意识扯到意识层面,人才可能正视它并找到盛放它的容器。讲述像空气一样注入那些往事中,气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讲故事的人心怀忐忑,既期待又忧虑它爆掉。她的工作,就是帮助人们把铁杵磨成一根无比细的针,再鼓励他们把针刺进气球。
他的嘴巴在诉说,而他的全部感官,尤其是内心,从语言中分离,在同时重历这些记忆。她呢,则把自己的专业理性和共情能力调整到最佳的结合点,她游在比他更深的水下。
一个童话?火焰唱歌这个主意挺绝的。
二
我迷路了。
周围都是榛树,并不高大,但是漫山遍野,无边无际。
我向坡顶走去。我知道脚下就是她所在的那面山坡,但就是找不到她。村里老人说,这些树是十年前封山育林时栽的。栽树的时候,山坡上的坟并没有迁走。
我看到了几座坟,能看出,每年都有人来祭拜。不是她的,她父母早已去了遥远的黑龙江。村里人说,他们在那里种土豆和玉米,黑土种出的土豆特别面,玉米黏糯香甜。
我在山林中逡巡了一整天,从日出到太阳落山。后来,我清楚自己找不到她了,可并不想离开,只是不停地走。我在想,如果遇到一条毒蛇可太好了,我无比期待它牙齿里的毒液。那或许是我的药。
天渐渐黑下来,在山林中,天是大水漫过那样黑的。
唰——
窗帘缓缓拉上,黑夜像胶水一样把一切都粘在了一块儿。
天上没有月亮,我迷路了,分不清东南西北。双腿麻木,我躺在地上,青草用柔弱的身躯托住我。眼泪喷涌出来。很多年没有过这种感觉了,我想,她就在这片泥土之下,早已跟着流水、虫子和风遍布山林。我就这样跟她重新接触,十年前,是我亲手把她推进去的。为了露出额头,我还撩了一下她的刘海儿。她睫毛细长,嘴唇青紫。
我想,如果就这样睡去,再也不醒来,多么好。但我也知道,自己配不上这么好的结局。我有我的罪,罪是不能赎的,罪只能受。我必须承受完相等量一算上利息一的罪,才有资格去地狱。
这时,我听到了猫叫。瞄喵声绕过微风和树木,敲击着鼓膜。
不是幻觉,是一只黑色的猫,也可能是别的颜色,但在夜晚只显现为黑。它的瞳孔反射出两束光芒,像两把小扫帚。
我看懂了它的意思。
黑猫转过身,尾巴上翘、弯曲。我站起来,跟着它。我的脚不像它的那样充满弹性,它走得平稳丝滑,我则走得深深浅浅、跟跟跗。
它带我走出山林。
一刻钟一更久或者更短,我看见了远处村庄的灯火。就在微光抵达的一瞬间,黑猫消失了。我四处寻找,周围只剩下轻风摇动草木的影子。每个影子都像一只正在跳跃的猫。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xsyb20250601.pd原版全文
回头,大山在黑暗中融化。
我忽然惊醒,这只黑猫就是她。
从山上下来,我进村时,狗只叫了一声。
那不是对陌生人的警告式吠叫,而是类似于人对不置可否的事情的一声“哈”或“呵”。
事情发生一周后,我第一次来这个村子,找到她的父母。
我跪在两个悲伤过度的人面前,说这一切全是我的责任,他们可以报警,也可以报复。我全盘接受。
可是,他们沉默不语。
我不断诉说,到最后,那个父亲使劲摇头,只重复说一个字:不。
他们觉得我说得完全不对,是我受了刺激之后的胡思乱想,是我把梦中事当成了真实。
我走出院子时,那个母亲追出来,跟我讲,不要想了,一切都过去了。这是孩子的命,也是我们的命。
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们的另一个孩子,七八岁的男孩,正骑在杏树上够一颗刚刚透出红的杏子。
他摘下来,咬一口,魮牙咧嘴地喊,太酸了。
这是我第二次来,苦寻不到她的坟,却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何如此。那才是真正的悲痛啊。
三
那一次,回到城里,我养了一只猫,黑猫。因为这只猫,我认识了一个女孩。
它是一只流浪猫,在我居住地附近行动。它的前腿有点瘸,但不影响跑跳。我把它带回家里,没有做任何防疫措施。我甚至期待着它带点什么毛病,然后用利爪和牙齿抓伤、咬伤我,让我有机会比它更早死去。
它健康成长,野性并未彻底消失,喜欢从窗口跳出去流浪几天,找不到食物或天气骤变时,又会满身脏污地出现。它更大的特点是,从不叫。
我们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同居关系。
那一天,在它出走一周之后,我们在公园不期而遇。一个女孩正拿着猫粮逗它,它表现冷淡。我走上前,想凭借跟它的关系帮助女孩完成善举。猫冲我牙。我跟女孩说,这只猫很凶,你最好小心。她问我怎么知道。我说我是它的主人,它半流浪半居家。
女孩继续逗它,它却抓伤了女孩的手。其实,只有我知道,它这么做是为了告诫我。它试图显得更为独立,没有谁是谁的主人。但在法律上,我对它的喂养形成了主人和宠物的关系,我是它的监护人。我不得不带着女孩去医院打狂犬疫苗。
在电瓶车上,女孩诧异地问,你的猫没有定期做防疫吗?
我说,没有,所以你必须打针。
那你被它抓伤过吗?
我向后面伸出一只手,给她看,手臂上密布细小的伤痕,像一幅碎掉的拼图。
我没有打针。我说。
我以为她会问为什么,她问的却是,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女孩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在打针那天,她强迫我也打了狂犬疫苗。她的口吻不容置疑:你如果不打,我就不打。这样,我病了,仍然是你害的。她用她的命要挟我,我无法拒绝。然后是第二针、第三针,然后是逐渐熟悉和亲密,然后是同居,然后是结婚。
我的人生因此走上了我此前一直拒绝的那条道路,但这段路并不长。
矛盾出现在要不要生孩子这个问题上,她想做母亲,我选择不做父亲。我始终没办法跟她讲述那件事。后来,我买了一本书送给她,村上春树的《奇鸟行状录》。她本就是村上春树的书迷,但是我送她这本书,有另一重含义。我告诉她,村上春树因为父亲曾是侵华日军而选择不再繁衍后代。她冷笑说,也许,他只是为自己的不育症找个高尚的理由罢了。
他为什么要承担父辈的罪责呢?过了几秒钟,她又说。
不只是基因,有些事也是会遗传的。我说。
她看了我一会儿,没再说什么。这之后,我以为她理解了我的意思。她的确不再强烈要求我在她排卵期跟她做爱了,但我能感到,挫败让她身上的母性更加浓烈。半年后,我们坐到了民政局。离婚很顺利,之前她在家里拿出协议书的时候,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总算到这一天了。但是我的名字签得有些勉强。
我终于想明白你为什么不生孩子了。她说,所以,我也下定了分开的决心。
哦,那太好了。对不起,这的确是我的问题。
你应该勇敢一点,去追求你真正爱的人,而不是遵从世俗的观念,跟我搞形婚。
形婚?
不是吗?你是同性恋对吧,为了遮掩这一点才和我结婚。
我按捺住反驳的冲动,心里想,也许,这是个恰当的理由。特别是将来她跟别人提起这段婚姻时,这样的前夫形象能让她获得更多同情,甚至,她的魅力都会因此增加一点。
四
我恢复了独居生活。
也不算,那只猫仍然不时回来。它看我的眼神有些变化。
区别是,我已经形成习惯,定期带着它去驱虫、防疫,给它剪指甲,还有日常的喂养和铲猫砂。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获得了多年未有过的平静生活。游荡了几年之后,我有了工作,开网约车,一个新出现的行业。乘客对我仅有的评价是司机看着有点忧郁,不怎么说话。我既不像有些司机那样充满好奇心,从后视镜里打量每个乘客,跟他们聊天,问人家的个人信息;也没有另外一些司机那种对工作的热情。一定程度上,我像一个真人模拟的自动驾驶系统。乘客能听出我必要的对话里都没有语调。有些深夜,我行驶在北京的四环路上,看着车灯形成的河流向远方流淌,会幻想一种情形:这个世界的白天消失了,从此以后每时每刻都是夜晚。那样的话,我觉得自己的心能得到真正释放。这么多年,它一直在收缩。受此影响,我搜索了北极圈的极夜游,挪威和瑞典的某些小镇,还有俄罗斯的诺里尔斯克,一年有长达三个月的黑夜。但我同时了解到,这些地方温度很低,是抑郁症高发地区。犹豫中,我没有成行。我不是怕抑郁,而是不愿意跟更多的抑郁者待在一起。
现在想来,后来我还有过一段更长时间的“愉悦生活”。
就是那三年。这么说有点冒天下之大不违,但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在人人紧张的氛围里,我却仿佛被一种力量从水底托举到了水面。我不免想,人类已经走到了尽头,地球即将毁灭,我的那点事,已轻若鸿毛。我真是这么想的。那些日子,每天除了刷这类新闻,就是安静地回忆那件事。许多已经遗忘或者被时间模糊的细节重新鲜活起来,声音里的颤抖、火焰烧出的灼热气流、灰烬的特殊味道,比三十年前的那一天还要清晰。心脏的疼痛是永远不会减弱的,只是,这时的心痛会引发眼泪,不再像以前,只有歇斯底里的绝望。痛苦有时也会带有希望一只不过,我的希望通向同归于尽的毁灭。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xsyb20250601.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