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星之声
作者: 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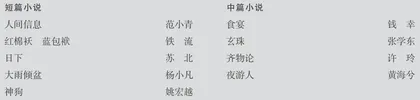
我已经忘了在什么场合听过那支乐队的歌,可能是在京郊的地下舞厅、室内滑冰场,或是公司团建的KTV包间,某个灯光昏暗的角落。总之你不会想象自己在一个穿长衫的地方听到他们的歌。当我和“北落师门"乐队主唱景辰初次见面时,我提到了这一点,并哼出了我记忆中的那首歌的旋律,“高潮部分大概是这样”。他沉思了一会儿,严肃地告诉我他们乐队不是叫北/落师门,而是北落/师门,换言之我断错了位置,而这一点比我有没有听过他们的歌更重要。
遇到北落师门乐队刚好是我人生处于最低谷时,此前我投稿参加音乐流媒体举办的歌词大赛,经过层层投票选拔意外贏得第三名,我写的歌词被谱成了曲,成为一位昔日天王复出新专辑的主打歌,这让我得以进入这个光鲜亮丽的圈子,也给了我一些虚假的希望。心态膨胀的我从旱涝保收的城商行岗位辞职,决心靠写词为生。起初,那家音乐流媒体的总监阿亮经常叫我喝酒,给我介绍了许多生意,我还可以从中挑选,但一般都是有一个初步概念先让试稿,而我交稿以后大多再无下文。蹉跎半年后,我惊觉一事无成,银行卡交易记录一片赤红。眼看下个季度房租还未有着落,我打电话问阿亮之前推掉的一家小众摇滚乐队是否可以谈谈看,阿亮说这都三个月了,人家都已经发完歌准备全国巡演了,还谈什么谈。
放下电话,我吃了半片安眠药,准备第二天爬起来去面试一家金融公司。药效可疑,半夜我被阿亮的来电惊醒,他让我赶紧上后海边一家酒吧找他,“有笔大生意要谈”。听到他语无伦次的声音,我以为是喝断片了,立马打车过去。临湖的酒吧大厅已经空空荡荡,阿亮正和两男一女猜拳,牵拉着脑袋,毫无生气,见我从天而降,拉起我的手介绍面前这群“怪咖”一这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灵魂音乐乐队。左起依次是主唱景辰、贝斯手安吉拉周和沙槌手叶隐。然后他向乐队成员介绍我,李云帆,我哥们儿,写词的,靠谱。这几个词浓缩了我的一生。
我不知道什么叫灵魂音乐,上网搜索了一下,了解到这种兼具东西方音乐特色且有神秘的野性的音乐类型。
后来我们五个人挤在网约车上,阿亮告诉我公司正在大力推原创音乐,他刚刚签下这支乐队,准备出一个电子乐专辑,想麻烦我写词。我说,不麻烦,你要几首我写几首,不,我还可以多写几个版本供你挑选。沉睡的景辰突然侧过脸看着我说,我们的歌都是自己作词谱曲,不是大厂工业线制作。阿亮拍了拍安吉拉周皮质短裙下的大腿说,这就是你们不红的原因,太端着,缺乏烟火气。
后来,我上网搜索浏览了北落师门乐队的所有公开报道。景辰是老北京,拆二代,从高中开始玩音乐,有点特立独行的意味,据说他当年为了梦想,卖掉家里房子发了几张专辑,但仍不温不火。十年前景辰参加一个卫视选秀节目,认识了小他好几岁的年轻歌手安吉拉周以及叶隐,组成一个乐队,慢慢积累了更为年轻的受众群体,算是在亚文化小圈子里小有名气一当然对此我几乎一无所知。
那个神奇的夜晚之后,我很快收到一份委托创作合同,要求我按时按要求交出十首歌词,但时间和要求那两栏是空白的,基于对阿亮的信任,我没有询问原因就签下名字。头期款很快就打了,解了我燃眉之急,而合作的事久久没有消息。
夏天快要过去之前,阿亮发微信叫我去公司的新录音棚,刚刚从北三环附近一栋文化园区写字楼搬到了通济河边的旧厂房。此处原先是大型国有药厂,甫改装完毕,偌大的厂棚里没有一根梁柱,吼一嗓子能听到持续不断的回音,就像无数面镜子立在面前,把人晃得晕头转向。此时,景辰正指挥一群工人搬运一些黑不溜秋的大玩意几进来,走近些我认清是台发电机。我问景辰,你们是要自主供电吗?我曾经听过一个段子,国家电网未合并前,水电柔,火电暖,风电空气感强,核电富有激情和能量。水电中,以葛洲坝的电音色最好。火电中以北仑电厂的电音质最好,因为烧的无烟煤的比例最高。景辰瞥了我一眼说,这个段子是真的,十五年前我玩音响时在天涯上写的体验帖,后来被无良媒体搬运过去当作笑料。
景辰带我去楼上的录音棚,进门要在玄关处脱鞋并穿上白大褂,据说是为了避免浮尘对收音设备造成干扰。安吉拉周和叶隐正在调试机器,叶隐抬头看了一下我说,这里的电压不稳,仔细听声音有杂质。我查了一下,这里的并网电组里包括附近的居民楼,傍晚六点钟正是用电高峰,影响了供电稳定性,我都能听出一股炒菜炝锅的味道。景辰说,这个很好解决,等今晚发电机开动起来就不会再有杂音了。
安吉拉周坐在椅子上,给我递了一只耳机,我接过来,以为是刚录下的小样,但很快发现不对,是一首熟悉的古典乐,这唤起了我多年前参加钢琴考级的经历,我小心翼翼地说,巴赫的《十二平均律》。安吉拉周说这是奥地利钢琴家古尔达演奏的,世界上最好的巴赫。之后,他们三人忙于测试新的机器,完全顾不上我,我站着听了半小时巴赫,感觉双腿酸疼,意志力涣散,往后一退,退到墙边的摆台上,忽然感觉腰部抵住了一个尖锐的锥体,回头一看竟是一具头骨。我吓了一跳,为了掩饰紧张,若无其事地说,这不是失踪已久的北京人头盖骨吧?景辰说,不,你仔细看,这头骨小巧很多,其实是尼安德特人的头骨,嘴部和下颌骨突出,我们称他老先生为史前音乐家。
等到三人终于停下来,躺在沙发上休息时,我忍不住问,你们的新歌demo(小样)可以让我听一下吗?按照之前签的合同,我要尽快提供歌词。景辰吃惊地看着我说,我们还没写歌呢,何来demo?我说,那或者我先写几首简单的给你们参考,等定下来主题再修改。景辰说,不着急,我们可以一起创作,以后你每天都来这里碰头吧,我们会慢慢把脑海中的旋律发展成曲子,你再做一些即兴创作,这才是灵魂音乐的核心。
临别时我收到一份新专辑的概念说明,一本印刷精美的小册子,名字叫《25光年外》,为什么是25光年?我没想明白,后来才渐渐知道北落师门b星正距离地球25光年。
根据新的指令,我每天早起坐公交车赶到录音棚,就跟过去上班一样,只不过是逆着浩浩荡荡进城上班的人流,不用再把身体折叠成柔术一般的姿势,也不用呼吸和鲱鱼罐头一般污浊的空气。那辆早班车上几乎看不到年轻人,大多是老北京人提着布袋子出城,也许是去买过冬的大白菜或走亲访友。我在公交车上自睹这座城市像一艘坚硬的破冰船驶入北方冰封的海面。日复一日,沿路树叶翻飞的绿色拱廊如退潮般隐去,入目变成一片萧瑟的白色,贴白色瓷砖的低矮民居仿佛浮冰盘踞在海面之上。我想象自己在做一些类似北极科考的工作,特别是到了录音棚,当我换上那身白大褂进人无尘工作室时,好像就要发现什么了不得的奥秘。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xsyb20250606.pd原版全文
新歌制作进展缓慢,我主要是在烟雾缭绕中,和主创交流新专辑的制作理念。通常是景辰在谈,他开着高保真音响,给我听了一些片段,雷声、雨声、融雪声、流水声,据说是他在环球旅行时搜集到的。其他人则沉默不语,或是低声发出疑问,这有什么用呢?好几次安吉拉周用钢琴弹出了几段还算抓耳的旋律,可以发展出一首完整的曲子,但很快被景辰否掉,他说他不想要这样庸俗的芭乐情歌。
有天我在楼下院子里散步,腐烂的落叶铺成一条地毯,坐在地毯边椅子上发呆的叶隐突然叫住我问,你觉得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小心翼翼地说,我们是在创作音乐吧。叶隐说,不,我们在陪他“聚淫”做梦,“异常”春梦。我愣在原地,过了会儿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陪一个巨婴做梦,一场春梦。
距离阿亮给出的期限还剩下一个月时,任务终于有了些许推进。景辰告诉我他想寻找一些被都市生活掩盖的日常声音,自然界不生产噪声,我们人类是最大的噪声制造者。他希望这张新专辑能尽量减少电子合成音乐,将日常声音作为其底色,就像25光年以外的北落师门星人来到地球时发现的那样。
什么是日常的声音?我租住的北京筒子楼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建的工厂集资房,板正的长方体,就像一面笔直插入大地的麻将牌。平时,我并不喜欢待在那个逼仄的房间里,所以每天下班后就在外面街头游荡,直到夜深人静时回到家。你以为已经很晚了,晚到所有人都已经进入了梦乡,但当你进入卫生间坐在马桶上,就会立刻发觉,暴露在外面的水管就像一个麦克风,把整座楼的声音都收集过来,并再次放大,但并非等比例进行的,多少会变形,最后变得跟梦境一样缥缈。有人在床头窃窃私语,有人在洗衣服,有人在看《新闻联播》,有人发出固定节奏的碰撞声。很多时候那些声音的来源并不确切,需要发挥想象力去补足缺失的画面。我按下抽水马桶的按钮,所有杂念都随之摇曳远去。
当我把这个秘密告诉景辰时,他脸上露出好奇的模样,他说他是在大栅栏四合院长大的,单门独院,从未有过混居的经验。我原以为景辰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提出要去我家体验一下。
我花了一下午把堆满杂物的房间收拾干净,晚上刚过十点钟,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景辰踩着尚未干透的木地板进来,脚尖躲着水渍就像在跳《天鹅湖》舞剧。我们寒暄了一会儿,景辰就说要去卫生间。我看到他打开了一只录音笔,然后把门紧闭。
过了会儿,景辰喊我拿卷纸给他。我掩着口鼻把纸从缝隙间塞过去,他却嚷道,进来啊,站门口干吗?我轻轻推开门,看到景辰正穿着裤子坐在马桶盖上,手里举着录音笔靠近那根水管,机器表面布满水珠。景辰把我递过去的纸铺开擦了擦机器,就像在擦拭自己延伸出去的器官。
我莫名其妙地问,有什么新发现吗?景辰说,你这里四面墙上都有管道,就像一台电视机里的不同频道,在这个角落可以听到谁家的客厅在放老电影。我顺着手指方向侧耳去听,从混沌中分辨节奏,恍然大悟道,搬过来好几年我竟从未注意过,他们好像正在看《泰坦尼克号》现在放到了沉船前小提琴乐队奏乐那段。景辰说,你再仔细听。我皱着眉凑得更近,水珠滴落在我额头上,有股直顶天灵盖的寒意。在接近眩晕的宁静中,我听到一阵持续的呻吟,伴随着撞击床头的声响,忽然明白了什么。景辰说,日常生活中有些声音是被遮蔽的,它们有着不同的层次,真正的音乐也应该是如此,但现在的流行乐太直白了,我希望大家能听到被遮蔽的情感。
景辰回去后半夜给我发了一段语音,是他用吉他弹的一段前奏,几个简单和弦回环往复组成的小调。我回了一个如痴如醉的表情,又觉得单薄,评价道,音乐中好像夹杂着蒸汽波的声音,这也许就是被你遮盖的情感,我想后现代的世界一切都在加速,对吗?过了好久,景辰回复道,我好像忘关加湿器了。
之后每天景辰都会发来更完善的片段,主歌、副歌、bridge(桥段)都渐渐成形。过了一周,乐队就录了一首完整的demo,请了公司合作制作出最厉害的编曲,把歌朝着流行音乐的方向改。
我则着手写词。根据新专辑的概念说明,这首歌应该讲述的是北落师门星文明先遣队来到地球后,对人类的上下班制度感到非常困惑,因为在他们的文明中劳动就是创造美的事物,比如制造雨雾、排列云朵、修饰山川河流的形状,而不是在逼仄的工位上浪费时间。
“世界多美好,我看你似乎不快乐。但愿今宵长考后,明天纵酒去捉狗。”
那一刹那,我觉得我写的就是我自己,至少是过去的自己。
在新专辑制作期间,公司安排北落师门乐队在三里屯一家LiveHouse(音乐展演空间)举行一场小型歌友会,提前看一下市场反应。作为乐队经纪人的阿亮邀请我参加,用了“拨冗出席”这样文约约的词,还给了头一排的票。这是我时隔多年再次听乐队现场表演,因为害怕晚高峰堵车,提前很长一段时间到达目的地,而场地尚未开放。
百无聊赖的我在太古坊附近逛街一一纯逛街,不曾进入哪家店里,那一路奢侈品牌的香水气味仿佛形成了看不见的结界。路过三联书店时瞥见一个熟悉的人影,我以为自己看错,又退回去看,确实非常相似。进人店里逡巡一番,在科技区发现景辰正站着看书,戴着鸭舌帽,也许是想隐藏自己,但对我来说那顶限量款的帽子实在太扎眼了。我轻轻咳嗽一声,景辰稍稍抬起头,眼珠四处游弋,终于发现了我,合上书页。看封面似乎是一部人类学著作。
景辰说,演出还有一段时间,所以他一个人出来溜达。我问,你的队友呢?景辰说,他们还在排练,但暂时不需要我,因为可以用录音代替。
我问,你对人类学感兴趣?景辰说,我是想看一下音乐的起源和人类进化之间的关系。我问,有什么研究心得吗?
我们走出书店,汇入外面的寒流。景辰带我走在迷宫般的胡同里,为躲避快速驶过的外卖电动车而不时碰到,皮衣摩擦的静电把我吓了一跳。我说,你在放电吗?他不以为意,高亢的声音击落几片摇摇欲坠的树叶,就像一种先进的超声波武器,音乐是人类进化的一条根本路径,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很早就通过研究指出,音乐构成了人类社会演化的前奏,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类物种的形成。音乐比语言产生更早,它刺激了大脑的不同分区,改善了人类的神经结构,同时赋予了早期人类强大的共情和社交能力,从而塑造了整个文明社会。《旧约·撒母耳记(上)》记载了扫罗王通过大卫弹奏七弦琴的神圣之音,赶走了身上附着的恶灵,获得了疗愈,这就是音乐引领人类前进的证明。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xsyb20250606.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