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机接口:人类与AI共处之道?
作者:张从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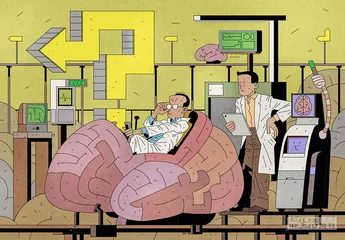 2025年7月底,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在上海举办。今年邀请来了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作开幕演讲,这是这位“AI教父”首次访华。他的演讲主旨落在了对AI(人工智能)潜在风险的担忧上。辛顿认为,我们正在创造比人类更聪明的AI,人类与AI现在的关系,就好像在家里养了一只虎崽子。人类对此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把它训练好,让它不攻击你;要么把它消灭掉。而实际上,我们已经没办法消灭AI了。这是辛顿这几年来一直在输出的观点。有人信,有人不信。
2025年7月底,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在上海举办。今年邀请来了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作开幕演讲,这是这位“AI教父”首次访华。他的演讲主旨落在了对AI(人工智能)潜在风险的担忧上。辛顿认为,我们正在创造比人类更聪明的AI,人类与AI现在的关系,就好像在家里养了一只虎崽子。人类对此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把它训练好,让它不攻击你;要么把它消灭掉。而实际上,我们已经没办法消灭AI了。这是辛顿这几年来一直在输出的观点。有人信,有人不信。不信的人会说,虎崽子长大后会吃人,但它终究变不成人。这就涉及智能本质的辩论了。辛顿一派认为,智能不是人类独有的,虽然现在的人工神经网络是通过模仿生物神经网络而来的,但它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径,已经获得了智能。比如说,正在使用大语言模型的你,从它的回答来看,你应该不会怀疑它没能理解你的问题。辛顿往前更进一步,他认为人工智能甚至已经有了意识。
意识是什么?现在没人能说得清,但多数人都认可,意识是一种基于人类主观体验的东西。辛顿攻击的正是主观体验这个东西,他设计了一些巧妙的思想实验,得出的结论是,主观体验不过是人类的幻觉,所以意识并非人类独有的东西。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变得越来越难解难分。这一次,我们决定回到争论的源头——大脑之中,去寻找新的解释。大脑是一切智能的源头和载体,也是因为对大脑之中神经元的研究,计算机科学家受到启发,发明了人工神经网络,于是有了今天的ChatGPT、DeepSeek这些大模型。
以大脑为研究对象的神经科学家们,是如何看待这些争论的呢?他们会为捍卫人的特殊性提供什么新的证据吗?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大部分神经科学家都能接受辛顿的一个观点——人工智能会超过人类智能。尽管对机器已经产生了意识这个结论,脑科学领域不太能接受,但他们不排除机器未来产生意识的可能性。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雄里近年来的态度就发生了大的转变。他告诉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深蓝战胜国际象棋冠军,到AlphaGo战胜围棋冠军李世石,每次有人请他来做评论,杨雄里都会说,人类智能是至高无上的,很难被机器超越。因为人脑进化了数百万年,其复杂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这几年,杨雄里已经修正自己的观点,他说,机器超越人类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而且这种可能性不小。
如果说人工智能现在或将来势必要超越人类智能,又如果机器有控制人类的倾向,我们依靠自己的大脑,还能找到新的抵抗手段吗?
埃隆·马斯克给出的方案是脑机接口技术,他在2016年创办的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现在已经把脑机接口产品植入到了至少九例受试者大脑内部。通过解读电极采集到的脑电信号,他们让瘫痪的患者可以借助机械臂拿东西、喝水、玩游戏,还能让失语患者用“意念”打字、“说话”。马斯克的终极目标,是让普通人也能植入脑机接口,实现人机融合,从而避免人类被机器控制。在中国,近年来也创办了一批脑机接口公司,借助国内丰富的临床资源,他们的临床试验开展得更快。今年,一些产品就有望拿到正式批文。
技术似乎已经跑到了科学前头。今天的神经科学家们承认,他们对人脑的了解还非常少,特别是对人的高级认知功能,比如语言、记忆、推理等了解更少。过去上百年来,科学家们在宏观、微观和介观层面都做出了惊人的努力,但在大脑的复杂程度面前,这些努力还相形见绌。进入21世纪后,各国政府又发起了各种版本、耗资巨大的脑科学计划,试图对大脑之谜来一场联合攻关。这些项目有的在争议中收场,有的虽然从中取得了很多进展,但与公众期望相去甚远。
不过,在各种新技术、新工具的涌现下,人类对大脑的研究模式如今正在发生一场变革。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大型科学设施陆续设立,它们利用规模化、自动化的成像、测序等技术,正在给脑科学研究源源不断地生产数据。很多科学家寄希望于这些数据的累积,能给我们认识大脑的旅程带来惊喜。我们深入到这些设施中,看到了我们大脑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