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1圆桌派:“不想长大”是“病”吗

重养自己一遍:让回溯成为成长的阶梯
林悦小时候生活在一个普通县城,睡在一张不到一米宽的小床上,枕着一个荞麦皮枕头,床一边靠着灰扑扑的墙,一边用旧床头挡着,当时她最渴望拥有的是一张公主床,像外国电影里的那样,上面铺着松软的被子,摆满大大小小的枕头,周围挂着精致的纱幔。她还喜欢芭蕾裙,然而县城里并没有专业的芭蕾培训机构,父母也没有精力陪她往返省城学习跳舞。公主床和芭蕾裙是她童年时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后来渐渐成为她内心深处的执念。
现在的自己,成为儿时梦想中的“公主”
如今的林悦,在大城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当她有能力满足自己的需求时,那些童年时期的渴望像潮水般涌来,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弥补曾经的遗憾。
她首先给自己买了一张公主床,配上粉色的床品、纱幔,还在床上摆了七八个松软的枕头。每天起床,不管多晚,她都要把床恢复到睡前的模样,就像儿时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平铺的被子,下垂的被角,以及翻折过来的被头。每当她站在床前,轻轻抚摸柔软的床品时,就仿佛回到了童年梦境,那些精美的床上用品,每一套都代表着她对童年美好生活的向往。
她还报名参加了一个成人芭蕾舞班,每周都会抽出时间去上课。虽然身体已经不再像小时候那么柔软,但她依然努力地练习每一个动作。当她穿上芭蕾舞鞋,在镜子前旋转时,一种多年未有的满足感油然而生,恍惚间,她仿佛看见童年那个渴望跳舞的自己,在平行时空里已然成为出色的舞者。
对林悦这样的年轻人来说,“重新养自己”恰是以成人之姿弥补童年缺憾。曾经被父母忽视的心愿、未竟的期待,如今由自己的双手去弥补,这不仅是自我疗愈的良药,也是打破“社会时钟”的偏见、实现自我成长的一种绝佳方式。
“社会时钟”是心理学上的概念,将人生各阶段固化为标准化模板,求学、婚育、事业皆需遵循既定时序,也就是老一辈人常说的“什么年龄干什么事情”。年轻人“重过童年”,显然是打破了社会时钟,以个性化的节律,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情感、物质匮乏,寻找一条让内心重新丰盈与平静的可靠路径。
不想长大,是进行自我疗愈的有效方式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说,人的一生总是在弥补童年的缺失。研究表明,童年时期的物质与精神匮乏会在潜意识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影响成年后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状态,有人甚至会频频想起童年时对一个玩具求而不得的伤心。网络上流行的“把童年的自己重新养一遍”,其实是通过自我疗愈,实现内心真正的成长。补偿性消费,有时也能弥补童年的遗憾。
与童年的自己和解,不能仅靠补偿消费
随着时间的推移,林悦逐渐发现,这些报复性消费并没有真正让她感到满足。公主床虽然精美,但每晚躺在上面,她依然会感到空虚;芭蕾舞课上的努力让她实现了梦想,但满足感却只是短暂的,她还会有层出不穷的新渴望。她不禁反思:童年的需求,真的能满足现在的自己吗?
心理学家阿德勒的“自卑与补偿”理论指出,童年时期产生的自卑感,往往会在成年后寻求补偿,但这种补偿行为往往只能暂时缓解内心的焦虑,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林悦开始意识到,她真正想要的并不是那些华丽丽的表象东西,而是童年时缺失的情感需求。小时候的她渴望被关注、被爱,渴望得到父母的理解和支持,但那时候父母忙于养家糊口,孤单的她只能从电视上感受“理想的亲子生活”,而公主床、芭蕾裙是影视剧中“幸福小女孩”的标志。
于是她停止了消费补偿的行为,转而开始接触心理学,通过与自己的内心对话,了解自己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理解和接纳童年时期的自己,学会用更加成熟的方式去面对情感需求。在心理咨询师的建议下,林悦与父母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主动与他们说起自己童年时期的感受和遗憾,她理解父母当时的难处,但也希望他们能明白自己的缺憾与内心需求。通过沟通,亲子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亲密,她也感受到了父母的爱和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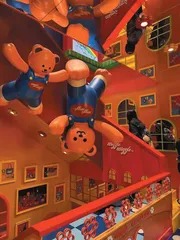
总有人质疑,在二三十岁“重新养自己”是否太幼稚、太晚,林悦觉得,在重养自己的过程中,她学会了用更加积极的方式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也更加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她不再被童年的遗憾所困扰,而是以更加成熟和自信的姿态面对生活。
重养自己,不是成人的儿童化,而是满足时光里那个小小的自己的心愿,有人重养身体、重养爱好,也有人重养感受、重养心力。通过这种“自我抚育”,年轻人不再把失败或者挫折归咎于原生家庭或成长环境,而是勇敢地站出来,用自己的力量疗愈自己,实现真正的成长,仿佛捡起了时光中的碎片,拼成一个在当下更完整、更真实、更自信的自己。
雏鸟青年自救指南:戒断依赖,独立学飞
当熬夜赶出来的方案被客户否决,云宝挨完上司的责骂,选择躲进楼梯间给妈妈打视频电话。听到妈妈的声音,她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电话那头的安慰如往常一样温柔:“乖宝别哭了,妈妈给你煲最爱的排骨汤喝。”挂断电话,她看见手机屏幕中的自己,突然感到一阵空虚。妈妈的安慰像一剂用了二十年的止疼药,配方没换,止疼效果却越来越弱,无法再医治她人生中不断出现的新“伤口”,哭诉之后,她还是要回到办公室处理现实问题。


不想长大,是习惯性回避问题和对父母的过度心理依赖
许多人成年后仍保持着对父母过度的心理依赖,在职场、社交、情感等社会生活中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找父母寻求解决,潜意识回避成年世界的复杂和冲突,害怕承担责任。
或许戒断对父母的习惯性心理依赖,迎接迟到的成年,是“雏鸟青年”成长的第一课。
“妈妈永远是我求助的第一人”
25岁这年,云宝发现,面对职场、社交、情感等人生课题,她从小到大依靠的“妈妈牌”安全感正在失效。
在云宝的记忆中,从衣食住行到手工作业、竞选班干部填资料、高中分科选择、高考填报志愿,全都是妈妈一手包揽,她只需要专注于学习本身。
上大学后,遇到任何问题她都习惯性地给妈妈打电话,比如和舍友发生生活方式的冲突、收到男生的表白、宿舍空调坏了,等等。
后来云宝离开大学校园,进入职场。第一次在工作的城市独立租房,在答题世界中游刃有余的云宝发现生活竟如此陌生,租房合同怎么签、门锁找谁换、去哪儿缴水电费、浴室花洒水很小怎么解决、燃气阀门突然回吸是什么原因……生活难题接踵而来,让她手足无措,只好呼叫妈妈从异地赶来陪她生活三个月,把生活理顺。
现在回想起来,云宝觉得自己一直有一种逃避心理。“从小看着妈妈替我操办一切,其实也会觉得,大人的世界好难好累,潜意识里害怕做大人,担心自己做不到,也做不好。”
这两年,每当云宝向母亲哭诉困境后,总会涌起一阵难以名状的焦虑。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父母的经验已难以匹配职场新生态,情绪价值当然重要,但除此之外,云宝更需要解决具体问题的智慧和方法,以及直面复杂世界的勇气。而长久的心理依赖已形成巨大惯性,她总是想再在妈妈背后躲一躲、拖一拖,她必须下定决心,走出“妈妈牌”安全屋,开始学习独自面对人生的风雨。
戒断过度依赖,成长虽迟但必到

在网络上,许多年轻人都在感慨:父母的30 岁,成家立业、建设祖国、养育子女;我的30 岁,旅行、买手办……他们一边在社会规则中怀疑自己过于孩子气,是不是应该像社会期待的那样组建家庭、承担更多责任,一边又在内心深处告诉自己“我还没有准备好进入长大的世界”,在矛盾的心理中,带着迷茫在人生路上徘徊。
近年来,“成年期的消逝”成了全球学者和文化评论家热议的话题。客观来看,一代人陷入延迟长大的困局,是诸多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均寿命延长,教育年限持续增加,导致经济独立、结婚生子等传统的成年标志显著延迟,这并不是个体选择问题,而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社会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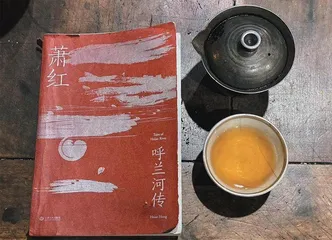
在应试教育体系下,像云宝这样习惯于“听话”的群体尤其典型,他们从小到大都活在“好学生”保护罩里,一旦离开象牙塔,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成年切换,瞬间具备与复杂、混乱的现实世界打交道的能力。有心理咨询师发现,越来越多年轻来访者呈现出“温室综合征”——熟稔星巴克隐藏菜单,却搞不定社保转移;能策划百万流量的线上活动,面对办公室同事关系却手足无措。
在25岁的尾巴,云宝终于开始迎接迟到的生长痛。她给自己规定:每当想要打电话问妈妈怎么办时,先暂缓30 分钟。在这30 分钟里,问自己这件事是否有第二个解决办法,如果有,就自己学着来。
就这样,她磕磕绊绊地照着B 站视频学习换灯泡,跟着小红书上的“女生独立计划”学习如何提取公积金、如何结算个人所得税、如何报销医保,她的微信通讯录里,不再只有娃圈好友,还加了物业客服、水电工、开锁匠、洗衣店老板等。她还创建了一个“长大文档”,记录自己第一次独自完成一件事后的感想,她说:“学会拒绝同事甩锅、学会更合理地利用团队合作资源,过程虽然很痛苦,但是,当我踏出第一步后,我发现,原来人生不是只有躲藏和忍耐,原来我也可以主动去改变、去拓展,好像天地真的变宽了。”
在互联网上,更多“云宝们”的蜕变故事让我们看到年轻一代新型的成长范式,成熟不是不再害怕,而是带着恐惧继续前行。当更多“大号宝宝”学会在裂缝中打捞勇气,或许我们能够见证:那些曾被母爱包裹的脆弱,在现实的土壤里开出意想不到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