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戏剧舞台的有限与无限
作者: 展世邦
千年来,戏剧观众也在看戏的过程里被规训,他们成长为挑剔的行家,而不再是暴怒中拔枪射舞台的大老粗。观众们在对“本该如此”或“从来如此”的舞台程式里产生了觉醒式的主动参与意识,看戏者与创作者间的博弈从未休止。
现代戏剧稀释了舞台上的首要造型——演员,创作者不再单纯依靠角色吸引观众、营造幻觉,他们培养观众的怀疑精神,他们与现代观众在颠覆和消解中成为默契的共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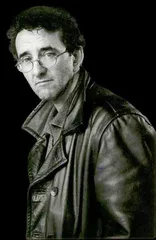
文学与电影间的诠释空间
当一部畅销小说已被好莱坞搬上银幕,并成为里程碑式的奇幻电影后,戏剧还能做什么?2002年,小说《少年Pi的奇幻漂流》获得布克奖,随即成为备受电影界关注的改编目标。2012年,《少年Pi的奇幻漂流》成为全球的话题电影,观众惊叹银幕上的视听奇观,也绞尽脑汁探寻故事之中隐藏的深意。2022年,舞台剧《少年Pi的奇幻漂流》获奥利弗奖(英国舞台最高奖)五项大奖。2023年,该剧又获得托尼奖的最佳声音、灯光与布景设计奖。戏剧在小说的无限想象空间与电影的视听幻觉间,给出第三种表达可能,并赢得了挑剔观众的认可。
剧中的动物是故事的第二主角,指涉着Pi的精神世界,受限于剧场内的空间和技术,如何准确地向观众传达动物们的情绪?创作者们选用了最为质朴的表演形式——木偶。该剧的木偶设计师芬恩·考德威尔与尼克·巴恩斯(合作设计过《战马》《天使在美国》等舞台剧),用等比例的木偶表现老虎、狒狒、斑马、鬣狗……大型动物由两到三位木偶师协同表演,配合演绎出动物的一举一动。它们的动势、步态都充满戏剧张力。这一舞台设计,模糊了木偶的“假”,而强化了其情态的“真”,就此掌控了观众的临场感。
“Pi”的两重境遇,一重在船上,另一重在病房里。升降舞台随时可变出船的轮廓,灯光填充了船四周的波澜海浪,让Pi讲述故事的自由得以延展。当升降舞台降回到与周围齐平,回到病房,Pi又成了被质疑的对象,也是被盘问的人。
舞台剧对小说和电影做“减法”,让观众找回了看电影时被视觉奇观夺走的注意力,去思考戏剧背后的问题——为什么Pi会讲出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或者,为什么他能讲出如此迥异的两个故事?
戏剧作者不惜用四分之一的篇幅铺垫了Pi的“信仰困境”。在影片里,我们跟着他去过各式的神庙。而在戏剧里,一个“市集”就完成了全部表达。在嘈杂的市集,他被人们团团围住,每个成年人都代表各自的宗教符号,他们像商贩一样叫卖着信仰,都想把Pi拉到自己“门下”。而“市集”同样也暗示了Pi的实用主义,他并不真正皈依于任何一种信仰,而是拿来“为我所用”,这也正是Pi历经残酷的生存挑战还能活下来的原因。
戏剧中呈现最多的,是印度建筑的穹隆顶造型和船头的弧线造型,二者合为一体,从平面的屋顶到立体的船头,从二维到三维的变调,消除了观众在视觉上的疲乏。穹隆顶造型和船头的造型,也把戏剧主旨蕴含其中——信仰和生存的对立与共处。同理,病床与救生筏的一体,也是主观叙事和客观质疑的博弈,病床与救生筏又在视觉上把Pi放到被审判的位置。
在船上存活的动物,尤其是与Pi相伴相争到最后一刻的猛虎,都由木偶师操纵。我们在木偶的动势间隙,能清楚看到木偶师的存在。木偶——木偶师、野兽——人,这直接指涉了少年与猛虎的一体两面——老虎既是Pi又不是Pi,它的兽性本能解决了少年的生存危机,但它的兽行却令少年无法正视——他的人性无法令他的兽性自洽。当抵达大陆,“文明世界的人”来救援的那一刻,猛虎遁入丛林,Pi回归到理性秩序中,观众也将目送操纵猛虎的木偶师(人)离场。
舞台剧版本绕开先天缺陷——缺乏炫目的视听奇观,直接表达包容与理解。也正因为穹隆顶—船头一体两面的造型,把戏剧性的冲突两极(信仰与生存)完美地统摄在一个小舞台之上。
如果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以准确洗练的形式,选择性地阐释了文学原著,那么《2666》就是以最“反文学”的方式把原著硬生生地推到观众面前。
2017年盛夏,“去天津看一场十二小时的话剧”——成为当年文艺青年标榜品味的一桩事件。舞台剧《2666》改编自近年最炙手可热的智利作家波拉尼奥的同名小说。作为波拉尼奥的遗作,该书出版后被西方主流媒体奉为“年度最佳小说”,全篇共有五个独立成章的故事,彼此呼应,由隐秘的线索串联,时间跨度从二战前直到当下,空间以墨西哥为轴,辐射西欧、美国和南美洲。2016年,法国一家剧团把《2666》搬上舞台,在阿维尼翁戏剧节首演,成为当年的焦点剧目。这家剧团在2017年受邀来华,参加“林兆华戏剧邀请展”,长达十二小时的演出时长,让其早在上演前就已成为话题。
说它“反文学”,是因为演员在舞台上的演出,几乎原文引述小说原著,演员经常跳出角色去担任旁白,把作者在小说中的叙述直接面对台下观众念出来——这一形式,被很多评论家认为是“最具文学性的戏剧”,或是“最接近原著的舞台文学剧”,甚至有人直接判定这出话剧就是“文学”……吊诡处在于,在舞台上念书看似“忠于”原著,实则刚好消解了小说的媒介条件,由被阅读的作品变成了“有声书”。这在表达上偷换了概念,演员时而参与到故事情境中,时而抽身到一旁对故事进行评述。这种最笨拙的“间离”手段,不停地把观众从戏剧情境里拽出。有趣的是,演员间的对话——作为传统话剧的基本手段——几乎不可见。
与之呼应,舞台上的置景刚好有三面玻璃墙,以之为前景,全部真人表演都在玻璃墙后面呈现。这种直接凝视被阻断后,观众不得不聚焦在舞台上方的幕布投影,表演的情境都被摄影机“记录”下来,同时放映在幕布上。玻璃墙和投影,让观众无法“直接”把目光投射到演员身体上,而是被迫注视着拍摄的不完整的情境段落,从中得不到实质信息,只能捕捉演员被“记录”到幕布上的即刻情绪。舞台上呈现的只是冰山一角,原著冰海之下的神秘和恐惧绵延到观众的意识中。
舞台剧严格按照原著小说分幕。
到了第三幕,刚好对应小说的第三章“法特”。一位黑人体育记者去墨西哥报道拳赛,意外获知了此地持续发生的针对女性的虐杀事件。然而作为一个蹩脚的记者,他什么也做不了。这是典型的“反类型”电影套路,这一幕的角色行为通过幕布上的投影被观众看到,镜头晃动,模拟了法特的主观视角,把他的震惊和无力传递给观众。
第四幕“罪行”以女声旁白“背诵”小说原文开始,历数发生在墨西哥城附近的女性虐杀案,在加工制造业崛起的背景下,在城中村、工地、烂尾楼、甚至在街边,女性被残忍奸杀,一具具被摧残的身体根本挤不进疲于奔命的人们的视野,当地人对发生在身边的骇人暴行视若无睹,警方毫不作为——要么查到权贵阶级就自觉罢手,要么干脆去保护黑社会以求活得体面。冷峻的女声旁白,每念出一个女人的姓名和死状,就相当于让观众“目击”一次暴行。在重音的强调下,观众被迫成了视而不见的目击者,每个人都和当地人一样麻木,每个人也都间接参与了针对女性的暴行,以及对暴行的掩盖。
在第五幕,主创试图显影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存活在我们身边的暴力幽灵。表面上,舞台叙事的任务是揭开作家阿琴波尔迪的身世之谜,实则是揭开他被迫参军并历经二战的每一次身份变换。他在经历纳粹犯下的暴行中,既是被动的参与者,也是目击者和记录者。他的身份一次次被历史的暴力进程抹除,他也逐渐习惯了对身份的隐藏,成为世界上最神秘的作家,行踪飘忽,甚至出版商也没见过他的真面目。
还是通过玻璃墙和摄影机,第五幕的两条叙事线渐进而行:阿琴波尔迪的身份之谜,有人自称是墨西哥虐杀女性案件的凶手,这两条线在某一刻似乎能交叉。观众见证了审判暴力的过程。面对暴力,你可以视而不见,却无法抽身逃离。我们由此体会到人之为人的幽暗本质,观众也会感受到无力与绝望。
在首演和复排之间的重述空间
2022年是剧作家莫里哀诞辰四百周年,法兰西喜剧院邀请比利时导演伊沃·凡·霍夫重排《伪君子》。该剧首演于1664年,公演后不久,就因为对教会的讽刺遭到当局禁演。此后,莫里哀以各种方式修改剧本以规避审查,三年后,他终于说服了路易十四,获得该剧的公演权。在戏剧史上流传着一种说法——“法语是莫里哀的语言”。在戏剧史上,《伪君子》始终是“警世钟”一般的存在,被搬演过无数次。面对这样一部早已深入人心的名作,如何把原作的讽刺精神熔铸进当代议题之内?在法兰西喜剧院的舞台上,伊沃·凡·霍夫铺了一张白纸。《伪君子》那早已为人所熟知的故事、人物间荒谬的关系、这出戏的戏剧性和反戏剧性,都将在这一张白纸之上奔突激荡,也都注定会在这张纸里瓦解重构。
苦修教士答尔丢夫被富商奥尔贡一家收留,他的高尚风度很快征服了一家之主奥尔贡,而他严苛的禁欲观念又把家里的老夫人(奥尔贡的母亲)洗脑成一个狂热的道德审查者。答尔丢夫逐渐获得了家庭的主导权,他攫住了奥尔贡母子对他的信任,窃取全家人的秘密、挑逗奥尔贡的妻子,甚至让奥尔贡甘愿把女儿嫁给他。戏剧的每一次重排,都是创作者对文本的重述。伊沃·凡·霍夫在文本上采用莫里哀首演的三幕结构,他“破题”的角度是舞台。他取消了原故事的空间——家庭——的视觉形象。在新版《伪君子》的舞台上,很难看到生活的痕迹,观众无法通过舞台置景获得“真实”。导演不在“拟真”方面浪费精力,反而是透过对空间的重构,实现了对所谓真实的阐释。

在这张纸上,答尔丢夫第一次被奥尔贡一家人“洗”干净,成了他们都渴求的精神崇拜对象。也是在这张纸上,答尔丢夫与奥尔贡的妻子私会,一步步走入圈套。还在这张纸上,奥尔贡窥见这个伪君子原形毕露。一切败露之后,奥尔贡忍无可忍,用头顶破了纸,最狂热拥护答尔丢夫的老夫人,却拒绝承认真相,而她最终也死在了这张纸的正中,白纸从遮羞布变成了裹尸布。
三百多年前,莫里哀的这部讽刺喜剧激怒了宗教保守势力。他们究竟在害怕什么?答尔丢夫和他的信徒,提线木偶般演绎着反智的荒谬行径,是谁在他们背后牵动线绳?答案,就在那张纸上。
在纸上第一个登场的是老夫人,一个最有权力的失权者,一个不准别人张口的歇斯底里者。从老夫人开始,这张纸成了家庭权力的角斗场。序幕里,当奥尔贡发现答尔丢夫的时候,他第一个召唤的人是“妈妈”。这是一次招魂,一家之主对卫道士母亲的招魂,也是匮乏的一家人对伪君子的招魂,他们给自己招来了精神控制和道德审判。第三幕,奥尔贡亲手用纸裹住母亲,全家为老夫人举行葬礼。这不仅是送葬,而是一次“驱魔”,全家人的理性和常识回归后,他们对代表卫道士的老夫人驱魔,也是对曾经被洗脑的自己驱魔。在舞台上,白纸的存在远比答尔丢夫的角色重要得多。我曾经困惑为什么现代戏剧的舞台造型要“过度表达”?为什么一定要强制观众“看到”造型的过程?直到《伪君子》的重排,我才恍然:正因为把舞台造型摆在前面,我们不得不目击到“制造”答尔丢夫的过程、“建构”整个资产阶级生活空间的过程。这正是现代戏剧作者的狠辣手笔,彻底消解“典型时空(17世纪的法国)中的典型人物(答尔丢夫)”,进而给观众们当头棒喝:历史始终循环,荒谬不停复制,我们每天都在制造答尔丢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