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新时代心理健康的新诠释
作者: 俞国良 何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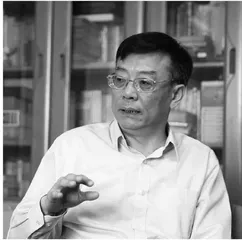
健康与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与论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自身的幸福感获得和心理健康问题;而维护与促进心理健康的实践,也进一步促进了幸福感的实现。俞国良教授认为“追求并获得幸福感,实现人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心理需要,无疑是完成心理健康实践的过程,更是完成生命本质力量的精神突围、实现幸福感的过程。”究竟幸福感的成分和心理健康的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着怎样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关系,本期访谈我们邀请俞教授为读者进行深度剖析。
关键词:幸福感;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社会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2684(2022)19-0004-05
俞国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心理研究所所长
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专家委员会委员
健康与幸福就像一对孪生兄弟
何妍:俞教授好!近些年,全社会对心理健康与幸福感的关注持续升温,而心理健康与幸福感也是心理学界研究的热点。总体上,您怎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俞国良:有关健康与幸福,古今中西的哲贤圣者都曾有过无数的训诫和智慧,且已达成共识:对于一个人,健康与幸福是改善生存生活状况、享受生命和成就生涯的前提;对于一个国家,健康与幸福是创造财富、开创美好未来的根基;对于一个民族,健康与幸福是繁荣文化、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石。近几十年,人们对健康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深化,认为健康不仅仅是指躯体没有疾病,还包括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这种新的健康观念使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演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把心理健康和幸福状态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可以说,健康与幸福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良好的心理健康与幸福状态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开发个体心理潜能,增强学习与发展能力,适应家庭和社会生活,支持可持久的人际生态和环境生态,并有助于安全、高效、快乐地融入社会生活。它既是一种发展资源,也是一项发展目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在2018年8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就明确提出了“健康第一”的理念;并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毫无疑问,健康且幸福地生活着,这是一种极致的生命境界,也是新时代对心理健康宗旨和目标的一种全新诠释,更是对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国家强盛发展具有特殊战略意义。
幸福感是心理健康的本质特征
何妍: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幸福感是心理健康的本质特征”,从心理学意义上,如何解释幸福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
俞国良:心理健康作为一个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具有许多特征,如结构特征、动态特征、主观特征等。心理健康的积极、消极之分是其结构特征,“微笑下的抑郁”是其动态特征,而心理健康的诊断标准不能像患“感冒”一样进行诊断,则是其主观特征。显然,上述种种特征都是表面化、现象化、非本质化的特征,而幸福感则是心理健康的本质特征。因为“从心理健康到获得幸福感”这一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场生命本质力量的精神突围。
在心理学意义上,幸福感主要指直接体验到的快乐、欣喜与愉悦的情绪,以及基于生命质量而产生的对生活、对自己、对社会关系的满意程度的评价。尤指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的集合体。这几个概念作为幸福感的主要成分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它们都与心理健康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
主观幸福感是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体验和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目前研究者普遍认为,主观幸福感就是一种快乐体验、一种对生活的满意感,并在情绪情感上予以表达。显然,人们对于自己美好生活的主观想象是一种期盼,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与现实之间存在差异在所难免,能否正确、客观地认知和接受这种差异,是衡量个体是否心理健康的“分界岭”。维持并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实际上就是让人们生活得幸福快乐,至于人们是否真正体验到幸福快乐,则取决于个体的主观判断、评价,即主观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为个体心理健康奠定了情绪情感体验的认知基础。
心理幸福感强调幸福感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我完善、自我实现,是人的心理潜能的完美再现。心理幸福感试图将从古希腊到现代心理学的有关幸福的观念整合到一起,融合荣格的个性化、奥尔波特的成熟形成、罗杰斯的完全功能和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等诸家理论,认为快乐虽然属于幸福,但幸福不能仅仅归结为快乐,而是人的积极心理功能的能动反映。人类寻求心理健康、心理和谐的过程,并不仅仅只是主观情绪上的体验,也是自我实现的过程,更是开发心理潜能、提高心理幸福感的过程。即心理幸福感是个体心理健康的客观反映。
社会幸福感强调幸福感的社会属性,关注个体的社会功能、社会价值和社会表现。由于纳入了社会取向的因素,而使我们能够更好、更确切地理解幸福感的最佳功能以及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社会幸福感包含社会融合、社会认同、社会贡献、社会实现以及社会和谐五个维度,它从“社会适应”角度被概念化为个体对其环境和社会功能的认知和评价,其实质就是社会适应。与此对应,心理健康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适应良好的状态,这样符合逻辑的结果便是社会幸福感最后成了心理健康的社会产物,这也与目前心理健康研究的发展取向完全吻合。
何妍:前面您分析了幸福感的三个成分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可以说是横向的一个视角。学习心理学的朋友都知道,幸福感是积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和研究方向,而心理健康在传统心理学研究中更多指向消极的维度。请您从纵向的角度谈谈幸福感作为心理健康本质特征的社会历史基础。
俞国良:我们可以从幸福感研究与概念演变的发展轨迹来看,这是幸福感作为心理健康的本质特征的历史起点。心理学自1879年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把研究重心放在了对心理病理问题的研究上,这使得心理学几乎成了病理心理学的代名词。在这种研究取向下,心理学为心理疾病的治疗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使得心理学成了专门为一部分人服务的学科,使得学科的发展道路变得单一化和片面化,从长远来看,势必会削弱心理学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这一点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以心理健康问题研究为核心的积极心理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并迅速“异军突起”。它强调心理学不仅要研究人或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还要研究人的各种积极力量和积极品质,而对幸福感的研究正是积极心理学的一个核心内容。
心理学对于幸福感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虽然研究历史非常短暂,却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结果不但加深了人们对心理健康的理解与认识,拓展了心理健康的研究内容与范围,而且强有力地促进和提升了心理健康研究的绩效,这更是使幸福感与心理健康直接发生了联系。可以说,幸福感与心理健康的“历史演变”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是幸福感作为心理健康本质特征的社会历史基础。
心理健康是幸福感的重要载体和媒介
何妍:与“幸福感是心理健康的本质特征”相对应,您也特别强调了“心理健康是幸福感的重要载体、媒介和具体表现形式”,这一论断的提出是基于哪些理由?
俞国良:心理健康作为幸福感的重要载体和媒介,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从内涵上审视,心理健康与幸福感当属仲、伯之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阐释,心理健康不仅是指没有心理、情绪、行为和社会领域的功能性障碍,而且还包括在心理和社会领域维持的最佳功能或积极的幸福状态。这里既有“负面清单”,又有努力方向。再进一步,心理健康与幸福感的内涵固然有相似地方,但幸福感的内涵显然更为深厚,涉及内容更多、范围更广,站位也更高。一句话,所谓心理健康,归根到底就是一种幸福状态,一种幸福感的具体表现形式。
第二,从溯源上考察,心理健康需要幸福感的支撑。前面我们讲到,心理健康实际上是一种幸福状态,而这种状态又来自个体要么根据经验的主观判断,要么根据事实的客观评价,要么根据社会适应的综合评定。自然地,幸福感就成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源泉,而心理健康作为其重要载体或媒介,特别需要幸福感的有力支撑。以主观幸福感为例,它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由生活满意度、领域满意度和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四部分构成,前两者是认知成分,后两者是情绪成分。这些心理维度都是支撑并构成心理健康结构的核心成分。再深入考察,从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来看,其中社会文化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具有共同的文化来源,心理健康凭藉社会文化的媒介从而得到幸福感的支撑。目前,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大量研究者开始关注人类的积极心理品质对个体心理健康及心理和谐发展的影响。这种带有鲜明幸福感价值取向的“美德”,不但体现了有关心理健康的主要特质,而且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心理健康的共同认知,以及这种认知对幸福感的“反哺”作用。
第三,从目标上解析,心理健康的价值追求就是幸福感。毫无疑问,人格是心理健康的核心,也是幸福感的基础。在有关人格特质与幸福感的研究中,人们关注最多的就是大五人格特质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开始人们关注的主要是外向性和神经质两个维度与幸福感的关系,得出了几乎一致的研究结果,即认为外向性与积极情绪、生活满意度有关,与负性情绪无关,可以提高个体的幸福感;而神经质与消极情绪有关,会降低个体的幸福感。可见,仅仅是大五人格的外向性和神经质两个维度,就彻底“绑定”了幸福感,又顺便“捎上”了心理健康的“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高新技术产品(如智能手机等)在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影响着人们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其获得幸福感。
第四,从结果上考量,心理健康应是幸福感的副产品。以幸福感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对心理健康发挥的重要影响为例,研究指出,社会支持可以缓冲生活压力的消极影响,并促进个体的社会适应和身心健康。社会支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个体的自主需要、胜任需要和关系需要等基本心理需要,并通过三种需要的满足进而影响其幸福感、心理健康水平。例如,来自老师的支持有利于帮助学生提升对自己自主性与能力的观念,来自同伴的支持能够满足其对关系的需要,增强其关系满足感。这些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因素对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这种社会支持的中介或调节因素进而作用于个体的幸福感,最终表现为他们的幸福或适应状态。也就是说,社会支持作为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或调节变量”,作用于个体的知、情、意、行等心理过程,同时也有效影响了心理健康水平,即心理健康成了幸福感的副产品。
幸福感与心理健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何妍:从前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幸福感和心理健康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这是否提示我们,考察心理健康的时候需要纳入幸福感要素,反之也是一样。
俞国良:是的。对幸福感的孜孜追求,使人们开始更加重视心理健康;维护与促进心理健康的实践,也使幸福感的实现进一步成为可能。幸福感业已成为新时代对心理健康的一种新诠释,而心理健康作为个体能够正确思考、表达情绪、相互交流和享受生活的基础,其对人健康成长的有力推动,使自我得以充分实现。从这个角度说,追求并获得幸福感,实现人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心理需要,无疑是完成心理健康实践的过程,更是完成生命本质力量的精神突围、实现幸福感的过程。
可见,幸福感与心理健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考察心理健康时,不仅要纳入幸福感要素;在考察幸福感时,也要纳入心理健康要素。即必须充分考虑幸福感与心理健康及其要素间交互作用后产生的协同效应、叠加效应。
何妍:也就是说,不仅幸福感与心理健康会相互影响,它们的成分或构成要素也会影响到对方。请您首先谈谈心理健康对幸福感的影响体现在什么地方,具体是如何影响的?
俞国良:心理健康影响幸福感的内容。幸福感和心理健康都是多学科的研究对象,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认为,在活动与实践层面,最终落实幸福感具体内容的载体,就是心理健康。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3月23日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曾指出,“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健康。健康是1,其他的都是后边的0,1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确实,健康、心理健康相对于经济建设是“软件”,但相对于幸福感却是“硬件”。心理健康投入的人才、队伍和资金是实现幸福感必需的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心理健康的知、情、意、行等内容也深刻影响着幸福感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