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青少年,漫长的结核病战争
作者: 张婉莹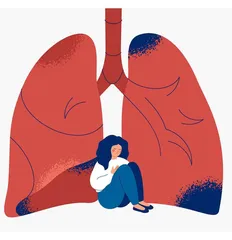
晚上十点,15岁的李欣躺在床上,清晰地听见“呼哧呼哧”的水声,伴随着自己每一次呼吸。
暗夜让听觉变得灵敏,李欣感受到胸腔里有一种牵拉感,每呼吸一次,胸腔都会发出这种声音。甚至平躺在床上,不经意翻身时,也会有“水”跟着一起流动。
李欣很确定这不是幻觉,即便在武汉金银潭医院面对耐药结核病科主任聂琦的询问时,李欣依旧很坚定地表示,是水声。但她的父母却听不到。
这是耐药结核杆菌在李欣身上留下的“印记”——来自结核性胸膜炎产生的胸腔积液。结核病,扰乱了她对很多事物的感知。李欣来自一个结核家庭,奶奶和自己,先后确诊耐药结核病。这种传染性的疾病,不仅一度摧毁了她的免疫力,也动摇了她与奶奶的亲密关系。虽然没有明确证据链证明是奶奶“传染”给李欣,但她有时心里会隐隐埋怨奶奶,她不愿再与奶奶一起生活,也不愿意坐奶奶坐过的车。
一个被忽视的现实是,2023年全球有1080万新发结核病患者,其中55%的结核病患者是男性,33%是女性,12%是儿童和青少年。在中国,像“李欣”这样的患者,绝非特殊的少数群体。而且他们容易被忽视、被误诊,2023年,这个群体的治疗覆盖率,仅为55%。
李欣所患耐多药结核病(或称耐药结核病),被认为是结核病的“升级版”,也被称为有传染性的“白色癌症”,全球治疗成功率仅为68%,远低于非耐药结核病的治愈率(88%)。治疗费用更贵、治疗时间更长,且副作用也更多。对于青少年来说,走出耐药结核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早李欣3个月确诊耐药结核病的奶奶,因有严重药物反应与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只能回到农村老家,进行保守治疗。而李欣经过500多天的治疗,终于能够重返樱花盛开的校园。
她需要重读初一,而之前所在班级的同学,已在挂着中考倒计时的教室中奋笔疾书。当同龄人在操场奔跑时,李欣只能在消毒水的气味中重新学习如何拥抱。在最需要建立社会联系的时候,他们却变得孤立无援,这是李欣们的普遍困境。
对他们来说,走出结核病的阴影,是青春期最大的痛。
狡猾的结核
谁也不知道李欣的奶奶是如何患上结核病的。
最开始是咳嗽、发热、胸痛、盗汗等症状。确诊后,奶奶从农村老家赶到武汉住院。更为不幸的是,奶奶患上的是耐药结核,由于自身有高血压等慢性疾病,能选择使用的药物极其有限。出现极为严重的药物反应后,她只能出院与爷爷回老家休养。
多项调查研究显示,肺结核报告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呈上升趋势。在2023年,60岁以上老年患者占肺结核患者群体的43%。65岁以上更是易感结核病的重点人群。
结核杆菌非常狡猾,进入人体后不会立即发病,而是蛰伏着等待合适的时机。当人们出现衰老、免疫力低下等状况时,就是结核杆菌“爆发”之日。
结核病密切接触者,是需要主动筛查的重点人群。在奶奶确诊结核病后,李欣一家与大伯一家都到医院进行过检查。当时李欣只有一个指标过高,但并未确诊。
当同龄人在操场奔跑时,李欣只能在消毒水的气味中重新学习如何拥抱。在最需要建立社会联系的时候,他们却变得孤立无援,这是李欣们的普遍困境。
直到三个月后,持续半个月的反复低烧,终于让李欣父母察觉到不对劲。她先是在县里的诊所治疗,后在市里的医院确诊患上耐药结核。
得知女儿确诊,李欣的爸爸很难相信,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在自己的家庭出现两次。他后悔自己把女儿的低烧当作感冒,耽误了治疗。面对妻子的埋怨,他将女儿从老家带至杭州治疗,在新冠疫情期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结核病患者的症状与很多呼吸道疾病相似,即便是医务工作者,也容易无意间忽略这一点。“被动发现”的策略,一方面可能会耽误患者治疗,另一方面,当处于活动期的结核患者就诊及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过程中,亦会进行二次传播。
与被动发现相比,在密切接触者、结核病高危人群中进行“主动发现”策略,可以将诸如李欣这样的患者提前“找”出来,既提高患者诊疗成功率,也降低了传播风险。
蓄水池
“主动筛查可以将结核杆菌的传播链抑制住。”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圳)副院长杨崇广教授告诉南风窗。
他是中国防痨协会青年理事会副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传染病(结核病)系统流行病学等相关研究。他将结核病患者人数比作一个蓄水池,如果没有新的水源注入,那蓄水池里的水,会随着自然的生老病死而“蒸发”掉。但目前人类“消灭”不了结核病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不断有新的水注入。
2022年《中国防痨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中国15岁以上携带结核杆菌的人数为20.34%。相当于全国每5人就有一个曾经感染过结核杆菌,总人数约为2.8亿。
在杨崇广看来,携带结核杆菌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病。近3亿人中的多数人,身上的结核杆菌处于“休眠”状态,在他们一生中,只有5%~10%的概率会发病,成为活动性结核。“只要控制住这一部分活动性结核人群,主动把他们找出来治疗,就能有效减缓结核病在社区中的传播。”

2024年11月28日,国家疾控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24—2030年)》(下称《规划》)就提及:“我国仍有约10%的县(区)为高流行地区,防治工作不均衡,患者主动发现和规范治疗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积极的预防措施和新技术应用不足,防治工作不容懈怠。”
结核病,听起来是一种遥远的疾病(如契诃夫、卡夫卡、鲁迅、林徽因等历史名人都死于结核病),但在当下的世界里,它正越来越猖獗。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结核病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因结核病死亡人数为125万,结核病重返全球单一传染病死因首位,其导致的死亡人数几乎是HIV/AIDS的两倍。另有数据表明,约有20亿人为结核杆菌潜伏感染者。相当于每4人中,就有一位携带有结核杆菌。
潜伏群体的庞大,带来了患者发现率不高的严峻问题。对此,《规划》才提出“要强化主动筛查”。首先要加强医疗机构预检分诊,及时诊断患者。此外,对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老年人和糖尿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监管场所、社会福利机构等重点场所,以及疫情高发的重点地区,加大筛查力度。另外要推广应用新技术。
很快李欣就感到了孤独。在长达18个月的治疗期内,她没有同龄人一起玩耍。朋友们甚至不知道李欣休学,除了家里人,也没有人知道李欣与奶奶患上结核病。
由于“主动筛查”这一策略,李欣在结核病早期得以发现并接受治疗。在经历18个月的治疗后,她成功战胜了耐药结核病,相较于同患耐药结核病的奶奶,李欣获得了“新生”。
孤立无援的儿童
得知因为结核病需要休学做治疗时,李欣的第一反应是高兴。
对于一个刚上初中正需要睡眠的孩子来说,相较于对疾病的恐惧,不用6点钟起床去学校,才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那时的李欣不懂什么是结核病,在她看来,没有学业压力还可以躺在病床上玩手机的生活,“过得也蛮开心”。
可是,很快李欣就感到了孤独。在长达18个月的治疗期内,她没有同龄人一起玩耍。朋友们甚至不知道李欣休学,除了家里人,也没有人知道李欣与奶奶患上结核病。
刚入初中,没几个月就患病,李欣还没在新校园里结识到几个交心挚友,就住到了医院里。即便现在回到校园,见到曾经班里的那些同学,也没有了太多交集,“见到以前班里的同学会尴尬”,李欣停顿了会儿说。
结核病对她的影响,除了现在跑200米都喘的身体,还有青春期少女社会时钟的停滞。对李欣这样的年轻患者来说,孤独和无助,是普遍存在的心理。
北京胸科医院党委副书记、临床心理学主任医师庞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大多患者需要隔离治疗,很多青少年患者可能会感到孤独,与同龄人产生距离。加之病情复杂或治疗时间长,他们还可能会感到无助和无望,进而对病情治疗和康复失去信心。
儿童对于结核病的抵抗力很弱。尤其5岁以下幼儿,免疫屏障较弱,如果得了结核,很容易发展成脑膜炎或全身播散型肺结核,死亡率高达50%。
由于儿童结核病早期症状不典型,可能仅为低热、体重降低与精神萎靡,很容易被误诊为普通感冒或肺炎,因此儿童和青少年结核病漏诊率非常高。世界卫生组织在2023年版《消除儿童和青少年结核病路线图》中指出,15岁以下儿童结核病的误诊、漏诊率达40%,5岁以下者甚至高达69%。
北京胸科医院精神心理科是全国胸科医院中首个独立建制的科室,庞宇在临床中发现,结核病会导致青少年结核病患者暂停学业,从而带来焦虑和抑郁的情绪。若长期不愈,还可能使青少年患者产生情绪波动,容易受到外界刺激而悲伤和哭泣,有的还表现出易冲动的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病耻感有时比躯体疾病本身对青少年的健康影响更大。有些青少年患者可能会因为患病而感到羞耻,害怕被人歧视和嘲笑。不止青少年患者,很多成人结核病患者,也会因为担心“社交孤立”选择隐瞒病情。
这种自我规训,实质上是福柯笔下“规训权力”的微观体现——当社会通过疾病标签建构起“健康—病态”的二元对立时,患者将不得不承受“污名化身份”带来的符号暴力。
“一老一小”
儿童结核病具有特殊性,传染源多为家庭内成人患者。在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中,老年人在家庭中常承担照顾儿童的责任,若老年人处于结核潜伏感染期,则儿童因长期密切接触而更易感染。
家庭结构中的代际互动模式与文化认知特性,使得老年人与儿童成为结核病传播链的关键节点。提升筛查意识,降低“一老一小”群体的疾病负担,才可以阻断结核杆菌从家庭到社区的传播链。
武汉金银潭医院耐药结核病科咨询员谢家强,从事咨询关怀服务工作,陪伴李欣在金银潭医院住院期间的治疗。她告诉南风窗,像李欣与其奶奶这样“一老一小”的确诊患者并不少见,“患者中有学生也有老人”。
在各种人群中,根据患病率情况,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65岁以上老年人、糖尿病患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既往结核病患者等,被作为开展结核病主动筛查的重点对象。
以老年人为例,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慧解释,相关研究表明老年人结核潜伏感染率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发病率是全人群的7倍;全球结核病死亡人数中,老年人占比达到50%—60%。随着中国老龄化加剧,老年群体发病比例还可能继续升高。
针对一老一少的主动筛查策略,贵州省的经验值得参考。
学生群体的主动筛查工作进行得更早,其疫情发现情况呈现出先增后降的趋势。目前贵州省学生报告发病率由2018年最高的每10万人55例,下降到2023年每10万人27例,下降了56%。
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所所长李进岚向南风窗介绍,贵州省在2023年将“一老一小”结核病主动筛查工作作为省里十大民生实事进行了落实。其中,老年人筛查由卫健、财政、民政三部门协同,与老年人的健康体检工作一起配套落实;学生筛查工作则是由卫健、财政、教育三部门协同,对初一、初二、高二和中专二年级的学生进行体检。
2023年,贵州省投入5040万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及4672万元省级财政经费,共计9712万元来保障“一老一小”的筛查工作。
成效非常显著,2023年,贵州省一共筛查了257万老年人和144万学生;此外,通过胸片筛查,还发现了一些慢阻肺等疾病的患者,相当于一张片子发现了多种疾病。
李进岚向南风窗介绍称,学生群体的主动筛查工作进行得更早,其疫情发现情况呈现出先增后降的趋势。目前贵州省学生报告发病率由2018年最高的每10万人55例,下降到2023年每10万人27例,下降了56%,可见主动筛查对于结核病防控的成效。
除了主动筛查这一手段,最重要的是,社会需要对结核病患者消除歧视与误解。很多患有结核病的人即便康复,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患过结核。甚至有人因为害怕住院被单位发现,而选择隐瞒病情偷偷治疗。
人们用隐喻来污名化疾病。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谈到结核病时写道:“在疾病被赋予的某些道德判断之下,潜藏着有关美与丑、洁与不洁、熟悉与陌生或怪异的审美判断。”
可随着社会与医学的进步,人们赋予疾病的隐喻不减反增,由此产生的对待疾病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控制疾病的手段造成的二次伤害,甚至超越了疾病本身。
正如李欣所经历的那样,当疾病阴影裹挟着祖孙隔阂、学业断层与社会凝视,李欣“听”到的水声背后,涌动的是一个中国青少年患者群体隐秘而汹涌的生存暗流。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欣为化名。感谢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中心耿引弟、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屈燕及武汉金银潭医院耐药结核病科对本文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