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千年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胡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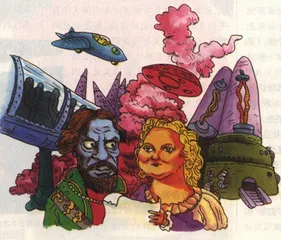
千禧年来临了(不论千禧年的概念与古老的中华文明有多大关系),新未来的展望与预测成为热门商品。我有幸或曰不幸地被一些媒体选中,要求回答下一个千年将会发生什么。这当然是一项荒谬的要求,我连明年都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又焉敢妄论千年?
在网上看到一篇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谈论“下一个千年的性与性别”的文章,不禁为她硬啃这样一个力不能胜任的题目感到担心。不用说千年,20世纪百年性文化的变迁都非任何人所能想象。
1900年,有谁预见过罗德曼、麦当娜、互联网聊天室中的性对话、跑马拉松的健壮妇女和梳着马尾发给婴儿换尿布的男人?谁能够洞察避孕药和克隆术的发明及同性恋权益运动的兴起?
我和能够阅读我写下的这些文字的读者诸君都是跨世纪的人。我们的生活现在应该是什么样子,100年前专家早有定论,只不过现实与他们的期望并不完全相符。没有空中汽车(有一种飞机叫做“空中客车”,但那只是个比喻);没有宇宙飞船载着我们奔向太空度假地(连不载人的机械装置都登不上火星);也没有机器人替我们打理家务。
会飞的汽车曾经是人类长久为之着迷的梦想。一个世纪前,一家法国公司发行过一系列描述2000年生活的卡片,那时,人们连怎样造出在地上奔跑的汽车都不甚了了,而这些卡片却大胆绘出人们驾车升空、在空中咖啡馆喝咖啡的情景。
电影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所有关于21世纪的影片中都少不了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汽车。1930年,好莱坞曾经出品过一部叫做《想象一下吧》的音乐片,其想象力也是好得可以:它设想1980年空中汽车就会在纽约普及。
事实上,福特汽车公司的设计工程师说,造出一辆能在空中飞行的汽车并非完全不可思议,但会耗资1000万美元,听起来像造波音747一样。造价昂贵倒是件好事,如果空中汽车易打易造的话,我们上街都得戴着头盔,以免被空中车祸发生后掉下的碎片砸晕。
为什么过去那些流行的预测最后成了笑柄?因为预言家们总是从已知的世界出发,预测现有事物的改进,根本无力想象崭新的、能够改变世界的发现。他们没有预见过电视和电脑,在每一个家庭、每一间办公室中出现的这种“永动装置”,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约翰·埃尔弗雷思·维特金斯在20世纪初作过很多出色的预测,比如预言了空调器、国际长途电话服务、郊区的兴盛、彩色照相术以及冷冻食品。但他在另外一些方面过于乐观,比如他说,我们将会消灭所有的蟑螂、苍蝇和蚊子,又说,从郊外住宅到办公室上班将仅需数分钟。他似乎忘记了新的交通工具会互相阻塞。到了1950年,《大众机械》杂志宣称,50年后人们将会住在塑料房子里,使用防水家具。“2000年的时候,家庭主妇将用水龙带每日冲洗房间”。
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没有人愿意住这种房子。人们对旧有的并不那么高效的东西抱着顽固的态度。所以在进入新千年之际,在我们仍为交通阻塞所苦、为苍蝇和蚊虫叮咬的同时,人性的变化比任何专家预测的都要小得多。
唯有一个预测是永远准确的:人们会继续作出各种各样的预测,因为人类具有天生的焦虑感和不安定感,总想探知未来。也正是为此,那些通灵者、伪科学家和煽动家对未来的简单解释才会赢得大片市场。
伪科学预测总是比科学预测更有吸引力,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伪科学家以一种确凿无疑的口吻发言,而科学家则令人烦恼地使用概率语言。大多数科学预测事关群体和趋势,与个人和特殊情况无关。因此,科学家可以准确地说,吸烟将增加早亡的可能性,但却无法预料一位特定的吸烟者是否会患肺癌。
第二,伪科学预测的基础是本能、信仰、传说和个人体验。它更具亲和力也更戏剧化。科学预测则源于统计概率,高度的数据化使其显得冰冷而遥远。科学家知道自己不能够预测什么,而伪科学家则会预测任何人们要他们预测的东西。
当然,在每一年的年尾,或者,在更罕见的百年年尾乃至千年年尾作一些愚蠢的预测无伤大雅,也很好玩;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进行预测和相信由别人作出的预测?这是严肃的问题,因为它牵涉到我们为自己的生活所作出的大大小小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