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围墙的图书馆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胡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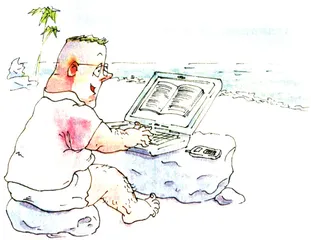
1997年10月,大英博物馆的环形阅览室宣告关闭,其藏书和读者都被转移到一个崭新的、拥有一切现代化设备的图书馆中。工作人员对此兴奋不已,因为在新建筑中,沉重的、灰尘扑鼻的卡片盒被计算机系统所取代,旧式的书籍输送系统也实现了自动化。每一张阅览桌上都配有插座,供人们接驳计算机和电话。图书馆与互联网世界融为了一体。
但许多人对阅览室的搬迁怀有复杂的感情。这一行动似乎一举抹去了一段漫长而奇特的历史。古老的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曾经是许多学术文化泰斗和巨擘的栖息地。对弗吉尼娅·沃尔夫来说,它好像“悬于眼前的有圆形穹顶的大脑,人在其中就好比巨大的秃脑门里闪现的一个想法”。只有小说家才能想出这样的比喻。这个“有圆形穹顶的大脑”孵化出了多少思想!叶芝在此编撰了爱尔兰童话集,肖伯纳在此研究过瓦格纳的歌剧,为了追寻马克思的踪迹,列宁曾使用化名“雅各·李赫特”进入这个神秘的地方。当然,不用说,它也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之处,那日后掀起滔天巨浪的理论给阅览窒增添了浓厚的传奇色彩。后来,旅游者们会专程前往参观马克思用过的桌子,他曾坐在那张桌子旁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汲取营养,绘制出革命的蓝图。
环形阅览室其实是一个通往后面巨大书库的建筑入口。从外面看,那古典的、圆柱支撑的正门仿佛一个图标,指示着入口。环形的、有圆形穹顶的阅览室在平面图上看起来仿佛分区的硬盘,读者可以在阅览桌上填写上架书的编号,工作人员会在书库中检索,书用完之后被重新上架归位。今天的计算机技术人员都知道数据库服务器,从功能上讲,当时图书馆的全套流程就相当于运行一个巨大的、缓慢的服务器;你发出请求,然后得到内容。
这种非常巧妙的实用设计是长期演进的结果。在早期的图书馆里,藏书册数很少,书架就在阅览室中依墙而立。后来,随着藏书量与阅览空间比例的转变,书库与阅览室分隔开来,并日益成为建筑空间的主体。1854~1856年,西德尼·斯默克为大英博物馆旧楼设计了一个圆形辅楼,书库部分成为巨大的、与阅览室分离的钢铁结构。
流行的个人计算机图形用户界面与斯默克精心设计的建筑方案大有异曲同工之妙。图标排列在屏幕上,使入口一目了然。点击一个图标就像敲一扇房门,用户进入一个空间,在那里可以要求查询信息。应用户的查询要求,软件的例行程序从磁盘中检索文档,把文档显示到屏幕上供用户审查和操作。
现在,从这个小规模的例子推演开去,设想一个大规模的数字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永远没有下班的时候,正门不用石头材料而用像素制成,分布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个屏幕上。布置书架、查找图书的工作变成了建设数据库并提供搜索和检索例行软件。巨大的书库几乎消弭于无形,你将不再可能告诉旅游者哪儿是下一个千年中某位马克思坐过的地方。
传统的保存书的方法存在空间的压力,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拥有1500万册图书,书架长度达550英里;大英图书馆也有1200万册图书。正因如此,人们才致力于“数字化保存”。数字化图书馆的一大优点是它不受实体结构的限制,然而,它却可能导致信息过量、数据超载。在致力于解决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书册的排放的同时,我们考虑过广泛的哲学问题吗?比如,我们真的因为有了这些信息而变得更加聪明吗?
在网络如浪涌来的时代,难以产生马克思般的智慧。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比林顿说:“我们称之为信息时代,这意味深长。我们谈论的不是知识时代。” 图书馆不列颠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