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WTO:轿车与小麦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三联生活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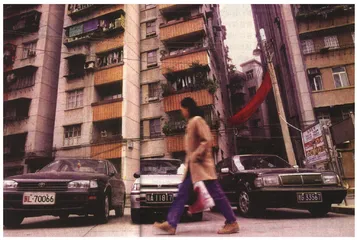
“他们正努力在入关前给消费者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
6月20日闭幕的上海车展依旧拥挤不堪地吸引了中国先富阶层的爱车者们。由于此番车展被认为是中国入关前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展会,从20多个国家纷至沓来的整车和配件制造商在临展前一天最终确定为500多家,以至于主办者不得不首次占用了当地的三个展览中心。
通用、福特、奔驰-克莱斯勒、大众、丰田、雪铁龙、沃尔沃等外国巨头,国内三大轿车厂商和上海通用、广东本田、东南全顺等30多家整车制造商,在6天的展期里纷纷向热情高涨的人群出示他们带来的神秘“礼物”。这些熠熠生辉的新成员普遍售价在25万元人民币以上。“他们正努力在入关前给消费者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一位从北京最大的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专程来参观车展的销售商肯定地说,“关税的下降将使这些现在看来较为昂贵的轿车在中国吸引大量的买主。”
在亚运村汽车市场,这个时候最为畅销的轿车还是在上海遭到冷遇的“桑塔纳”、“富康”和“捷达”,以及那些1.0左右排量的价廉物美的经济型轿车——它们甚至根本没有资格走进上海展会富贵典雅的车群。当然,畅销也是相对而言。“亚运村”和同被称为北京车市“晴雨表”的北方汽车交易市场今年迄今为止的轿车销售量只相当于去年同期的1/3。据“亚运村”的一位接待小姐介绍,在惨淡的行情中,国内三大品牌目前已占到市场销量的80%左右,“尼桑”算是进口高档轿车中卖得最好的了,6月的前半个月出了30辆。这位小姐称,由于“亚运村”的进口车销量已占全北京市的一半以上,“尽管今年以来国家集中打击了轿车走私,但尤其是最近这一两个月,进口中高档汽车在普遍熊市中尤为萎靡不振几乎是肯定的”。上海福特“别克”和广东本田“雅阁”未雨绸缪的宣传攻势曾使它们在6月上市前就一度被传脱销,但事实上,至少在北京,这两款新式“中外合璧”的高档轿车闻者甚多,而问津者少之又少。来自汽车工业协会的信息表明,今年国内汽车销量大幅锐减,主要原因是公费购车遭到控制和百姓持币观望。
对名车的热望和车市上的踌躇不前,再明确不过地反映着人们对迫在眉睫的WTO的期待。在上海车展流传的一条消息颇具代表性:一辆现价34.8万元人民币的别克汽车在美国的售价是2万美元,在日本,雅阁轿车的价格相当于1.8万美元,而在广东,则要人民币29.8万。据有关部门今年初预计,到2000年,中国具有购车能力的家庭将达800万~1000万户。“
由于私人购车已经不可逆转地占据轿车销量的60%”,拿买一辆“桑塔纳”的钱等着买本田“雅阁”的持币待购心理“延迟着”新富者们的购车计划。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展公司的一份市场研究报告称,“轿车市场昔日每年30%的增幅风光不在”,国外厂商可以伺机分割未来的广阔市场,国产车则无疑遭遇“雪上加霜”。国家机械工业局宣布,去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十大汽车生产国,国内轿车产量达到创纪录的65万辆,但车市需求量只有55万辆;今年预计产量可再提高到75万辆,可整个一季度销量不过11.7万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如果找不到买主,平均一小时生产85辆轿车又有什么用呢?中低档轿车尚差强人意,“大哥大”“桑塔纳”一季度销量同比增长了2.98%,“夏利”在“奥拓”和“云雀”大幅度下跌的基础上涨了22.14%,“富康”倒是一跃窜升为车市“老二”,但它也不是胜利者,一季度的销量仅完成了全年计划的14.14%,这可不是一个吉利的数字。中高档轿车更惨,“红旗”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7.19%,“奥迪”的王牌C3V6也降了76.12%,“富康”推出的三厢988货源充足,却基本上都堆在厂区库房和露天市场里。亚运村汽车市场的一位姓季的经销商笑着说:“在这个时候大规模推出高价车,中国的厂商显然还没有真正做好入关的准备。”
至少在那些“婆婆”和“皇帝的女儿”看来,现在最紧要的事情是辟谣。国家机械总局行业规划司的官员们再三向记者强调,进了WTO,轿车价格也不会有多大的调整,进口关税即使真的要从现在的80%~100%降到25%左右,也需要5~6年时间,第一年的降幅不会超过5%。或许是想用事实说话,5月以来,进口轿车的价格被突然抬高,普遍上升1万元左右。各类受购车者欢迎的报纸媒体也开始劝告消费者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该出手时就出手”,因为“汽车是财政利税大户,既是支柱产业又是幼稚工业,国家必将千方百计保护这个关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业”。
“除非国家给每一个耕作的农民发工资”
与“幼稚”的汽车工业相比,农业似乎已被认为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成熟产业”之一。4月10日,通宵达旦谈判的中美外贸官员们就中国加入WTO一揽子协议中的重要部分《中美农业合作协议》达成一致。据新华社通稿称,中国在小麦TCK黑穗病问题上作了重大让步,允许美国西北七州向中国出口小麦,中国还解除了对美国包括加利福尼亚在内的四个州向中国出口柑橘的限制。
由于官方迄今为止仍未公布协议的具体内容,因此可以预料的巨大争议仅仅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而且全部是在与农民毫无关系的城市知识界中间展开。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和天择经济研究中心曾召集国内一批知名经济学家讨论这个协议及农产品市场开放问题,结果没有哪两位专家持完全相同的观点。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卢峰教授对《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几乎是举双手赞成,他认为,这个协议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动植物检疫方面的协议,中国从1972年开始禁止美国TCK小麦进口,但经过科学测定,TCK小麦经过加工处理后对人畜都不构成危害,而且TCK病在我国不存在气候生长条件。中国已决定在海南建立TCK小麦的处理加工厂,TCK病通过贸易方式传入危害中国小麦的可能性很小。加州柑橘可能传播“地中海果蝇”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提高检疫手段解决。卢峰指出,从美方利益来说,中方的让步确实足够重大;而从中国的利益来看,这一让步本身并不要求支付特别大的额外成本和代价,并不会立即或直接给我国粮食生产造成压力,“也不会对农民收入产生显著影响”。卢峰说,农业上的让步客观上解开了长期以来两国贸易分歧的死结,降低了其他领域入关的门槛,“这样一个双赢的结果,不仅内容积极有利,而且在贸易谈判策略和技巧运用上也可圈可点”。
然而,像卢峰这么乐观的看法并不太多。温铁军——国家农业部农业研究中心最著名的青年学者——就认为,“我们不应该忘记近代史上美国农产品依托‘美麦贷款’和‘美棉贷款’大举进军中国、把我国的小农经济打得一败涂地的教训。”这位曾精辟地提出“中国的发展是自我资源资本化”论点的经济学家警告说。
对农产品开放,温铁军从积极方面的评价是:“对城市消费者显然是有利的。国内的小麦80%是低面筋度的软质小麦,结果面包一切就掉渣,挂面下锅容易烂,大量进口美国硬质小麦可以解决这些消费品质上的问题。它可能还会迫使一部分土地资源短缺的地区调整农业结构,比如中国的水产品、蔬菜和一部分畜牧产品这些非基本农产品还是有一定出口竞争力的。最后,开放会促进中国正在进行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90年代初以前,中国是以农产品的低价保护工业,因此低价的农产品本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但在1994年,为了在农业比较效益低的情况下以价格隐含的补贴稳定农民的粮食生产和收入,国家大幅度调高农产品收购保护价。到1996年,提价幅度达到105%,国内粮食价格开始全面超过天花板价格(国际市场价格),而且收购价甚至高于国内市场价。“以玉米为例,今年3月份国内市场平均价格1.44元/公斤;而美国芝加哥的期货市场平均价格折合人民币仅0.72元/公斤。即使考虑运费,中美粮食差价仍然悬殊,如果再加上品质上的差距,不难想象,美国(加上加、澳及欧洲粮食出口大国)将很容易地占领国内市场。”
卢峰教授不认为扩大配额和关税的降低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中国在进入WTO初期,粮食进口配额要上升到1500万吨,“1995年中国就曾进口过2000万吨粮食,当时就并没有对粮食生产造成多大的冲击,”卢峰道,“2000万吨粮食只占中国总产量的4%,会给粮食价格和生产带来什么问题呢?”
社科院经济所的盛洪说的更专业一些,“价格是由边际决定的,而不由平均决定,饱和之后较小的进口量,也可能导致价格的很大变化。”他认为,中国入关后的粮价肯定是由美国的价格来决定,因此,“中国农民可能会把粮食生产成倍削减,而不仅仅是2000万吨。除非国家给每一个耕作的农民发工资。”
农村,中国改革承受力最大的载体
在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今天,再讨论是否应该入关、是否应该开放的观念问题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但入关确实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过度膨胀、就业问题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应该以何种姿态加入以资本大国制定的游戏规则来保护资本对全世界统治利益的WTO?至少我们应该开放哪些行业,保护哪些真正关乎国家利益的领域,开放之后的利弊究竟如何,本来就是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应该认真和广泛加以讨论的问题。
据美国高盛亚洲研究部最近的模拟测算,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贸易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的增加,对我国GDP每年的潜在贡献为0.5%~0.6%。国内另一个更为乐观的说法是,入关可望使GDP净增两个百分点。劳动及社会保障部估计,中国的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以影响750万人就业。对就业压力越来越沉重的中国来说,不管是170万还是700万的就业机会,都肯定是很具吸引力的砝码。然而,这些数字中可能包括多少离开土地的农民呢?回答无疑是悲观的,因为到下个世纪初,中国仅城市劳动力剩余就将达到4000万左右。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已超过2亿,而据一般的估计,国内粮食市场被分割的缩小,将可能再挤出2000万农民。
“一旦放开,对其他行业都是利弊兼有,惟有农业的市场开放对9亿农民尤其是耕作传统农作物的农民基本是只有弊而享受不到利益,将直接导致他们的收入下降。”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袁钢明博士说。
袁钢明前不久曾到河南东部的夏邑县调研,那是一个在中西部属中等发展程度的平原县,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1800元左右,其中1000元来源于粮食,种一亩地按现行国家收购价可收入100元,其余800元主要是养猪和其他家禽,养一头猪的收益也在100元左右。但今年1月以来,全国生猪价格狂跌40%以上,由于农民不赔不赚的生猪收购价格应在每公斤5.5元上下,而目前实际已跌至3.2元,每养一头猪亏本100~150元左右,许多农户为减轻负担开始宰杀猪崽。
农民生存的艰辛使袁钢明心中的忧虑更为深重。“中国的粮食生产与价格实际上不是一个市场贸易的问题,而是一种收入分配的人为调节,或者说不能简单当作一种生产性的产业,而应该看作一种为了保障9亿农民基本生存的公益事业。国家设立的较高的粮食收购保护价,实际上是在不承担农民社会保障的情况下,给农民支付的某种补贴,也是国家为保护工业免受农业过剩人口和小工业的冲击,将农民留在土地上的一种有效措施。”袁钢明因此认为,粮价倒挂是完全正确的,他介绍说,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在工业化时期都遇到过按照比较效率来说放弃农业才划算的情况,但他们无一例外地用提高粮食价格保护农民收入。日本本来是一个粮食进口大国,但为了维护本国农民稳定的生活结构,他们向进口的粮食征收700%的关税。
袁钢明当然明白,“在许多人看来,中国需要保护的行业好像越来越多,没有认识到农业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劣势。他们正好弄错了,事实上,除了农业——或许还有金融业,我看不出任何一个行业有充分的理由应受到保护。”
“在越来越多的制造行业,中国对美国的竞争优势正越来越明显,”袁钢明通过对1997年中国出口情况的研究发现,当年出口额最多的不是一般认为的棉纺织品,而是半导体,其次是电池。袁钢明因此指出,中国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的出口竞争能力将越来越低于其余的工业产品,“尤其是那些普及的、技术已成熟的制造业,中国很快就会占据优势,10年前谁会想到中国能大量出口彩电和冰箱呢?汽车也是这样,尤其是中低档轿车,别看他们成天叫苦不迭,一开放生产成本马上就能降下来,用不了多久中国就能凭借劳动力优势占领国内、开进国际市场。高档汽车中国可能还会暂时处于劣势,但不开放就永远跟不上国际潮流,永远不能提高技术含量,永远幼稚。”
“私营企业家有工商联作为他们的社会压力集团,汽车和电信企业的意见也总是能得到听取。”袁钢明笑着说,“对自己的处境没有充分了解的农民却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代表,即使是我说的可能有失片面,也算是替这些没有‘议价能力’的弱势人群说了说话。”
这当然可以看作是一句笑话。然而,入关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它毕竟涉及众多的受益和牺牲,理应由各种有着独立利益的社会群体充分而广泛地“博弈”。这其中要有金融、汽车,还要有官员和农民。毕竟,计划和市场本身都不能给这个经济的社会带来公平的结果,让弱势者继续承受那一份牺牲和代价无论如何不是公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