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82)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胡伦 孟湄 施武 老乐)
怎么搞一台晚会
文 胡伦 图 王焱
肖斯塔科维奇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写出了他的《第七交响曲》。据说,红军战士听完这首曲子的转播之后勇气倍增,终于把围城的德国鬼子打败了。前两天看到一个纪录片,正是讲这段历史,列宁格勒一片备战景象,电台播音员说,为了保证《第七交响曲》的现场演出,红军各战斗单位要压制住德军的炮火,不许德国鬼子破坏艺术。
看完这段纪录片,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如果哪天我们也遭受外国鬼子的围困,我们恐怕会搞一台晚会,战士与民兵看完了晚会之后,就跑出城去杀鬼子,要是战胜了敌人,则说明我们的晚会是成功的。
我们的晚会总喜欢请几个外国人上台表演,他们说汉语的流利程度远比我辈说英语的流利程度为高,这似乎说明,某些洋人已臣服于我泱泱大国的文化传统—他们学相声,学京剧,尽管这两种玩艺中国人已经不大爱学了。
晚会中另一项不可或缺的玩艺是小品,但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戏剧,也不要把它当成是生活,因为小品演员最重要的基本功是装傻,他们总要降低自己的智商来逗观众发笑。这让我联想到另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化不太注意培养同情心,一个正常人看到一个智力障碍者就要笑,这是不对的,他看到智力障碍者时应该有那么一点儿同情心。
然而,一台晚会中最让你受不了的是虚假,你看不出为什么那么多现场观众会为某个节目、某项法规的出台、某个演员装傻而欣喜若狂。据说,这是导演的要求,他让那些观众忽然间变得不那么正常了,总是笑,总是要鼓掌。也许偶尔还要为某个蓄意安排的细节热泪盈眶一下。
这各种愚蠢的东西在春节期间会达到高峰,只要你打开电视,就会看到一台晚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它鼓舞人们好好活着,跟各种你看到的或看不到的困难斗争。主持人的音调都高扬着—这是我们世俗生活的大礼赞,它预示着世俗生活多么美好,多么了不起。
事实上,虽然每个人都免不了过一种挺世俗的生活,但绝不该堕落到赞美它的地步。当然,如果德国鬼子来了,不让我过庸常生活,我一定去打鬼子,但出发之前我可不想看一台愚蠢的晚会,那还不如死了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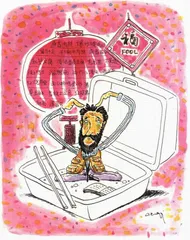
学校作什么用?
文 孟湄
“学校作什么用?”有一本面向父母亲的法国杂志要求孩子回答这个问题。孩子的回答必须用明信片(为的是求简短),并有意外的奖品鼓励。结果得奖孩子的答案是:
马吉越,男孩,9岁:为了每得一个好分数能得10法郎(相当14块人民币)。
瓦郎丹,男孩,7岁:为了当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卓尔丹,男孩,4岁:为了让我在妈妈离开的时候哭鼻子。
曼侬,女孩,6岁:为了让我喜欢放假。
罗曼,男孩,6岁:为了有我的朋友。
法比安,男孩,6岁:为了学会自己一个人给圣诞老人写信。
曼侬,女孩,4岁半:为了能每天看到我的小情人。
欧罗尔,女孩,10岁:为了让家长们玩儿的时候有人管孩子。
奖品:一只款式很酷的小学生手表,价格499法郎,设计师的名字,保证期,下水可到多少米,赞助商等等,都有说明。广告做得礼貌得体:用小三号的字体微乎其微地介绍销售点的电话,不像我们常见的广告,首当其冲喧宾夺主铜气熏天。
这杂志怎么就那么聪明:说是给你们作父母读的,读的时候孩子们要是来吵你,或者你想和孩子分享一会儿工夫,那你们就可以跟孩子一起做这个答题,正好有奖品可以刺激孩子,省得你没有招儿逗他们。而且正儿八经的书呆子式的回答人家不稀罕不鼓励,专喜欢那些最嘎的,最逗人的,最是孩子味儿的,给他们堂而皇之地赠送奖品。
我一定是个很痴的母亲。这类的问题和答题,我经常会在灯下傻傻地读上不止一遍,哈哈地大笑不止一遍,把自己的孩子读的时候爆发的笑声甜甜地咂摸不止一遍。有时候还会偏去琢磨孩子回答中所包含的哲学,杂志编这种问题的时候给父母们的提问。
唉!忘了谁说过:要活很久才能够年轻。
孩子,真好!
作父母,真是门儿艺术!
“最好”的东西
施武
“最好”的东西是“好”东西的最大敌人。这是我家老公信奉的格言。如果我收拾房间刷锅洗碗的时间超出他所能容忍的时间,如果我嫌他衣服脏催他换,他又一时犯懒,他差不多都要表达这层意思。
最初一次是我在收拾厨房时决心把炒菜锅彻底光亮,结果我用了半筒五洁粉,五个铁纱圈,半天的时间,最后还是把那个锅扔了,重新买了一个不粘锅。虽说是不粘锅,可我还是怕它免不了年深日久粘一锅黑嘎巴,尽量避免炒那种浓汁浓味的菜。吃了一段时间的清食淡菜之后,老公说:“咱们家的锅真干净”,我以为他在夸我,接着他又说:“去外边吧。”不约而同地,我们都点了最浓味的菜。此后,我们经常一感到嘴馋就到馆子去吃,直到我们家附近的几个馆子的人和我们都很熟了,我越来越不自在,总觉得我们家好像没厨房似的。幡然悔悟似的,我们的厨房又恢复了烟雾腾腾的菜香味儿。大不了,等锅粘了一身刷不掉的嘎巴儿再换一个。老公为我们得以从锅的专制下解放出来而高兴无比。
去年我们家铺了新地板,我自然比以前在意一些,擦地的次数多一点。也考虑能否让人进门换换鞋,老公反对,理由是反正三天两头擦地,也不用在乎鞋底那点土。可是,我们家有个能制造,混不懂整理的5岁孩子,吃饭喝水少不了滴汤漏水,不断地从外面往家捡着破石头、乱草叶,玩水更是天性。水点和鞋底土一混合,可想而知那地板是什么样。有那么几天,我差不多像职业清洁工,终日拿着拖把,腰没直过。你道这是什么,这是最干净的地板造成的地板专政。终于爆发了场大战:我和女儿的大战,以“不许”二字为战旗。“不许”说得多了。女儿大概不知道“许”什么了,可她不是善罢干休之辈,给我制造出更大的麻烦,处处与我作对。我的家里整日喊叫声不绝于耳,老公参战,等于挑明了女儿的疑问:这家里“许”什么?他说他宁可把地板掀掉,恢复田园诗般的水泥地。并且提醒我在“锅”的专制下我们失去了厨房,现在地板的专制快让我们失去家了。
算我错了,现在无论家里多乱多脏,我一天只整理一次,并且绝不求彻底。
但人总想把事情做好一点儿,再好一点,总在某些最在乎的事情上求最好的境界,至少是自己心中的最好。尽管我有过教训,那也会时不时偏执起来。每当这时,老公就搬出他的格言,说一个有强制能力的国家都有一定比例的犯罪率,如果把所有的小偷小摸都判死刑,那世界倒是干净了,但是到那时候,衣服不干净,说句脏话就成了要判三五年的罪了,到了这些也要判死罪时,那连抠鼻涕也不行了。我不知道他这是从哪位思想家那儿搬来的理论,不能说没道理。但是当我从他的枕头下面发现了一堆干鼻涕嘎巴儿时,我们家又开始讨论“犯罪率”到底应保持在什么程度才算好。
(本栏编辑:苗炜)
熊猫老师
老乐
“熊猫老师”是我们给他起的外号,他给自己起的别号是“竹神宫主”。这么称呼自己是因为他自信自己的竹子画得最好。虽然在我们看来他的竹子实在没有什么特别,而且“宫主”两字总让我们联想起“公主”,但他那些书画界的同行却似乎觉得这个别号很名副其实。
有一次他在自己画的一丛竹子下加画了两只熊猫。那丛竹子倒和他平时画的没什么不同,只是那两只熊猫太难看了。从此他就有了“熊猫老师”的外号。
“熊猫老师”是我上大学时参加的“书画社”的辅导老师。实际上他辅导不了我们什么。我们当中没多少人喜欢画竹子,而“熊猫老师”只画竹子。因此他更多的时候只是躲在自己的画室里拼命画竹子。在我上大学期间,他完成的最得意作品是一幅两三米长的巨作。画上密密麻麻地堆满了竹子,而这幅画的最特别之处在于“熊猫老师”在这些竹子的竹杆上抄满了历代有关竹子的诗句。
诗歌是“熊猫老师”的另一大爱好。他自己偶尔写诗,风格和他笔下的熊猫一样有个性。他更喜欢的是朗诵诗。那时我们这些人都知道,千万不要和他谈与诗有关的事,否则他会拉住你聊个没完,而且最后肯定要朗诵他那个“保留节目”—长诗《奉献》。
这首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破诗,在“熊猫老师”的努力下在校园里尽人皆知。其中一种宣传途径是这样的:除画画外“熊猫老师”还负责学校里许多杂务,其中就包括每年去火车站接新生。“熊猫老师”相信自己负有进行入学教育的重任,于是每次在从火车站回来的车上都要朗诵一遍《奉献》。
我不清楚“熊猫老师”是否知道我们对他的竹子和《奉献》不感兴趣,反正他总是一丝不苟地完成着自己“传道授业解感”的任务。有一次他负责给我们年级上有关中国传统美德的修养课,一进电教室的门我们就被那阵势吓住了。“熊猫老师”把他的讲稿工工整整地抄在20多张整开的大纸上,然后把它们挂满了一墙。上课后他又变出了一根竹竿似的教鞭,讲到哪儿指到哪儿。虽然他很少看墙上的文字,但据我们观察他背得一字不差。
下课后我们几个人留下帮他收拾场地。当他把那些大纸一张张摘下,再一张张仔细卷好时,他脸上的表情很是失落。那时看着他我就很好奇地幻想他在那个著名的夜晚脸上可能的表情。那天晚上中国足球队又像往常一样输了球,往常不爱闹事的我们学校男生突然按捺不住了,于是开始从宿舍楼窗子里往外扔椅子、扫帚。“熊猫老师”虽然已过40岁但仍单身住在男生宿舍一层。骚乱开始后他看不过去就打开窗朝楼上训了几句话,结果被另一阵椅子、扫帚压了回去。当时我不在场,不知道那天他是否又朗诵了《奉献》。
不过,说来奇怪,毕业之后我很少想起我们学校那些名教授,反倒记住了这位“熊猫老师”。但有一件事一直让我觉得惭愧:听“熊猫老师”朗诵了4年《奉献》,至今我连其中半句也背不出来。 熊猫电视奉献大熊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