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在游泳的修道士》到《艾奇逊》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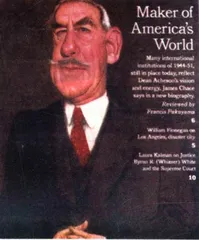
武夫从本期的上榜书来看,只有两部可以做些简要说明。一部是《正在游泳的修道士》,其作者马拉齐·麦库特(Malachy McCourt)是《安吉拉的桉树》一书作者弗兰克·麦库特(Frank McCourt)之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正在游泳的修道士》可以说是《安吉拉的桉树》的续篇。因为书中所写,是这位作家兼演员1952年抵达美国之后的事情,记叙了他如何从身无一文的年仅20的爱尔兰移民成为演员和节目主持人、酒吧老板和剧作家的经历。书中虽然也涉及他青少年时代成长时所受到的爱尔兰文化的影响,但主要讲他如何在纽约谋生和奋斗的生涯,从时间和内容上看,与《安吉拉的桉树》是连续的。既然《安吉拉的桉树》上榜已逾百周,这部略嫌粗俗,但终不失幽默的续篇得以畅销,也就不足为怪了。马拉齐诚然不是修道士,但这种写法主要想突出比较正统和保守的天主教徒如何适应美国这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
另一部是《市民军人》,作者是斯蒂芬·E·安勃罗斯(Stephen E.Ambrose),书中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从诺曼底登陆到德国法西斯投降中的事情。众所周知,二战时美国虽然参战较晚,但也称得起“全民动员”,许多过惯了城市生活的中产阶级青年投身战场。由于他们平时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标准和习惯,首先为后勤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说,每个美国兵身后,要有一卡车的辎重来供应他们战斗外之所需(包括图书,据美国一部图书馆史的专著所载,美国官方要求“美军官兵无论驻在何地都不得缺乏提高士气的读物”,单单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两条运书线,就在短时间内征得了1700万册的图书,运往前线)。这些美国大兵为了适应战争环境,自然吃了不少苦头,也闹出了不少笑话。从心理上说,美国中产阶级的自满自足,是美国在二战初期采取“孤立主义”政策的基础,让这些满足于个人及家庭小天地的人去为反法西斯而战,其心理转变、考验和承受力也是深刻的。
该书作者安勃罗斯先生看来是专事二战欧洲战争后期研究的。我们在8月23日《书评》的简装本畅销书榜上的第16位,看到了他的另一部著作:《D日:1944年6月6日》(D-Day,June 6,1944)就是一部记述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纪实文学作品。
另外一部虽未上榜但值得一阅的新书是詹姆斯·柴斯(James Chace)所著的《艾奇逊》(Acheson)。狄恩·艾奇逊这个名字,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或许并不熟悉,但对50年代初抗美援朝时已经上小学的人来说,却是难忘的。他那张留着一撮上唇胡的长脸,经常出现在当时报刊的漫画上。他和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以及杜勒斯所制订的一系列美国对外政策,如冷战及反华等等,不仅当年确立了世界政治地图,而且至今仍对国际风云、中美关系等影响深远。
只消看一看艾奇逊的任职和政绩就颇能说明问题了:1944年他担任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时出席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即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成立了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会;在任副国务卿时监督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财务执行状况;在任国务卿时谈判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支持参与朝鲜战争,还推进了美日安全条约……如该书副标题所称,是“建立了美国化世界的国务卿”。当今的北约东扩、南北朝鲜对峙等等重大国际问题,都与当年美国的外交决策有关。
艾奇逊当时执行的政策后来遭到许多批评:一是花钱太多,如拨款4亿美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欧洲战后重建,尤其是资助德国和日本恢复国力;二是主张冷战外交,不但在50年代造成朝鲜战争,60年代在越南不宣而战,而且还有东西方的大量冲突和麻烦。但也有人认为,根据1991年以来公布的前苏联同一时期的内部决策档案来看,二战后的冷战对峙非美国和西方单方面的责任。评家指出,这部《艾奇逊》中没有使用前苏联方面的材料,未免失之片面。当然,无论怎样支持艾奇逊的政策,也没人主张那种反共反苏的外交应该成为麦卡锡高压政策在国内肆虐的借口——那段令人谈虎色变的时期,实在为美国历史上所罕见,至今为美国人所不齿。
除去资料不新不全之外,该书还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深入内心的洞察力不足。书中当然没有忽略狄恩·艾奇逊的家世和性格,并且确实指出了他的廉洁和自信是他成功的关键,也介绍了他的父母。他父亲是美国主教派教会的主教,对他的成长不够关心,对他的抉择很少支持。而他的性格主要继承了母亲的独立头脑。书中也没有否认他这种个性的弱点:时常拒绝他人的意见,甚至与朋友反目。但与艾奇逊本人所撰的回忆录《晨与午》(Morning and Noon)和《创造中的礼物》(Present at the Creation)相比,内在的探索就欠深刻了。
虽然艾奇逊辞政后即不再抛头露面,但从客观上说,他在美国外交上决策者的重要地位,只有后来的基辛格可与之相比。如果抛开他们不同的对华政策在我们中国人心理上的不同反响,这个人物倒是值得研究的。
为杜拉斯梦幻般真实的一生立传
(刘芳)
法国人9月休假归来,暂时没有为畅销书榜添加新作。图书市场值得一提的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传记今夏出版,引起文学界极大关注。
杜拉斯是个令人吃惊的女人,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都从未停止过一级级攀登文学殿堂的台阶。她说过自己只精通一件事情:写作以及聆听词句那特有的声音。她能像艺术家穿起珍珠那样完美表达出她感受到的一切。她一生的作品总计有40余部小说,10余部戏剧和电影,其中《情人》(1984年)和《中国北方的情人》(1991年)最负盛名,既讲出了生命无以复加的享乐和痛苦,也讲出了她本人无休无止的写作欲望。
但是文学界人士都知道,玛格丽特·杜拉斯从不授权别人谈论玛格丽特·杜拉斯。她总是先把什么都说出来,接着又把什么都否定掉,让立传者根本无从落笔。“我的生命没有中心,没有路线,没有故事,”她对每一个采访者都这样说。她像王者赐言一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不说就不说,突然打住是她的一贯风格。这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她知道自己才是真正的“作家”。
为了给这样一个人物立传,劳尔·阿德勒首先要充分了解她,并且赢得她的信任,以他的话说,是“在浪涛之中穿越杜拉斯的假面”。他每周与她谈一次话,还经常因杜拉斯的失忆症和其他病症而中断;他钻研了杜拉斯的每一部著作;去了一趟越南找证人找感觉;还查阅了几公斤未曾公开的档案卷宗……6年艰苦的工作凝成了今日这部600页的大作。
劳尔·阿德勒本人对这部传记的评价是“真真假假搅在一起,像一杯浓烈的鸡尾酒”,他劝人一口饮尽,“这样才挡得住那冲劲儿”。玛格丽特·杜拉斯确实度过了梦幻般的一生,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感觉我是一个梦游的人,我的生命是一个影子的生命,我仿佛失去了重力,脱离了大地的束缚,在空气中行走。如果光线穿破这黑暗,我就可能掉下去。”劳尔·阿德勒看到了这段话,并把它用在了传记里。梦幻就是杜拉斯的真实,阿德勒写道,杜拉斯一生可让人接近的真实之处就是她同时是正面和反面。 杜拉斯军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