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爱情》:沉重的担子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卞智洪)

7月30日,广电总局电影事业管理局签发了《冬日爱情》的影片公映许可证,这部1996年冬即在大连开拍的影片有望年内面市。与其他完全在体制外擅自制作的“地下电影”不同,《冬》片本属国家正式出品影片,后因未经批准私制拷贝,擅自参加国际电影节而受到电影局查处。近一年的修改和等待之后,影片重新浮出海面,导演阿年不禁长嘘一口气。
90年代的大连,录音师马洪与“傍大款”的刘嘉英相爱,拒绝了来城市寻找他的女孩段爱。大款要买下马洪的歌曲,令马洪很苦恼,他请刘嘉英和他一起离开,刘拒绝了,理由是他不给人安全感。与此同时,影片以1/3的篇幅插叙了从60年代回溯到20年代间,马洪祖父母的一段坚贞爱情。最后,梦境中马洪与刘嘉英站在俯瞰城市的高地上,当他们相拥时,流畅自然、带有一分怀旧情绪的歌声响起:“我不知该怎样拥有你/我不知道你是否真的美丽……我没想过要娶你做新娘/但我想娶的人和你一样。”
如果说曾有几部“新生代”电影(如《北京杂种》、《头发乱了》)无意中为90年代初的摇滚乐队作传的话,《冬日爱情》则像90年代中期城市民谣的大MTV。前者是城市土著青年的压抑与烦躁,后者描摹了城市外来青年的漂游状态。对历史与现实的共同关照是《冬》片的独特之处,它意味着创作者力图摆脱肤浅的状态描写,而进行一些形而上的思考。阿年说:“和祖父母的伟大爱情相对照,我想刻画当代都市人生活与情感的不确定性。”
1987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的阿年同样被归入“第六代”、“新生代”导演或者“60年代生电影人”之类称谓中。从《冬日爱情》恰好可以看到这一批新导演的普遍困境。一是由于违规制作或题材等原因,相当一批作品难以寻找到正常流通渠道,二是制片体系的不健全,很多导演既要做制片人(寻找投资、组织制作、控制方向),又要做导演以实现个人的想法。这副当爹又当妈的重担至今没有减轻多少,阿年的体会:“往往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三是不少年轻电影导演讲故事的能力并不成熟。与上一代相比他们多自己编剧,而这些故事鲜能善始善终并引人入胜。阿年自己坦言,可能因为生活经验不足,影片的人文叙事仍嫌单薄。
即使不是泾渭分明,近年来的中国电影也大体可分为主旋律电影、商业片和探索片。商业片以票房为检验标准,而探索片如果有外在目标的话就是在国际电影节上拿奖,二者的目的和形态既不相同,对中国电影的促进也完全从两个角度。1995年的《巫山云雨》(章明)是“新生代”导演最出色的影片之一,也颇能和国际上的艺术电影接轨,但国内公映时却票房寥寥。电影人对自己的定位——想做什么,能做什么——显然是至关重要的,然后就是:你有没有达到你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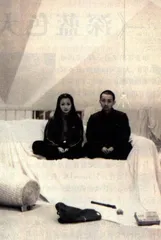
面对面,不确定的爱和不重要的爱
1990~1995年间似乎都在拍探索电影的“新生代”导演今天已分流到三类电影之中。阿年是一位矢志做艺术电影的导演,他认为艺术电影是一口井,挖得越深越好票房本属商业电影那口井,但水流有时也会相通——艺术电影获得不菲的票房。
因此事情还远没有完结,阿年要为《冬日爱情》找发行商,要筹拍他的下一部影片,要重新思考电影的叙事,……和几乎所有热爱电影的年轻导演一样。 影视电影电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