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明信片:上城,下城
作者:娜斯(文 / 娜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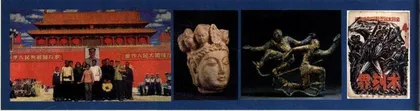
2月6日 古根海姆美术馆“中华文明五千年”大展开幕
刚还是写意、工笔,转眼之间,变成色调低晦的现代西画,再一转眼,满室满目的金光灿烂,革命辉煌——这是古根海姆美术馆的“中华文明五千年”大展。
古根海姆美术馆显然跟大都会博物馆前年的“中华瑰宝”展比高低。大都会固然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招牌,古根海姆也有它的特色。其一,台北故宫博物院虽然搬去了不少宝贝,毕竟是皇家收藏。中华文明在地域上的广阔性,1949年后大陆还不断有东西挖出来等等,都是只有与大陆博物馆合作才能领略到的;其二,古根海姆有上城、下城两个分馆,位于苏菏区的下城分馆,专营当代前卫艺术,是大都会所没有的。此次中国美术展上城展古代,下城展当代,可以说是古根海姆独家专利,也可说是中国百年来的现当代美术第一次在美国如此大规模露面。至于古根海姆缺陷的地方,是它本是以西方艺术为主要方向的美术馆,近年来随着在海外不断建立分馆(威尼斯、柏林、Bilbao)才开始向国际化迈进。它不像大都会博物馆有专门的中国部,办起这样的展览来手忙脚乱,不知所以。不过古根海姆雄心勃勃,这次美展拉来基辛格当名誉委员,请希拉里出席开幕式,衣香鬓影,人头攒动,是纽约今年最重头大展。
“中华文明五千年”吸引人的是其在时间和地域上的跨度之辽阔。500件作品来自中国17个省,云南青铜,北魏佛像,宋明陶瓷……到民初版画,抗战木刻,1949年以后的革命颂歌……去年,《时代》杂志的美评人Robert Hughes为公共电视台制作了一个美国艺术史系列片《美国视野》(American Vision),从美国艺术阅读美国心史。观看古根海姆下城1850年起的近现代部分,尤感艺术与时代之关联。150年来一个古老文明向现代过渡中的种种沧桑动荡,一览无余—尽管举办者安排、选材有很多混乱之处。
在纽约看那些“万山红遍”的革命油画,真有点置身什么“装置艺术”之中的感觉,而1949年前庞薰琹、徐悲鸿等人的现代西洋画风与之形成的鲜明对比,也让人无法不感受革命力量之无穷。齐白石、吴昌硕、傅抱石泼黑写意的同时,也有民初小报,比如—连环画连画带讲一个苏州男人曹名妓拒绝,趁其熟睡将其辫子剪下偷走—这是那时的花边新闻了。
“东方主义”的问题是把东方固定化。这个美展的突出贡献是,它既有历史,也有现代,有一个文明的来处,也有它的变化。当然,原计划的当代前卫部分,如政治波普,装置等不能实现,使其打了折扣。
古根海姆配合其美展还于4月份举办中国早期电影展。古根海姆美展开幕的同时,还有一个与其无关的中国1949年后电影展,但主办单位不专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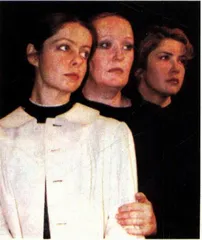
2月21日 《三姐妹》—莫斯科艺术剧院建院百年纽约专演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不仅在中国表演界大名鼎鼎,在美国也有很多徒子徒孙。100年前创立的莫斯科艺术剧院,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诞生地,也是与契诃夫剧作连在一起的名字。它被视为现代剧院的鼻祖,对全世界话剧艺术都有影响。1922年它第一次来美演出,号称在美国戏剧界引起了革命。美国最有名的表演教师李斯特拉斯堡就是看了其演出而创立自己的剧院,后来发展成“表演工作室”的(表演工作室是美国方法派演技大本营,数代戏剧和电影名演员都由此而来)。
契诃夫剧作是英美舞台上的经典作品。仅《三姐妹》去年纽约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百老汇传统版本,一个是外百老汇的小剧场实验版本。前者由几个好莱坞女星出演,但评论不佳。我看到的是后者,在形式上有大胆的新诠释。第一幕按传统形式,第二、三、四幕时间后移,移到契诃夫人物常提到的“未来”(我们已目睹到的现实),并以表现主义、哑剧等手法演出。这个版本反映不错,因我觉得它的形式探索与其内容表现非常吻合,保留了契诃夫剧作的抒情性,也有“当代化”了的新意味。
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是传统手法—在剧尾也加了一点抽象。我的感想是在剧之外—老见《生活》杂志上讨论话剧的问题,这些经典名剧为何在国内少见上演?去年看《玩偶之家》,也有同样想法。这部五四时代就传入中国,在中国现代史上鼎鼎大名的戏为什么得到百老汇才能看到?即使是中文经典,公演的机会也太少。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先锋、俗人,都让我觉得空。
2月25日无线电城格莱美奖颁奖典礼
一个朋友在E-mail上说:“见格莱美奖上不断冒出鲍伯·迪伦、保罗·麦卡特尼、艾尔顿·庄的名字,我几乎以为我是置身侏罗纪公园和一帮恐龙待在一块呢”我回复说:“嘿,我彻底反对你关于流行音乐……或者任何事物,恐怕……的进化论观点,难道你真听‘辣妹’不成?”这位朋友忙解释说,他想说的是近年新出现予人印象深刻的摇滚乐男乐手不多,好的都是女的。Smashing Pumpkins,Phish,和Creen Day似乎有希望,可也出道好些年了。他根本不认为辣妹是“musician”云云。
的确,今年格莱美年度最佳专辑提名,5位之中60年代的老将占了两位—鲍伯·迪伦的《Time out of Mind》和保罗·麦卡特尼的《Flaming Pic》,其他3位则是Babyface(黑人),Paula Cole(女歌手),Ra-diohead(另类音乐)。而且,这几年格莱美获奖新人和年度专辑奖也多是女歌手,如今年的Shawn Colvin(桑尼回家Sunny CaJne Home) .Paula Cole (This fire)。
当然,说男性新人少,指的是摇滚乐方面。摇滚乐的形象一直是白人男孩,然而90年代好像不是白人男孩的时代,或不仅仅是白人男孩的时代。黑人的rap热火朝天,受南美影响的hip - hop是最时髦流行的俱乐部音乐,写词作曲的女乐手越来越多—郊区白人男孩不再是独领风骚者:是不是他们一时找不到新的identity?总之,反而是老男孩们还在不断“开拓自我”,除了鲍伯·迪伦和保罗·麦卡特尼,Paulsimon还在那里大玩南美音乐,晚些的U2,Sting,Bruce Springsteen也仍有引人注目之作。
难怪《侏罗纪公园》大行其道。我就最愿意承认,我是最不可救药的恐龙爱好者,从“披头士”到崔健。有一位朋友加入讨论,更邪乎:“进化是对常者而言的。”
3月3日 麦当娜推出四年来的第一张新专辑《Ray of Light》
忽然之间,麦当娜的新形象布满唱片店橱窗。
麦当娜被学院派称为是“性、资本主义和名人文化”(sex,capitalism and celebrity culture)的现身说法。也许该叫她做“西方不败”?因为她的本领是不断重新发掘自己,每每出手不凡,总能在新潮还在最最新潮的时候身体力行,将之主流化。华尔街经济高峰的80年代,她是“物质女郎”( material girl),浓涂艳抹,浅金乱发,内衣外穿。90年代,黑人文化在流行风中越来越“酷”,她在音乐内外都与黑人大谈恋爱。迈阿密受拉丁音乐影响的俱乐部文化越来越火,她在迈阿密安家,还跟女同性恋者出出入人。不过,进入90年代后,麦当娜好像一时找不着北。尤其90年代初的《Erotica》、《Sex》—她本来就是以“性”起家,裸体写真集还有什么新鲜?而且80年代未经济退潮,90年代初是一派“大醉初醒”之感,没人需要过分的折腾了。麦当娜却没领悟,演的电影仍以情色为号召,既不叫好,又不叫座。
终于,麦当娜也明白了80年代已是昨日黄花。她在1996年摇身一变,出演《艾薇塔》,在电影圈总算有了翻身之日,又做起母亲,一下子,“物质女郎”成了成熟女性。今次新专辑,是其4年来的第一张专辑,结果是“物质女郎”转向精神探索,且前所未有地获得好评—大多评论都认为这是她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麦当娜的音乐、歌艺本身一直让人无法恭维,《艾薇塔》重新拜师学艺后,声音倒是大有长进)。也认为她代表了80年代雅皮一代在90年代充满不确定性的“长大成人”。在青年时代以自我为中心的奋斗现在要面临意义与满足感的问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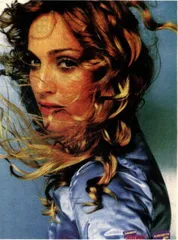
还记得第一次看麦当娜的MTV:一个金发女郎穿紧身泳衣,像上了发条般跳个不停。今日又见电视上的麦当娜MTV:黑衣黑裙黑发,孤寂的沙漠,神秘舒缓的舞姿,祈祷的语句和姿态,空灵的electronica配乐。首支单曲叫《冷若冰霜》(Frozen),手掌心是梵文图腾,手指头有伊斯兰教女人的刺青图案,左腕上有红带子,跟犹太教神秘玄学又有点什么瓜葛。
据说,这张专辑的风格始于她开始练瑜迦。而麦当娜为其“重新再来”找到的音乐出发点是方兴未艾的electronica。“我听了很多electronica和trance音乐(二者都是technol的新发展)”,她说,“它是一张白纸,一种情绪。我觉得你可以通过投注情感,把它提高到另一水准。”事实上,U2和大卫·鲍伊在近来专辑中都探索过引入electronica,但都被评为找不着感觉。麦当娜当然一弄就更主流,且被认为用得比较成功。“她把electronica的形而上感觉与流行乐的共鸣心联系起来了”(《纽约时报》)。化另类(alternative)为流行(pop),仍是麦当娜的拿手好戏。 古根海姆博物馆契诃夫艺术古根海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