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艺术:“首先要让人来看”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卞智洪)

邱志杰《进化的逻辑》
录像艺术至今已有30年的历史,但它的历史和对它的评价一样混乱。录像艺术最初产生于60年代反传统思潮盛行的美国,艺术家受惠于偶发艺术、大地艺术和Fluxus运动的生活化、平民化倾向,提出“录像带属于人民”,企图颠覆和改造大众电视网和艺术市场体制。比如白南准借用十字架、金字塔等宗教符号,用电视机堆起一座座当代文化图腾,无疑是将录像(电视)作为一种媒体批判工具。进入70年代,由大基金会直接资助的媒体艺术中心的出现和博物馆的接纳,促成了对录像艺术内在特性的研究。但被人们习惯地看成是装置艺术的一部分。到90年代,成熟的录像艺术才开始在各种国际艺术大展上频频出现,成为与架上绘画和装置并驾齐驱的艺术媒介。类似比尔·维奥拉、加里·希尔这样的大师,一改前辈以信息社会的传播学或文化理论为依据的唯理色彩,追求现场的戏剧性,深入个人体验和心理的隐秘处,构造出一种独特的超现实主义。
中国的情境与西方截然不同,上述3个时期的关注几乎同时并存于第一代甚至同一个录像艺术家的身上。按照吴美纯的说法:“现在来给中国的录像艺术下定义为时太早。因此我们的展览是包容性的而非选择性的,我们宁愿采取一种拔苗助长的策略。”
张培力的《焦距》是去年杭州展上引人注目的一件作品。他在展台上一排放置了8台电视机,其中第一个画面拍摄了路口的街景和鸣响,第二个画画的图像是在第一个画面上的局部拍摄,这样依次翻拍,到第八个画面时图像已经如同游动的微生物,声音也成为一种难以辨认的尖叫。这个作品因被认为揭示了人的感觉知觉的有限性,触及了媒体技术对现实的过滤与筛选,而获好评。
有的艺术家和美术评论家强调了录像装置中的互动性。邱志杰在《现在进行时》中,用电视屏幕取代了花圈中遗像的位置,屏幕中的一个人以各种方法证明自己活着,然后是一组模拟濒死者目光的主观镜头——濒死者周围亲朋好友的种种表情。花圈中有几簇纸花被微型电视屏幕取代,播放着正不断绽开的鲜花图像。与此同时,旁边另一个花圈中的电视屏幕上是正在观看该作品的观众的正面头像……当观众被提醒转向这个侧面花圈时,他在遗像的位置上看到自己的侧面形象。邱志杰试图使观众成为与录像装置完全处在同一时空中的合作者,从而给观众一种顿悟:生命极其脆弱,死亡就在我们身边,或者勿宁说死与生本是同一过程,而我们都无法面对事实。
也有艺术家对此提出疑义,王功新说,如果说让观众参与作品的完成,这本是装置区别于架上画和雕塑的所在,即它的时间和空间是开放的。如果单纯说互动,那电脑游戏恐怕是最具互动性的了,它只在互动中存在。王功新的作品《婴语》是在一张特制的婴儿床中注入牛奶,投影机将父辈和祖辈逗弄婴儿的表情投映在牛奶循环流动的表面上,嘴部恰对着中央一个小孔,牛奶从那里汩汩流下。三代人意象的转变与不断流动的牛奶的动感构造出一种世事无常又生生绵延的感喟气氛。
由于经费和场地的限制,今年的录像艺术观摩展缺少录像装置,而主要集中在电视平面上,但其中仍不乏比较有趣的作品。艺术家王功新的《玩蛋》展示了老人背在身后的一双手,手里旋转着两只钢质的健身球,健身球上映出周围旋转的、变化的风景。人手、钢球、风景的映像,其质地和本质的对比以及三位一体的旋转使人感知和想象到许多。在邱志杰的《木偶人尼采的权力意志》中,一双人手始终在摆布一具木偶人,这双人手又被从上方伸过来的不时出入画面的另一双人手握着。一位普通观众问邱这是否属于所谓的观念艺术,他否认说:“如果要做观念艺术,那这观念都成成语了,还要艺术表现什么。我想用人手、木偶动作的节奏和伴奏鼓声的节奏带给人心理上的紧张和欲望。”
尽管参展的艺术家有着各自的不同的认识和追求,但在利用媒介技术做艺术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否认技术的决定性,认为技术只是需要恰如其分地去运用。谈及为什么选择录像技术,王功新说:“这是被逼到这步的。如果一幅画和一台电视摆在一起,人们肯定会去看电视,尽管他知道画可能比电视要好。在视觉艺术中,视觉是本质的,几乎不可言说,采取什么技术手段都不影响你做艺术,但你首先要让人来看,然后才可能把好的东西传达给他。”
电影理论家周传基说:“电影电视在视觉语言上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和表现力,而日常使用的却是20年代就已经定型的语言,录像艺术打破常规语言规范拓宽了人们的想象力。”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录像艺术发展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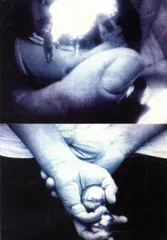
王功新《玩蛋》 艺术邱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