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43)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娜日斯 陆同 张洪 黄集伟)
也说名字
◎娜日斯
张爱玲写过一篇关于名字的文章,说自己的名字恶俗不堪,然而她愿意保留。其实不用她说我们也知道,这名字虽俗,却是大方的,它不是冰心、徽音等等的阳春白雪。张爱玲是张爱玲。
然而她那时代早过去了,这年代没人会叫七巧、流苏,即使是小说人物。
中国人到得美国来,则什么好名字也是白搭。我自己的名字则是,在中国是怪怪的,到了美国更是怪怪的,到哪都逃不了“边缘”、“另类”。刚来时,我的室友说,你的名字接近英文的南希,可是因为前两年里根的夫人叫南希,作风老派,所以这名字也不流行了。南希是旧好莱坞二流影星出身,有点“美国式琼瑶女主角”的味道。现在的孩子,连美国小姐竞选都要找潇洒大方的,名字自然也讲究利索。总统、副总统都是比尔、阿尔(Bill,Al,William和Albert的简称,昵称),年轻人更不消说。
现在中国流行的起名,则似乎是怪与洋。比如回国时,随便一翻报,记住一个名字,叫黄爱东西,据说是写小女人文学,文章没看见,名字是一下就记住了。问朋友,说是在黄爱东后面加一西得来。这真是利害,轻轻松松就把个革命时代的名字转眼之间变作了革命后时代的名字,又有怀旧又有新潮。
走在街上,又瞧见一卡尔吴波。说是拍人像的,拍出来的人像油画效果,很艺术。当然,名字上就看得出。
我的名字不用改也够特别了。回国时,给一新遇到的女孩留自己的名字,她言语颇有机锋:您也给我们留个中国名!让我大乐。当年,父母给我起了个寻根式的少数民族名,却赶上了今日的时髦。
有一个朋友,到安徽上学,见校刊上有诗人名鳞鳞,写的诗是一颗心碎成八瓣等等。一男生见了,很是心仪,觉得一定是才女了。朋友笑说,未必吧,我给你打听一下去。打听回来,作者不但是男的,而且原名王保国。
我上面提到的美国室友,却起了个中国土名,叫罗桂花,让我笑翻,尤其是见其到中国进修中文的证书,写:“兹证明罗桂花同学在我校……成绩优异,予以结业。”她的英文名劳拉,正是桂花的意思,她的姓又接近罗,所以叫罗桂花。中国人都说这名字是乡下女孩子叫的,所以遇到我时,她已被老帅改名叫罗兰了。可是她说,我还是喜欢罗桂花,我是爱荷华人,本来是乡下人嘛!
现在的网络文化,最满足人的转变身份瘾。网上的名字千奇百怪,而且都无从考证。变男变女,变和尚变大侠,变猫变狗,都是举手之事,一天之间,几世的轮回都轮过了。据说有位化名日本人的,遭遇的痛骂,够原子弹威力。又在哪儿见一位男士写文章说,有天化了个女子名上网去聊天,受了极大的教育,原来男人们对女人说话,是那样的!换了一个名字,人还是原来的人,身份却大变了,于是体验了做另一种人的感觉,网上天地,自是别有洞天。
教育我妈
◎陆同
我发现教育是一件相互作用的事.这不是说教学相长那种关系,而是说家庭教育这个问题:起初,你很小,不懂事,你爸教育你;等你长大了,你爸老了,他又有了不懂的事,你要教育他。
我和我妈就是这样,小时候,我妈总教育我要好好学习,还要练毛笔字,说字写得难看会被人笑话。如今我则教育我妈,用电脑打字更方便,您要学会电脑。我妈教育过我要攒钱,尽管她当年给我的零用钱只有5分1角。如今我则要教育她,有了钱买东西也算是保值,否则利率下降,通货膨胀厉害,人民币砸在手里有损失。
我不知道当年我妈教育我时是否觉得“朽木不可雕也”,至少现在我教育她老人家时常会发出这样的慨叹。
这主要是因为她头脑中的一些观念问题,比如我想让她认清自己处于哪一阶层就历时数年,费劲不小。
几年前,我妹妹去一家五星级酒店工作,下班后陪我妈聊天,就会说酒店里的饭菜多贵,一听可口可乐要20多块钱,我妈听罢就大发感慨。妹妹解释说,这里有个附加值问题,我妈听不懂,就说那我反正不去喝。我教育她,这不是您是否要去喝那20多块钱的可口可乐的问题,而是人家饭店并不是针对您这个消费阶层的问题。您要清楚,您老人家喝可乐只需上邻家的杂货铺就行。
我妈同意我的观点,但也为酒店可乐太贵发愁:那么贵,谁去喝呀?这发愁毫无道理,因为我妹妹工作的那家酒店没有倒闭,给我妹的奖金也是月月照发。
我妈虽从没去酒店喝过汽水,但逛商店总是一个爱好,而且固执地认为,老百姓都能在商店里找到乐趣。去年,北京新开张了一家百货店,我妈抽空去逛了逛,回来说那里的东西太贵,一个杯子60多块,一张床7000多块,一把椅子900多块,一块毛毯4000多块……我愤怒地打断了她老人家的报账,再次申明:那商店也不是为您准备的,咱们喝茶可以花200元就买一套漂亮的茶具,没必要去用那种日本杯子。我妈听罢,知道我也曾逛过那家百货店,就希望那家店是给我开的。
如今,在我的教育下,我妈妈终于知道了消费阶层这个概念,在报纸上或大街上见到什么奢侈品,会说:那不是给我准备的。她知道她属于“面的阶层”,出门时偶尔打车就打“面的”,可近一阵子,“面的”大多改成复利,她又问我是不是她这个阶层人数已减少,是不是她没有赶上夏利阶层的步伐。她已主动地把我视作老师,把她在生活中的疑惑摆到我的面前,并希望从我这里得到完美的解答。
多年前,我也是这样对待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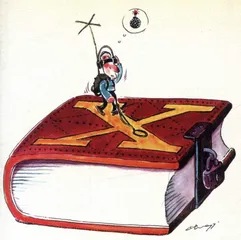
影子档案
文◎张洪图◎王焱
记得曾看过一部名叫《档案爆炸》的美国片。说的是一对夫妇要离婚,女孩判给了父亲,但是因为档案记载这位父亲上学时有过一次喝醉了酒的裸体行为(似乎是被迫的,因为同人打赌),他便被怀疑有侵犯女儿的倾向。女方火上浇油,一时仿佛证据确凿。男方被反复跟踪调查。直到有一天,被惹恼了的父亲敲开了档案室的门,把档案员反锁到了外面,他把电脑中的档案全部调了出来,用打印机打出,从窗口撒到了街上。外面,门被擂得地动山摇,此公却操作自如。影片的结尾是,从窗口撒下的档案挂满了树枝,挂上了公共汽车。像从天而降的白色纸雨,异常壮观。行人纷纷捡起来看。这些隐秘的档案走出了“暗房”,来了个痛痛快快的大曝光。
看完这部影片,我在心里高兴了好几天。真替这位父亲解气。当时还设想,如果我在街上,碰巧拾到手的是自己的档案,此公日后若蹲了大狱,我肯定给他送饭。在我眼里,档案是类似于日记一类的东西。不可告人,装满了隐秘。别人有权利给我们埋几颗地雷,我们却没权利把它挖出来。
虽然是那么几张装在牛皮袋里的纸,却一度像抵在我后背的凶器。上小学时,有一次旷课,老师勒令写检查,并说:“这是要放到档案里的。”那时我还不配有档案,却已经知道了它的厉害:“放到档案里,也就意味着要跟随你一生,那将是一个抹不去的黑点。”听了这话我害怕了好一阵,觉得这下完了,我的人生刚开始就有了黑点,我妈知道了不定怎么伤心呢。既然这样,以后旷不旷课还有什么关系呢?反正黑点已经在那儿了。从那以后,我反而不怎么害怕写检查了,就连默写不出生词也积极主动写上一份。
后来,我去上大学,单位人事科长把刚刚封好的档案袋交给我,要我拿到学校去。我几次萌生了作案的念头,想把它打开审查一下,终于没有得逞。但我掂量着我的档案也就那么清汤挂面的几张纸,不过换了几张不同发型的照片而已。毕业后,我的档案几经周折放进了人才交流中心,成了我必须花钱去养活的另一半自己。有一段时间,我干脆给它断了供给。想一想那档案蒙上了灰尘,什么工龄、职称全在几年前就给截住了,这一下好像变成了清清白白什么也没有了的一个人,反而没了牵挂。
误会和兴会
◎黄集伟
北大西门外有一家馆子,非常普通。那天,我坐班车从那儿过,看见他们挑着一个幌子,上书“北大菜,经济实惠”。我想,那真是…个特别有意味、特别有文化的幌子。北大菜?北大菜是什么菜?是陈独秀的早点?还是毛泽东的宵夜?是张岱年的稀粥?还是张中行的火烧?真的不知道了。显然,这样的不知道,会比“知道”更迅速地让人感觉神秘兮兮,时空错乱。
接着往前走。不一会儿,一辆崭新的长安奥拓慢慢滑到中巴前方。等我看清它后窗上的那行书法,我乐了——那行字是:“长大了,就是卡迪拉克”。在西苑附近的那个大转盘边上,因为有两辆夏利当众亲嘴,班车被卡在了停车场一样的方阵之中。等得不耐烦,我下车,抽烟,看热闹,无意中看见两辆亲嘴夏利中亲得比较凶猛的那辆,前鼻梁隆起了一个大包。我绕到它的后面,忽然发现,在它后玻璃窗上,也贴着一行字:“绝对新手”。我觉得这活从幽自己一默的角度说,挺绝,可却把自己给方了,不太划算。晚上,坐到机子前写字,我就想,一天看到这么多妙语,真是兴会。
第二天,照常坐中巴上班。路过北大西门的时候,我又特别留意了一下那家馆子的幌子。这一留意不要紧,我发现自己昨天得意的兴会,其实是一个误会——昨夜五六级的东南风,已将那条幌子收拾得平平展展,而昨天,那幌子的一角分明没有展平——所以,我看见的所谓“北大菜,经济实惠”,其实不过是“东北大菜,经济实惠”之误。
这样一来,所谓“兴会”,或者“误会”,怎么说?就我的经验看,很多铁一样的“误会”,也不是没有可能变成“兴会”。这个想法在几年前刚刚开始用电脑写字时,我就有预感。有一天,我在一篇文章中用到了“从北四环路经过”这样一句话,可没想到,被我“双拼”到荧光屏上,居然成了“从被死缓路经过”——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误会,却让我好久惶惶不安。
诸如电脑上“自由落体”和“自由裸体”,“敬业精神”“精液精神”的误会,使我觉得,所谓“误会”的“误”,并不排除它恰好是另一类思维,比如我一位朋友,他说他总会误读一块街边常见的招牌,即“补胎打气”,他读来总是“打胎补气”,这位朋友在医院工作,见了修车招牌上的那4个字,总会想到打完胎,气血两亏,应该补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