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心理咨询业把脉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徐壮志 张晓松)

“我很不幸。因为有了孩子,单位和家人劝我和强奸了我的人结了婚。”
“结婚,原本是要他承担这个责任,但近几年,他对我们母女越来越凶,经常打我和孩子,在外面和女人鬼混。”
“现在,我们离了婚。问题是我的孩子,她恨他。她最近老跟我说:‘妈妈,我要杀了他,他太坏了。’我很害怕。”
很难统计,8年来北京有多少求助者通过热线寻求帮助。据了解,青春热线6年来已为1万8千余人作过咨询,而全天候运行的华理心理危机专线则在一年里就接受了近2万人的咨询,他们还将咨询内容做了统计,结果是婚烟家庭占60%,性占15%,人际交往占10%,老年、儿童问题占5%,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正如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郑日昌所说,身体健康并不意味着心理健康,尤其在当前这种社会转型期,工作、生活压力加大,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封闭性加强,以及新现象、新观念的困惑,正处于心理问题的多发期。人们的倾诉欲即是心理热线兴起的主要缘由。热线的便捷性、倾听和引导、启发性,以及隐匿感,都使其易于为人接受。对于性格含蓄、内向而不愿“抛头露面”的中国人来说,电话咨询似乎尤为适合。
一个人可以开办热线吗?
我国第一条心理热线于1987年在天津出现。1989年,北京市首家心理热线——希望热线成立。1993年心理热线的发展进入繁荣期,仅春季就有30多家热线相继在京成立,各大传媒对此也深为关注、寄予很高的期望,热线本身就成了一种“热”。
但这种热并未持续多久。由于人员、资金等种种原因,多数热线都在一年内悄然消失了。剩下为数不多的热线惨淡经营,热线渐次“冷”了下来。
在’95心理咨询与热线工作研讨会上,青春热线的负责人陆小娅曾指出过:“热线的价值在于长期开通,随时服务,而不是一时轰轰烈烈的事业;热线也不是个人的事业,而是集体的力量。关键在人员的管理和培训上。”
仅凭热情是办不了热线的。成立于1994年的家庭暴力热线,以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为目的,也确实成功地解决了多起暴力事件,但由于家庭暴力牵涉到法律问题,仅靠心理抚慰是远远不够的。而请律师、打官司、设立庇护所等,又绝非一个仅有少量经费和人力的民办机构所能支撑的。于是,在今年初,热线不得不告停办。
个人办热线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个人守着一部电话就成为一条热线,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事实上,我们的媒介也报道过相当多的这样的热线,如武汉秋云的“倾心热线”,长春市身残志不残的女十佳余海波的“心语热线”等。但也有人指出,尽管这些热线办得相当不错,但从心理咨询业的行业观点来看,个人办热线并不适合。心理咨询员的身份按理讲是不宜公开的,因为公开咨询员的身份往往会影响双方沟通的平等气氛,而且容易使咨询员的个人事务和家庭受到影响。
更有一些电台、电视台办的所谓“心理热线”,虽然具有一定的心理常识的普及作用,但由于没有咨询业中极重视的保密性,因而使它的咨询色彩大打折扣,为同行所不齿。有人指出,此类热线是教育性大于咨询性,因为在无数耳朵的倾听中,很少有人会吐露他的隐私。
可见,心理热线之“热”既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有一时的盲目性,降温是合乎情理的。
谁有资格做心理咨询?
谁有资格做心理咨询?这是国内心理学界争论颇为激烈的一个问题。有精神医学背景的人,有心理学背景的人,有社会工作背景的人谁都不服谁。“圈儿里”某些权威人士也在这场论战中或明或暗地指责着业余的实践者。到底谁说了算呢?
事实上,在目前从事心理热线的咨询员中,极少有专业人员。他们多半是志愿性质的咨询,来自各行各业,教师、学生、记者、律师、作家……他们虽然极少经过专业的心理咨询教育,但多数都接受过这样的培训和学习,用他们的话说,“并非只有热情。”
对他们来说,来自专业人员的指责多少令他们有点不愉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大学热线364”咨询员们就有切身体会。1995年12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博士Mary Ni在北京大学为北京市心理咨询中心的负责人作讲座,他们闻讯赶去,却被主办者拒之门外。
其实,即使在我们所谓的专业界,谁才是真正咨询专家亦无定论。我国眼下在做心理咨询的专业人员有来自医学界的(精神科),也有来自心理学界的。但据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郑日昌介绍,甚至连“我们也称不上心理咨询的专家。心理学和心理咨询是两码事,心理咨询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都几乎完全不同于心理学理论或知识的掌握。各高校所设的心理学课程,也只是少量涉及心理咨询。包括我们做的心理咨询,也只是读读书自修一下,试着来做……在国内,真正的心理咨询专业科班毕业者还属凤毛麟角,目前来做这件事的都是边学边做。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家的起点都是一样的,谁也谈不上权威,若说有权威,也是业余的权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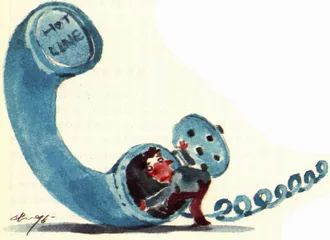
青春热线的督导龙迪女士曾获得医学硕士学位,但她坦然承认:“自己学医时对非专业人员不在意,瞧不上,等到自己在发展中遇到问题时,才感到专业的并不适用于解决问题,专业语言可用于同行间的沟通,但并不利于咨询。”她认为,专业和非专业人员间应互相学习。
一般认为,非专业人员有热情、非专业化的语言风格,以及平等对话的天然优势。但是,必要的学习、培训也是重要的。咨询的目的是助人,不能仅停留在陪人聊天的水平上。
青春热线就已形成了它自己的一套有关人员的选取、培训和监督的秩序。他们首先招聘一名专家做督导,负责技术指导;然后向社会各界(大学本科学历以上)招募志愿者,由专家3人一组逐一面试,通过后再过2个月的见习期和2个月的实习期方可上岗工作。工作期间每月举行一次业务研讨会,随时撤换不合格人员。如今,青春热线已经拥有了一支40余人的咨询队伍,在国内热线中可称是实力雄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主任王建中认为,心理咨询的形式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专业机构——重在治疗心理疾病,如医院和研究所;第二,咨询中心——解决轻度心理障碍,如高校及社区的咨询中心;第三,互助层次——由受过一定培训的人员组成,如青春热线。可以说,心理热线是治疗、面询的必要补充。
据郑日昌教授介绍,即使在国外,从事热线心理咨询的咨询员也大多是非专业出身,再加以适当培训的志愿人员。而在我国,在新生事物、价值观念、选择机会越来越丰富多变的今天,人们的心理承受力面对严峻的考验,人们会越来越多地需要心理咨询。而目前专业人士肯定不够。让一名心理专家坐在电话旁做咨询,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他认为,“做心理咨询学习专业知识是必要的,学习医理知识也是必要的。现在一些有志青年,完全是用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感悟来做咨询的。那么,只要能解决一定的问题,也是很好的。面对国内社会心理问题如此大的需求,现在还不是用专业权威的资格来泼冷水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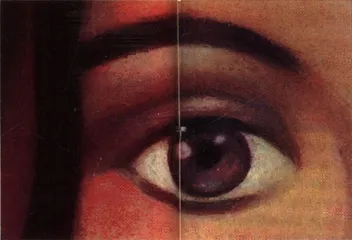
应该用钱来换取慰藉吗?
谈起经费问题,几乎没有一个热线不皱眉,北京市第一家心理热线“希望热线”(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办)就因为经费拮据,2年后即告停办,现在只是利用上班时间顺便做点咨询。“妇女热线”的负责人王行娟女士也说她“一天到晚都在为钱发愁”。
青春热线的负责人陆小娅告诉笔者:生存问题是目前热线所面临的根本问题。而经费正是一个热线生存所必备的物质条件。
目前北京市心理热线的经费来源大致有三类:一类是依托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如青春热线属于中国青年报社,心理健康热线为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科所办。这类热线一般无断炊之虞。另一类主要是依靠自己筹集经费,如妇女热线、家庭暴力热线,难度很大。就以妇女热线为例,自1992年创立以来,他们先后得到过美国福特基金会、简·方达基金会各1万美元的援助以及联合国妇女发展署的几万元人民币,以致同行们都以为他们是有国外支持的富裕热线。但这些支援都是一次性的。更多的经费要由他们自己来筹集。他们每年的预算是30万元,仅房租一项每年就要7万余元。筹集经费是妇女热线负责人最头疼的事情。
第三类也是最有争议的一类,即收费热线。如博爱博心体健康咨询热线、华理心理危机咨询专线。它们的方法自己养热线。如华理心理危机专线的收费是2元/分钟。
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心理热线的特征就在于为求助者提供慰藉和援助,若利用援助来收取费用,则会令人感到缺乏感情。作为热线来说,是不应当让求助者感到这种帮助是要用钱来换取的,这样会使求助者产生冷漠感。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6年第10卷第1期)的一份统计表明,心理热线咨询中,能在10分钟内完成咨询的仅为41.01%,多数咨询都在10分钟之上。青春热线的主任陆小娅估计,一般热线平均每完成一个咨询约需30分钟左右,情况复杂的要用2、3个小时,并且要多次才能完成。相比之下,2元/分钟的收费已大大超过了面询的收费。那么这样的价格是否合理呢?
据华理心理危机咨询专线的负责人王晓兰女士介绍,2元/分钟的收费并非是他们漫天要价,而是根据对自身的水平、投入、条件的估算,和160信息台协商确定的。在收费中,约有40%的费是收不到的,因为有人用公用电话以及许多电话局无法收费的电话咨询,20%要交给电信局,另外还有每部电话500元/月的管理费,最后大约剩收费的30%由热线和160信息台均分,热线到手的只有15%即每分钟0.3元。
王晓兰女士说,这笔收入只能保证热线的基本生存需要,并不足以维持整个热线的运转。他们的收入更主要的是来自一些与心理相关的实业。华理是北京首家以企业化模式运行的心理咨询机构,王晓兰女士对这种运作方式颇有信心,目前,她正在张罗着办一家(据说是国内首家)心理书店。
她还认为,打求助热线的人一般是急于寻求帮助,很少介意收费问题。她的专线24小时全天候运行的(这在热线中较为少见),但仍有相当多的人反映热线不易打进来。而且,她觉得免费热线由于其易得性,也导致了一些人打热线的随意性,而一定的收费则可以避免一些无聊者的干扰,并使求助者产生一种正规感,从而重视热线咨询员的意见。
据郑日昌教授介绍,在发达国家,心理热线大多都是公益性的,由一些慈善机构出资。收费的热线咨询很少,而且其内容亦多半与性有关。青春热线主任陆小娅女士特别向笔者提到香港的模式:由公益机构向社会募捐,然后负责将资金分配给各种公益事业如心理热线等。
遗憾的是在我国尚没有能承担这样一种角色的机构。因此,争议归争议,各种心理热线都在现实地探索着自己的生存、发展之路。

谁来保护热线的“消费者”
王晓兰女士曾讲过这样一则个案:有一次,她们接到一位年轻姑娘的求助电话,据姑娘说,她以前曾因心理问题而打过另一个热线,那个咨询员给了她很大的帮助,后来他们继续联系,以致约会并发生了关系。但她后来却发现那个男咨询员已有了自己的家。这使得她一下子如堕深谷。
这个事例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谁来负责审批建立一个心理咨询热线的条件并监督其运行?作为一个行业,谁来为心理咨询业制订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并保证它的贯彻?
我们采访过的所有热线都没有经过任何有关部门的审核和批准。有的只是觉得可以办就办了;有的是取得自己所依托单位的批准就办了,也有的(如收费热线)则在工商局注了册。
据市卫生局的有关人士介绍,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只有有“医疗行为”的机构,才归卫生局管,但心理热线咨询显然不具有医疗行为的性质。
据业内人士介绍,我国尚未有专门管理心理咨询的机构。而在民政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部门负责对心理咨询机构的审核和监督。
一般来说,各个心理咨询机构都有着一套运行规则:诸如为咨询者保密,咨询员身份保密,原则上不许咨询员与咨询者见面……等等。笔者也确信,我们的咨询员绝大多数都是诚实而富有责任心的(否则他们就不会志愿来作辛苦的咨询员)。但是,这样的规则毕竟约束力有限,并且有的尚欠严密。而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来说,仅靠其人员的自律显然并非适宜。心理咨询业的发展呼唤着一套完善的运行机制:从成立审核,到资金保证,以及运行规则和业务评估。 郑日昌心理学心理咨询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