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什么,怎样吃
作者:娜斯(文 / 娜斯)

吃红肉,还是吃白肉,那是一个问题。或者,吃肉,还是不吃肉,那更是一个问题。或者,吃脂肪,还是不吃脂肪,那又是一个问题。在今天的美国,关于吃,颇能让人生出些丹麦王子式的犹疑混乱之感。
在中国时,看到《廊桥遗梦》颇为风行,不知读者注意到没有,表示男女主人公之脱俗于中部乡村传统保守生活的元素,在懂得欣赏老桥之美,浪迹天涯的梦幻,昏昏暗暗的爵士乐酒吧,叶芝的诗句,性爱的灵性……等等之外,还有——他们不吃肉。不吃牛排,不吃香肠,不吃烤鸡,不吃火腿。他们的第一次浪漫晚餐吃的是:女主人公后园里采来的胡萝卜、香菜、洋葱,马铃薯……“素油,一杯半蔬菜,煮到浅棕色,加面粉拌匀,再加一品脱水,然后把剩下的蔬菜和佐料加进去,文火炖40钟。”第二次则是:“夹馅青椒,用番茄酱、黄米、奶酷和香菜末扮馅,然后是简单的菠菜色拉,玉米面饼,甜点是苹果酱奶酥。
请原谅我面对一个“超凡脱俗”的故事而大谈其吃——没有办法,我这篇文章要闲言的不是爱情的美国,而是吃的美国。据说“通向男人心的道路经过胃”,女主人公丈夫的胃需要牛排,而远游客的胃则欣赏蔬菜水果。经过这样不同道路抵达的心如何不同,就是所谓“故事”了。
果然,女主人公共鸣于远游客之吃的哲学:
“已经闻到香气了,“他指指炉子,“是清静的气味。”
“清静?清静能闻得到吗?”她想着这句话,自己问自己。他说得对。在惯常给全家做猪排、牛排、烧烤之余,今天这顿饭的确是清静的做法。整个食物制成过程的链条上没有暴力,除了把菜从地里拔起来也许可以算。炖烩菜是静静地在进行,散发出的味道也是静静的。厨房静悄悄的。
这段文字恐怕可以给哪本叫什么《禅食》之类的素食谱做广告。故事发生在60年代初,的确空谷绝音,因为那个时代的美国,还是不折不扣的“土豆加牛肉”——没有关系,30年风水流转,今天有一半的美国都开始大谈而特谈“清静”的饮食了,先驱者的故事因此大销而特销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吧。
《纽约时报星期天杂志》有一期专题讨论今日之食在美国。封面为一片蔬菜叶和一个汉堡包,被主题文章的标题隔开:“怎样吃;一个分化的美国。”看过《廊桥遗梦》的读者,恐怕应该先有具体的体会了。就象《廊桥遗梦》,《纽约时报》的作者们也在吃什么,怎样吃中间,发现着不同方式的美国生活。用《脂肪的道德》一文作者的话说,是:“你吃掉脂肪的数量,和你吃掉这些数量的脂肪的方式,比你开什么车,穿什么衣服,住在什么街区,更能说明你是谁。”
吃得太饱了!
据统计数字显示,美国人达到了历史最胖时期-2/3的人超过正常体重。这固然是得天独厚物质丰盛的结果,却也反映了美国人的饮食习惯该有点儿什么问题。《廊桥遗梦》故事发生的五六十年代,美国人的主要食物无一不是高热量高脂肪:牛肉,奶油汤,妈妈的苹果派……,后来更有快餐文化兴起,汉堡、薯条、炸鸡;再配上高糖分的可乐,四通八达的汽车——方便,方便,再方便,副作用是,因为万物遵循能量守恒定律,被方便了的人节省下来的能量,全变成了脂肪,在身上挥之不去,成了真正的不便。
我恰在“廊桥”附近的大学小城念书。周围的“乡亲们”一到周末就要到超级市场拉上小山似的食物回家,还爱去一种自助餐馆吃饭。这种自助餐馆便宜得象不要钱:六、七块钱一位,自盛自取,吃饱为止。至于台上的东西,从肉饼牛排,到面条薯块,从沙拉鸡汤,到蛋糕水果,质量不论,数量无限。在这样的餐馆里四下一望,果然无一瘦者,而胖者则多已胖得没边儿。
物极必反,近十年间,美国人好像终于觉悟自己吃得太粗鄙了,突然之间,节食和健康两个概念成为有关吃的一切之中最要紧的字眼。市场调查专家Leo J,Shapiro说他还从未看见公众对哪个题目达到意见一致之快,之完全,能如节食和健康。“对于食物,特别是食物中的脂肪成分会影响健康这样一种概念,已成共识。”他说,“统计表明,对于食物脂肪的关切超越了阶级、种族和地域的界限。”
“此刻,英文语言中最有力量的字眼是‘不含脂肪’,紧跟的是它稍胖一点儿的兄弟‘低脂肪’。”willaim Grimes在关于食品推销的《新产品!独特!无脂!——只要标签对路,你卖什么都成》一文中更小幽了一默,却并不夸张。喝全脂还是低脂牛奶?吃牛肉还是吃鸡!椒盐饼干还是炸土豆片?每个人或多或少要做种选择米安慰安慰自己。有人喝减肥饮料,有人在家实行严格节食,到饭馆时再“解禁”,有人只要吃东西就要掏出计算器算卡路里,还要记“饮食日记”,诸如此类,折腾得不亦乐乎。电视明星奥普拉·温佛瑞与体重做斗争艰苦卓绝,最近一次大为成功,一次减了100多磅,衣服尺码从十几号变成标准的8号——说是运动加合理饮食的结果,于是乎,奥普拉重金聘请的私人厨师出版的食谱一下子畅销无阻,长卖不缀。在最为形象而疯狂的好莱坞,一家牛排浓汤的老餐馆,是旧日明星的风头之地,却因落伍于时代而扫地关门,今日的好莱坞一座难求的餐馆是Nobu——直接从日本空运鲜鱼的日式餐馆。正所谓:新式饮食势不可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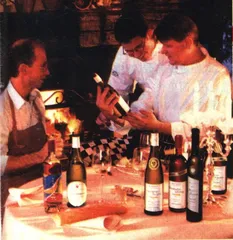
我在爱荷华的第一年同住的美国室友戴叮叮铛铛的东方耳环,会结结巴巴讲中国话,研究中医中药,正在有一个印度男友。不用说,她不吃肉。楼下的两个男生倒无所谓,但是他们很穷,故多以面包奶酪啤酒过活。他们都似乎非常接近孔夫子“一掸食,一瓢饮,在陋巷”的境界。
镇上有家印度素食馆,非常时髦,每每经过,常见门口人头晃动——店面小,要等候空桌。
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则有家合作社(co-op),是镇上“新时代”饮食风格的基地。这种合作社在大学城,城市时髦街区已经必有无疑,它们与大超级市场趣味正好相反,跟中国的杂货铺倒更接近,要的是小门脸,健康食品,社区气氛——顾客可以成为合作社社员,有折扣,收社讯,还可以志愿打工,等等。不用说,我的室友是积极一员,我因为离得近,每天放学路上也时而光顾光顾,顺便见识了不少小镇先锋人物和先锋食品——这里的所谓先锋食品,不少是中国的常见,象黄花木耳,小米豆腐,诸如此类。这样的小店看起来不起眼,价钱可是要比超市贵。
后来搬到纽约,不用说“新生活运动”就无所谓先锋不先锋,在这里日本寿司快餐店已经颇可以同麦当劳一争长短,我和一位同事出差,她的健康意识把我弄得不胜其烦;每次吃饭都为所点之菜是否热量太高而探讨一番。有次早餐我正好特别饿,就点了顿全副武装的传统早餐:炒鸡蛋烤香肠煎火腿摆满了一盘。她拿着一杯橘汁,一根香蕉,一片面包坐在我对面,令我觉得我这么肆无忌惮地把一堆脂肪吃下去,好像在犯罪。或者,吃完之后,没准一命呜呼。
我自己的经验似乎正好吻合《纽约时报》的统计报道:更富裕的、教育程度高的,居于城市的群落更加密切追踪关于营养和健康的研究,更乐于购买未加工食品及粗粮,更积极从事“低脂肪实践”的种种仪式。控制脂肪的摄人,已经成为控制生活之能力的一种显示。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比现在的美国人更关心其他种饮食文化的特点,更乐于对其他饮食文化采取“拿来主义”,比如跟美国饭特别南辕北辙的日本饮食。日本人似乎宋朝时候接收了中国的禅宗且发扬光大之后,食道也是一路玄远地发展下去,讲究生、鲜、清、涩,入口尽是海鲜,做法皆要原色原味。时下的统计,日本人确实属于世界上的长寿国家之一。总而言之天时地利,种种原因,日本食道在美国颇获成功,当然还是在大城市为多。高级餐馆如Nobu者又在纽约开了分店,仍是一座难求,快餐者如寿司吧,在曼哈顿处处可见,颇有自己的市场。
日本的饮食毕竟与美国文化相去甚远,不可能代替本土风格,所以,美国人改造饮食,还是要找近亲者比较有用——当然,找到法国去也。几年前,收视率很高、很有传统的CBS周日的特别新闻节目《六十分钟》制作了一个研究法国人饮食之道的专题,颇引起些反响。《六十分钟》的节目是琢磨许多美国人怎么也想不通的一件事:法国人有名地讲究美食,更有名地爱吃奶酪,奶酪消耗量比美国人要多得多,为什么法国人却不胖?
《六十分钟》有许多“振聋发聩”式的发现,最引起注目的是法国人不吃汉堡包,不喝可乐,而是中餐多吃三明治,晚餐爱配葡萄酒。《六十分钟》又赶忙找科学根据,好像医生们也同意喝适量的葡萄酒会化解脂肪,对健康有利。好了,据说节目播出后,葡萄酒销量大增。
我在一旁忍不住好笑不已。我觉得喝葡萄酒其实是枝节问题,整个文化所造成的“饮食心态”之不同才是关键。我这是所谓“上纲上线”吧。记得有次在一个朋友家作客,他在西班牙住过一阵子,偷偷带回不少西班牙烈酒,这天聊得高兴,就弄出一点大家喝着玩——其实还不如说是看着玩,因为这酒太烈,要先用火柴点着,映出蓝色的火焰,烧掉些酒精——颇造出点气氛,然后加一点糖,在粗磁杯里倒一杯底尝尝而已——的确有种独特的醇香。因此聊到了美国人的喝酒。美国人的喝酒好象总在两个极端,不是滴酒不沾,就是无法自拔,好像不能优雅处之。象我们那天那样的玩法讲给别人听一定以为我们是何等酒徒。我的朋友对此一言以蔽之,说是清教传统的结果,前题是酒是享乐,因而禁忌,因而罪恶,然而一有禁忌,就更有被压抑后更强烈的反弹,一反叛就比谁都更加邪乎。我觉得的确如此。美国人管教孩子是很严格的,法律规定不到21岁不许买酒,不许进酒吧,一般父母也都严禁孩子在家中碰酒。然而小孩子们进了大学,远离父母,又满了21岁,一定要疯狂一下——美国的本科生到了周五晚上没有别的,一定要喝啤酒狂欢,做种种荒唐之事。总之,在美国文化里,酒是狂欢,是解放,浅斟低饮是不大懂的,起码不是主流,象法国人那样餐餐喝葡萄酒更是没听说过了。其实在后者那里,酒可以衬美食,助谈兴,却不至要闹到上瘾中毒进戒酒中心不可。酒是如此,吃也一样,美国人老找不到平衡感,先是粗枝大叶吃得过饱,然后是大惊小怪谈脂肪色变。现在美国人对所谓“地中海饮食”也大感兴趣,因为这一带的人如意大利也是爱吃爱喝,却也没有美国人那么胖的,据说是他们做菜的橄榄油比其他种脂肪健康的缘故。于是乎,橄榄油又成了新宠。其实,美国人只要少吃点汉堡薯条可乐之类的垃圾食品,多点精致食道,就未必要象现在这样头疼脑胀地动辄要计算摄入的卡路里。果然,这阵子专家们又放话了:调查表明无脂肪食谱未必能减肥,不能一点脂肪不吃,不能完全压抑食欲,否则适得其反,云云。

9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节制的时代。清简是时尚潮流,身心健康是人人追求之事,环境保护是公共话题。60年代体验过性解放,80年代追求过物质享乐,现在要绚烂归于平淡。这是一个佛教显得颇有魅力的时代,也是素食者日趋增多的时代。就以我个人而言,虽然还不至于被感化到腥荤不沾的地步,却也颇接受了一些素食观念的影响。该不该杀生吃肉的道德问题于我仍是没想清楚,吃肉是否对我们的生存环境是大不负责的一种行为这种观念我也还姑且听之,但是的确肉类比蔬菜水果更易腐烂变质,蔬菜水果更给人以清爽舒服之感,于身于心都是后者更有益的道理我却是差不多照单全收了。我现在在“吃……不吃……”的问题上差不多是“吃白肉派”,道理上是即使吃肉也要多食鸡鱼,少食猪牛,而且弄来本素食谱,闲来钻研,颇有斩获。看来我是典型的“不能免俗”一类。不过偶看美国著名的女烹调专家Julia Child的一句话,“我最讨厌极端主义者”,于我很是心有戚戚焉,觉得这是食品专家容易拥有的人生观,起码于食道上未必不可信奉。

美国人也前所未有地愈来愈趋向于同意饮食有道了。新鲜,清爽,风格,品位……成了令人关心的饮食话题。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的是中国菜了。讨论吃却避而不谈中国菜,简直该称得上是大逆不道。不过,坦白说,中国菜虽然名震四方,流传四海,整个的形象在今日世界却有点模模糊糊,起码在美国,并没有创出品位来,不象日本餐的坚守自己风格,又没有法国菜的苦心孤诣。首先,中国菜在海外走的是低档路线,叫“中餐外卖”快成了“随便填肚子”的同义语,唐人街的小粤菜馆们又都面目模糊,了无意趣,就算是最高档的中餐馆,在纽约也进入不了同类的法式、意式、日式之环境水准。问题恐怕在于观念。中国人似乎太骄傲于自己的饮食之方了,骄傲到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到了海外,又认为洋人反正不懂,国人反正饮鸩止渴,两方面顾客都糊弄糊弄即可。殊不知,糊弄别人,最后害的往往是自己。再者,中国菜素与产生之的文化一样,以博大精深自豪,却还没有与现代化找到最终契合之方,没有在现代世界树立某种清晰的“形象”,使人认为中国菜无非是油锅爆炒,这形象也颇不合今日潮流。前一阵子,美国健康局发布研究结果,说中国菜含油量高,对健康不利,搞得华人颇为不平,认为那是因为老美不懂点菜,不知怎样搭配。可是,谁之过呢?中国人并没有教育老美如何吃中餐,他们当然不懂。就算是正宗中餐,似乎也在等待新的观念参与。在美国的饮食革命中,处处可见的中餐却无甚建树,不亦怪乎?如果有人说麦当劳是“文化侵略”,那么中国餐馆也可以说颇为占据美国,只是并没有明确的文化意识,这不该也把责任推到美国人头上去吧。我们进麦当劳,期待的是窗明几净,速战速决,简单快乐,毫无意外;如果哪天正好玉洁冰清,想说禅论道,可能该去日本餐馆“清净”;情人约会追求浪漫气氛自然爱选法国餐厅。当然,每种饮食文化之中又有自己内部复杂的风格区分,这一点不用说,中国菜极为自豪于自己的形象多变。在中国本土,香港台湾,餐馆文化应该说还是多种多样的,可是在海外,不知为何差不多都是披金戴银,大红灯笼高高挂,仿佛不如此,就必是数典忘祖,我倒怀疑对此摇头最厉害的该是孔夫子。
饮食批评家们说,美国的饮食终于“进入成年”了,美国的餐馆也发生着很大变化。一方面,麦当劳仍是快餐之王,且输出海外,四面开花——最新新闻是印度都有了一家:要知道,印度人是不吃牛肉的!然而没有关系,麦当劳在印度不卖汉堡包——所以全球有了第一家不卖汉堡包的汉堡包店,可见麦当劳卖的不仅是快餐,而且是一种形象,一种工业化社会才会产生的饮食“仪式”。另一方面,各式各样的异国饮食大举进入美国,也在改造着美国人自己的饮食经验。就以正在大出风头的纽约餐馆老板Drew Nieporent的事迹而言,此公自1990年在纽约的新艺术中心地带TriBeca拉来影星罗伯特·德尼罗合开“TriBeca烧烤”以来,就成了美国餐馆业的新星,不但“TriBeca烧烤”颇获成功,成了纽约一家时髦饭馆,而且使得他接二连三在附近或新开,或购买、或合营了四家餐馆:一家很受欢迎的法式餐厅,一家号称目前纽约最难订位的日式餐馆(就是上面提到的Nobu),一家带舞蹈表演的中东饭店,以及一家午餐、糕点店。从这几家餐馆的不同国家菜式,可见时下饮食风气之一斑。TriBeca是纽约苏荷区饱和后,艺术家向更下城一带流动新发展出的前卫街区,Drew Nieporent懂得掌握顾客心理,不仅菜式讲求风格,餐馆设计,布置和氛围也有戏剧性的情调,故成了《纽约时报杂志》举评美国最佳餐馆老板的一时之选。
从牛排汉堡,到寿司生鱼,从地中海风,到中国炒菜,从素食主义兴起,到垃圾食品挨批,美国饮食之“再教育”运动正方兴末艾。 饮食廊桥遗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