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大片想起中国人的梦与玩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孟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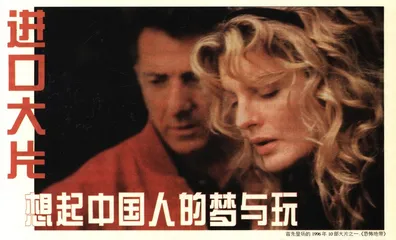
首先登场的1996年10部大片之一:《恐怖地带》
进口大片想起中国人的梦与玩
去年回北京,听说《真实的谎言》的热潮刚过,正赶上满街又多了个名字叫阿甘的,使我知道了有所谓“10部进口大片”一说。我还真的跑去看了一次阿拉巴马南方腔的阿甘说中文什么调——结果是一口普通话,觉得有点儿怪。国内进口的10部大片中,8部都是动作片(从名字中也可猜到)。我对大片怎么跑到中国去的背景毫无所知,但因为是个影迷,有关的话却引出一堆。
有人说进口大片都是好莱坞最好的片子,这样与中国电影竞争不公平,使我有点儿错愕。我对动作片的兴趣没那么浓,所以这10部片子,我看过的只有4部:《阿甘正传》、《生死时速》、《真实的谎言》和《亡命天涯》。《阿甘正传》在没公映之前,就偶尔在电视上看到关于拍摄过程的纪录片,里面展示了很多电脑特技,又有很多噱头,涉及美国历史,就去看个究竟。这部片子虽然是很正统的美国梦,但因为故意用阿甘的经历吻合战后的历史,所以有点儿自嘲的味道。一个傻小子误打误撞实现了美国小子们最常做的梦:足球冠军、战争英雄、总统接见、百万富翁、梦中情人(就差没当过一回牛仔),而且见证了国家历史。他的成功梦里也投射着美国的恶梦和歧梦。阿甘成为美国传统英雄一帆风顺,但是他的爱情却有点非主流——毕竟又不是完全“正常”的美国英雄,他还做了回嬉皮,体验了一番“在路上”,跑了3年步吸引了一群跟随者。他的青梅竹马、邻家女孩、梦中情人也不是寻常的美国甜心,而是60年代叛逆文化,要赤身裸体对牛弹琴唱“答案在风中飘”的。她走了另一条曲折的路,让阿甘读不懂,还得病去世了——隐喻了60年代最极端反叛一代的真实命运。她死了,却留下了一个孩子,是与阿甘生的,也有点隐喻。反感这片子的人不喜欢它看历史用的阿甘的——老百姓的、反智的——叙述,但这种叙述却是一种大众心灵的现实。大众美国人用它阅读历史,外人却可以用它阅读大众美国。
至于两部纯粹的动作片,《真实的谎言》还是最近因为几个朋友租了录像带所以跟着看了。比较喜欢《生死时速》,可能因为喜欢其中的男星,看时正好有家影院专放过了第一轮的电影,票价七五折。《亡命天涯》是惊险悬念,跟着紧张一回。
所以,这10部大片一来种类太单一,二来也谈不上都是“最好”的,只能说它们是票房高或最高的,而且有些连这也还说不上。据说1996年将要进口《水世界》,这部好莱坞的巨资制作恐怕也只能说是“最花钱”的。相对最高额投资,票房明星担纲,拍摄者精疲力竭(在夏威夷搭的水景,困难重重),其结果却是票房平平,明星失蹄,一片倒好(最近又有一部讲女海盗的片子同此命运,所以有种说法是拍水戏肯定要全军覆没)。不过这种电影一做就是全球市场,在美国不赚钱的片子,在海外还能捞回不少。这也并不奇怪,虽然美国观众傻乎乎的不少,但高科技的巨片动不动就隆重推出也见得多了,不是有点邪招实在会腻了。世界其它地方的电影制作没有好莱坞的成本技术,所以要看大制作的片子倒要看美国的。
娱乐片是为了彻底纯粹的娱乐
因此,对娱乐片的共识首先是我们去看是为了玩,为了寻开心,为了彻底纯粹的娱乐,但对娱乐的要求不是给一个要一个,也是讲高下的。某些人觉得特别娱乐的,另外一些人会觉得乏味透顶。像动作片,就不光是娱乐而且要说是非常男性化的娱乐了。影评家谈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偶像魅力时开玩笑:影院里有800个观众800个都是臭小子——有一个女孩子儿还是被她哥哥骗去的。所以没人请你谈艺术——尽管其中也有高下之分,也有作出艺术东西来的,也有艺术家的精心投入,也需要明智的评论。动作片票房高,也不至叫人人嫉妒,起码奥斯卡奖已经是很不“艺术”了,对动作片还要作出不理不睬的劲儿。可见各有各的地盘儿,不必较真。好莱坞不成文的规矩很多,比如说就没有什么动作片能得最佳影片奖的,没有一位演员因为演动作片能得演员奖的——事实上,演英雄得不了奖,演坏蛋的倒最容易受青睐。动作片明星施瓦辛格、史塔龙、史蒂芬·塞吉尔、梅尔·吉布森、布鲁斯·威利斯、哈里森·福特,你再数吧。前面几位是纯粹的肌肉先生,后面几位则都还算是演员,是靠动作片维持票房明星地位,靠其它电影维持演员声誉。像布鲁斯·威利斯、哈里森·福特、梅尔·吉布森在非动作片生涯中都还有点口碑,但是这些票房明星挣的钱太多了,锦上添花再被奖赏奖赏就难了。而且他们的形象太容易定型,所以这种人要想再来点别的承认,几乎不能再指望演技上而是要“自谋出路”:比如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那样干脆开始拍片得导演奖,今年则是轮到梅尔·吉布森(他自导自演的《英雄的心》获导演奖)。其实不只动作片巨星,偶像明星也是一样的。太英俊的罗伯特·雷德福迷倒众生数十年(可能应该说众女人),最后也是靠导演得奖。至于现在片酬最高的女星黛米·摩尔,美国甜心梅格·里安,桑嘉·布劳克,都有票房号召力,但跟任何奖励都还无缘。所以大家都平心静气:有得必有失。
虽然我说进口大片不一定是好的,但如果我呆在国内,肯定也是忠实观众,——因为我没有更多的选择。当年我也是连《第一滴血》都看了的。不知为何过了这么多年,进口片还停留在比《第一滴血》高不了多少的阶段,而且血越溅越多。美国生活的娱乐项目里,看电影录像带是很流行很容易的一件事,在北京则发现没有朋友晚上的娱乐项目是看电影。国内现在有了《红樱桃》和《阳光灿烂的日子》,可这也就够看两个周末的。能看的电影太少。
最近看的娱乐片是写洛杉矶警察和黑帮的电影《热》(Heat)。这是部惊险片,促成我去看的原因之一是同去的朋友中属男性的部分坚决想看;二是美国两大天王演技派巨星罗伯特·德尼罗和艾尔·帕西诺自演过教父之后20余年就再没同享过银幕,这次演一正一邪对手戏,舆论大噪;三是当时我正在洛杉矶,觉得看看拍洛杉矶的片子也行——听说此片拍洛杉矶白天一般晚上的城市夜景挺不错。看的结果是影院的立体声太高级,我们座位太靠前了,差点儿没给震出心脏病,而且漫长无比,震了3个小时才算完。看动作片坐头10排实在太可怕,这错误以后绝不能再犯,可那天是周末,后面都满了。另外好玩的是洛杉矶警察因为殴打开车违规黑人事件、辛普森案件等名声特坏,所以青年观众对警察格外大叫倒好,警察越倒霉大家越开心,格外认同黑帮——认真点儿说,此片导演拍过《迈阿密风云》,所以可想而知这回是把暴力犯罪放到洛杉矶。《纽约客》评论遭,这片子的毛病就是非想拍得比惊险片再高级点儿,再艺术点儿,探讨病态人性灵魂痛苦什么的——毕竟是两位天王大演员出演哪,可是不幸的是它光当惊险片倒也罢了。德尼罗和帕西诺在同样画面里只有6分钟,演技的确无懈可击,让观众觉得不够。但是我最同意影评所说,弄得最好的是Val Kilmer(新蝙蝠侠)演的黑帮和他老婆争执而又相爱的副线故事,Val Kilmor是“不折不扣的酷”,有枪没枪时都能把人毙了。
梦是不是更真实的心理现实
举这个例子是说,人们选择去看一部娱乐片,不一定因为片子十全十美。也许是拳打脚踢,也许是明星的魅力,也许是故事背景,也许是趣味;不管是什么,是为了娱乐。对好莱坞娱乐不必过于崇拜但也不必过于愤怒,其实它们是不是梦是不是话题,要听批评者言的是梦的意味、水准,梦的自我映照,梦的自我解构,梦的变形,梦与现实的折射对照。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会做某种梦?梦中有些东西是不是更真实的心理现实?分不清是梦是醒挺可怕,但一点不做白日梦的人其实也挺无聊。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幸而还有庄周、屈原一干人。一个民族总是要有梦的,只要知真知假,能进能出,有赞有斥,自我解析,反观现实,不长眠不醒就好。
我们现在还看《九歌》、《山海经》、希腊罗马神话,这也是梦。动作片我喜欢斯皮尔伯格的《印第安那·琼斯》、卢卡斯的《星球大战》,这种东西的妙处就是拍出了现代传奇、神话的辉煌感,没人要求它是真的。琼斯的故事大玩动作片模式又处处反讽,傻小子乐,聪明人也乐,这是高级娱乐。中国人的神话梦当代电影里也有,样板戏,李小龙,武侠,周润发,巩俐。“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之流行,其实反映了文革之后大陆人重塑民族神话的需要,它也的确是我们做的最辉煌最潇洒——尽管结局惨痛——的一个梦。满街小子们只知道找到了一种男性表达的方式,动辄喊一嗓子痛快痛快——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却不曾多想这个九儿“妹妹”其实是他们的奶奶,可以说也是我们常提的“祖国母亲”了。豪放之后,不知为何“我爷爷”的男性后代越来越没出息,越来越不光明磊落,接下去的可就都是恶梦了(《菊豆》、《火红灯笼》、《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写当代的戏则是“哥哥们”都不像丈夫倒更像是还没长大的儿子,“妹妹”恨铁不成钢之余只好孤独一人壮着胆往前走,还扶老携幼从没想过改嫁(《秋菊打官司》、《活着》)。这种显而易见的模式反映了什么?张艺谋的电影都是当代优秀男性作家作品改编,梦耶非耶,都是精神分析的好材料。这些电影中的“巩俐”既可说是抽象意义上的某种中国女人的代表,也可以作为“祖国母亲”的象征,而男人同她的关系——迷恋?依靠?赞颂?欲望?怨恨?同情?杀父?自虐?忏悔?西方观众与“她”没有这层关系,是站在远处用望远镜看,所以关心的只是影片所提供的另一种女性形态和生活故事,而中国的观众很难不与其中的角色发生认同(具体分析应该很复杂,在此不容多说),所以看着经常是爱恨交加、喜怒无常、五味杂陈。至于面对这样的民族残梦,最好的安慰恐怕就是读金庸看武侠片了:男人女人都可在那里找到自己的英雄和真性情。通俗流行受精英青睐不容易,金庸可是不分三六九等男女老幼,迷者如云,而且还要被北大授荣誉学位的。电影、文学和梦一样都是镜象的艺术:有时我们在镜中看到的是自己,有时是自己的梦,有时又是梦中的自己,正因为视角千变万化才如此迷人。
经过一番改革开放,人们面对八面来风又有了身份认同的意识,文化自我、殖民、侵略之类的词又被重新拾起了,说明我们的文化氛围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令人觉得很有意思。但我很怕特愤怒青年的那种,简单的语言,简单的对立,简单的逻辑之结果不用再体会一次了。不管有怎样的立场,最好多些混合一点的心灵,超脱一点的态度,复杂一点的语境,多方位一点的观察,全面一点的了解,冷静一点的行为,健康一点的心理,人性一点的观照之类。
票房再高的电影,也只是一部分观众爱看的电影,不能代表所有文化群落的趣味。伍迪·艾伦永远住在纽约,电影永远是在纽约拍,永远讲的是纽约的知识分子和犹太人生活,永远是小制作,永远是大城市部分影院放映,永远有忠实观众。这种电影与票房巨片代表的是不同的文化,它并不需要只看动作片的那批观众也能维持,这也是美国电影。
每一种创作都在某一种语境中实现,我们光看作品而不顾它的语境有时毫无意义,批评也是无的放矢。从前文的分析看,我们光用“造梦”来定义娱乐片没什么用处,因为严肃电影也未必就不“造梦”,电影本来就是一种虚幻。娱乐片的存在固然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美梦,但更多离不开人们需要“玩”的语境,是清醒着的“玩”,这跟做梦一样是摆脱现实,但却在人们的意识掌握之中,是有板有眼有规有矩地做梦,可以停止、休息、重复、评论。中国人对玩很看不上,似乎认为玩谁不会,玩还有什么讲究,玩有什么艺术,玩还分什么高下?这好像是有点像说吃是为了生存,只要吃饱了吃的东西有什么分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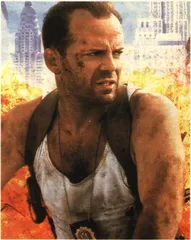
95大片《纽约大劫案》
我们为什么看不起“玩”
我们看不起“玩”,可是久不讨论这个概念了,恐怕连自己看不起的是什么都快搞不情。在中文里,玩如果用在成人身上,就有点贬义,不是指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游戏人生,就是指诡计多端,要不就是下里巴人。不管是褒是贬,最简单纯粹最正面的那层意思快消失了,好人都不玩,坏人才玩;正经人都不玩,没文化的人才玩。也许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说五音乱耳,五色迷情时就埋下了种子,固然有屈原记录了点南方山林的斑斓歌舞多情神怪——可是屈原投了江。不过,端午节赛龙舟的时候想,屈子毕竟是屈子,他的后人挺理解他,赛龙舟可说是我们民族诗人的族裔对中国人玩的一大贡献。
对一个民族的心理健康(包括严肃文化人)来说,娱乐片在内的有文化的玩也许是一种调整身心健康的必要形式。
好莱坞因为太会玩,靠玩赚钱混饭成了事业,怎么也停不住,变成一会儿不玩都难,自有惹人嫌、招人厌烦的地方,但不等于非要把玩批倒批臭。轮到中国人,光说玩物丧志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玩是人性中自然的一部分。小孩子的玩都要有章法规矩,成年人的娱乐更摆脱不了心智的参与,更跟生活中不能玩的部分纠缠不清,其实是挺不简单的事,玩出境界就更难了。最有规矩的成人游戏是体育,其规矩从“公平”的概念,到投入,到诚实,到真本领,非常有教育性。体育中的弄虚作假人们最难原谅,就因为它的原则首先是公平竞争,人们对冠军的无条件崇拜,也因为他们在公平竞争中体现了人类可以引以自豪的力与美。因为我们的文化中玩的概念已经名声太坏,流露真性情,摘掉假面具简直困难无比,不玩则已,一玩就“玩深沉”,把玩和深沉都污染了。其实,好玩需要一种认真,也需要一种艺术。看不上玩的人可能玩起来最没文化,或者没有分辨力把不该玩的拿着乱玩。先说什么是玩什么不是玩,何时该玩何时不能玩,哪种是有玩也有不玩,怎么才是聪明不俗引人入胜的玩,恐怕就够我们好好琢磨一阵子的。 动作片好莱坞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