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了你还不想睡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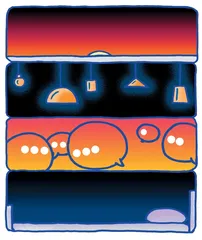
AC尼尔森最近进行的一项“全球睡眠习惯调查”显示,有1/4的中国内地受访者午夜之后才就寝,晚上22点至23点之间就寝的占1/4,在23点至零点之间就寝的占40%,在20点前就寝的只有1/10,在这个传统的主流上床时段里,绝对是弱势人群。
这个结果,显示午夜的电视时段有可能从传统的“垃圾时间”变成黄金时段甚至“黑金时段”,除此之外,惟一还能表明的,就是晚上不睡觉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不睡有二:不能睡,不想睡。不能睡是失眠,不想睡叫无眠。尽管失眠和无眠都是不睡,却有主动和被动之别,犹如失业和无业,失火和放火。接受调查的“不睡者”,显然是属于“不想睡”的,即不仅“天黑了你还不想睡”,甚至“天亮了还是不想睡”,与属于“不能睡”的失眠者基本无关,对于后者的调查,应属“脑白金”的分内工作。
为什么“不想睡”?(这个问题在尼尔森问卷里显示为“决定中国人睡眠安排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调查显示,62%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习惯”是最主要的因素,40%的人认为“工作时间”决定睡眠安排。特别是对20岁至40岁的人来讲,“工作时间”更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的睡眠安排。也就是说,决定“不想睡”的关键因素与其说是生理上,不如说是伦理上的。
几点睡是一回事,一个人所需要的正常睡眠时间,则是另一回事。虽然睡眠时间的长短因个体及年龄等因素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从4小时到10小时不等),但是主观或习惯上的“不想睡”对正常睡眠时间在客观上必定是只有缩短而不可能拉长。由“习惯”和“工作时间”决定的“不想睡”,正应了GDP曲线与睡眠曲线之间的反向关系,即GDP越高,睡眠值越低;GDP越低,睡眠值越高(这个公式大体不错,除了无法证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人都睡得很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古人的年度平均睡眠时间,大约在4370小时左右,每日大睡12小时,若以一生而论,几乎等于睡了半辈子。起码在上古或中古时代,中国睡情大致如此。清代以来,平均睡眠时间似乎逐步减少。李渔说过一个段子:“有一名士善睡,起必过午。先时而访,未有能晤之者。予每过其居,必俟良久而后见。一日闷坐无聊,笔墨俱在,乃取旧诗一首,更易数字而嘲之曰:‘吾在此静睡,起来常过午。便活七十年,只当三十五。’”很显然,在一部分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前夜,一个清代文人已倾向于相信,把半生时间用来睡觉,算是蹉跎人生了。
针对“全球睡眠习惯调查”的有关结果,AC尼尔森中国区董事长高恩分析说,“随着24小时昼夜服务的增多,全天候便利店重要性的逐步凸显,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中国人的就寝时间正逐渐被推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开始改变”。便利店、互联网,的确是导致“晚睡”及“少睡”的诱因,不仅“夜间动物”越来越多,在广州,甚至还出现了夜间动物园(我说的并不是夜总会)。然而在根本上,人类睡眠时间出现锐减的转捩点,与电力的发明和普及有关。
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汉代的部分中国人,非但有了“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觉悟,与之前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相比,后者还充分认识到夜间照明工具乃行乐之必要物质保证。1910年以来,发达国家国民的每晚平均睡眠时间由9小时减至7.5小时,当中数以百万计三班倒工人的每天睡眠时间更是少于5小时,主要原因,是工作与消闲活动所占用的时间愈来愈多。而使人类能将日间的“工作与消闲活动”继续到日落之后的重要技术保障,则正是“照到哪里哪里亮”电力。“帝力”不能干预的作息习惯,由绝对“够照”的电力一手摆平,照无眠。
电力使GDP翻番,电灯让人类不眠。美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表明,电灯发明以来,人类生活形态开始违逆大自然的节奏,人体新陈代谢逐渐失常,肥胖、糖尿病、心脏病、癌症和抑郁症等等,皆与此有关。因此,这些疾病的治疗之道也就再简单不过,四个字:熄灯上床。当然,大幅度提高电费,也未尝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在原油价格和睡眠时间之间,不知道是否也存在着一种反比关系。
塞万提斯说:“人睡而平等。”事情也许本应如此,然而历史的经验却无数次地向我们证实,就以GDP为核心硬指标的全球化竞争而言,世上最不平等之事偏偏就发生在睡眠时段——准确地说,就是有的人睡了,有的人还没睡,甚至还不想睡。不想睡,就会做些什么,生产些什么。若以公平起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这句话,则应易一字而作“卧榻之侧,岂容他人不睡?”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当亚洲睡狮一旦变成醒狮之后,想让我们天一黑就集体洗洗睡了,哼哼天底下哪有这等便宜的买卖? 不想睡眠天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