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铁4号线:开往融资的春天?
作者:贾冬婷(文 / 贾冬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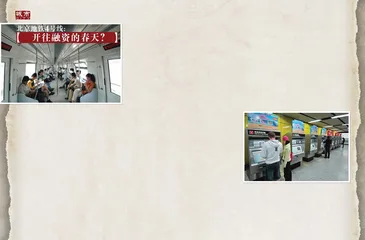 ( 在香港地铁里, 几乎看不见工作人员,均是无人售票 )
( 在香港地铁里, 几乎看不见工作人员,均是无人售票 )
638亿压力下的融资转变
近些年,北京地铁的发展已跟不上这个城市的国际化大都市雄心。一位曾参与申办2008奥运会的北京奥组委的宣传官员回忆说,2001年申奥时本想把地铁线路图绘入北京城市交通图,后来见到竞争对手巴黎的地铁,那真是一个庞杂又美丽的地下宫殿,拿一张巴黎地铁图,你可以到达城市的任何地方。与之相比,仅由1号线和2号线构成的北京“地下血管”太稀疏了。
申奥时或许可以避开,2008年的奥运承诺却必须面对。到2008年奥运会召开之际,北京需新建地铁4号线、5号线、10号线、八通线、奥运支线,全长120多公里。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灏2001年调入北京地铁集团负责融资,摆在他面前的是638亿的资金缺口。“638亿,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全盘推给财政是不可想象的。”令王灏印象深刻的是,1号线的延长线、复兴门至四惠的建设,因为70多亿的资金无法筹措到位,前后竟然用了10年。
有人用“挖出来多少土,扔下去多少钱”来形容地铁投资的巨大,事实上,目前地铁已陷入“建得越多,亏得越多”的循环,在对地铁数量和质量越来越期待的同时,是政府财政和地铁运营公司的疲于奔命。运营30年的“老线”1号线和2号线2002年运营一年亏损2亿元,依靠财政补贴才勉强度日,而2003年贯通的“新线”13号线也没有摆脱这一命运。
北方交通大学肖翔教授认为,这是一种体制性亏损,“地铁每公里造价4到6个亿,一条轨道交通线路上马动辄几十个亿,上百个亿,建成后运营成本也不低。但是,作为公共运输交通,轨道线路具有的公益性,决定了其票价不能完全按照市场来定价,这也就注定了其运营起来是一定要亏损。目前除了香港地区,全世界的地铁都是不盈利的赔钱买卖。”
“解决亏损就必须改变轨道交通目前的融资模式与运营模式。”肖翔介绍,目前我国的地铁建设基本采取由国家担当投资主体,其余靠政府担保下的银行贷款、政府投资等融资,尚没有能吸纳社会其他团体和民营资本进行多元化融资。单一的国有运营,也导致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捆绑在一起,从而造成巨额亏损。
此次的地铁4号线是融资模式转变的第一次试水,未来还有5号线、9号线和10号线等几百亿的大单,对社会资本,这是巨大的商机,对政府,也是减轻投资和运营压力的有效途径。王灏介绍说,过去北京市地铁采用的投资模式是市、区两级政府共建,资本金由两级政府或两级政府所属的国有企业负责,即将或正在建设的几条地铁新线,政府及其所属企业只保证40%资本金到位,剩下的60%资金则利用银行贷款、企业债券、信托工具或其他金融创新的工具获取。
公私合营:引资游戏还是解困出路?
4号线总投资约153亿元人民币,其中七成约107亿元由北京市政府出资,合营公司总投资约50亿元,香港地铁和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各占49%,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占2%。
这一合营联合体进入4号线项目,不仅是50亿元的资金注入,更重要的,是希望在长期靠财政补贴的“准公益项目”中引入竞争机制,形成政府和公司的良性博弈。
这也是王灏所倡导的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营)模式希望达到的效果。他介绍说,PPP模式主要为了完成某些公共设施、公共交通工具及相关服务项目的建设,公共机构与民营机构签署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达成伙伴关系,以确保这些项目的顺利完成。这一模式的实质是,把项目投资分为公益性与赢利性,公益性部分由政府投资,赢利性部分吸引社会投资,从而扩大资金来源,提高资金使用率,降低投资风险。
王灏认为,地铁虽然投资量大、回报慢,但对沿线经济的拉动很大,某种程度上来看,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他曾做过一次调查,从13号线的建设开始到结束,以周围2公里范围为界,选取了55个样本,结果发现,每平方米房地产空间上拉升81元,时间上拉升500到1000元。从经营城市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建立科学的补偿机制,将地铁外部效应转移到地铁建设上来,才是冲破地铁亏损困境的关键。
根据协议,北京市政府将负责轨道的土建工程,特许公司负责4号线的车辆、信号、通信等主要设备的投资建设,并在30年的特许经营期内负责线路运营和管理,在特许经营期结束后,特许公司将项目设备无偿移交给北京市政府。一个理想的互动模型也已经打造出炉,经营性收益由公司优先获取,多获利的部分,公司会以租金的形式补偿政府,而因票价收益、客流等带来的损失,也会由政府补偿公司。
“这种上下分离模式的最大优势是政府和公司责任明确,政府财政压力减小,功能可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公司负责商业化营运,效率更高。”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指出,“但是,如同所有的社会资本进入公用事业所要面临的,模式的搭建容易,而如何保持它的长期维系和发展,关键还在于稳定有效的第三方监管机制的建立。比如,成本的核算,票价的制订,普遍服务义务如何体现,对于正在建立中的监管机制,都是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提到西直门地铁站的换乘,从地铁换到城铁13号线,或者从地铁换乘地面公交,“就像在迷宫里绕”。“还有一些地铁口的朝向和位置,不是为行人方便考虑,而是被附近某个地产项目所影响。在地铁这样的公用事业中引入社会资本,更要注意政府和商业机构的良性关系,政府如何保证票价等公众利益不被侵害,商业机构如何维护自己的决策权,而不仅仅充当引资工具。”
香港地铁的北京角色
在三家公司组成的合营联合体中,香港地铁公司的身影尤其引人关注,这个地铁盈利神话的缔造者,能给北京地铁带来什么转变?
香港地铁自1979年底逐段投入运营,到2000年转为盈利,成为世界上惟一地铁投资盈利的公司,创造了独特的“港铁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其实是“地铁加房地产”,香港地铁在兴建路线时,需要土地作地下隧道及地面车站等,而这些土地就会根据政府及地铁公司的协议,由政府拨给地铁,作为“地铁用地”。以香港机场铁路为例,铁路还没建成,房地产已开始分期建设及出售,部分地权售予私人发展商,每次卖楼可取得大额的物业收入,迅速降低债务水平;再把营运上的盈利,用来支付利息及继续还债。在没有经常性的政府补贴下,财务依然得以保持稳健,有能力持续发展,开拓更多路线及相关业务的商机。
香港地铁公司对外事务经理苏雯洁告诉记者,在利润链条中,房地产物业开发投资回收期长,另一部分则是经常性收益,主要是车票收入,随着乘客数字及每年车费的增加而增长,还有约15%左右的收益来自通信、广告、商铺等。相比香港地铁形成的一条龙产业体系,北京地铁的盈利模式单一得多。那么,港铁资本的进入,能从根本上转变北京地铁的运营和回报机制吗?
原铁道部经济规划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文力认为,香港地铁有其特殊性,很难在其他地方全盘复制,北京的城区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商业房地产开发很难涉足其中。事实上,在建中的地铁4号线全长29公里,南起北京丰台区南四环路马家楼站,北至海淀区龙背村站,全线共有宣武门、西单、西直门、中关村、颐和园等24个车站,由南至北穿越北京丰台、宣武、西城和海淀4个区,是贯穿北京城区南北的轨道交通主干线之一,已没有发展地铁沿线房地产的先天可能。
而票价制订权,因涉及公众利益,还将控制在政府手中。短期内,随市场浮动的票价制还无法推行,一度风传的北京地铁改3元一票制为按里程计费的消息,曾引起市民激烈反响。
剩下的就是经营性收益了,这也是香港地铁公司行政总裁周松岗明确提及的部分,“在建设运营期间,将发挥香港地铁的优势,采取一些非票价方式,如在车站、车厢内设置广告和建立一些零售商业设施获得利润”。但从世界范围来看,这部分能扩展的相关业务不多,对利润的抬升空间也不大,如能贡献收益达10%到20%就不错了。
文力认为,香港地铁进入北京,更主要是扮演一个战略投资者的角色,为未来更大的市场和更深入的涉入探路,对于目前的北京地铁来说,是专业的管理和服务的引入,而更深刻的转变,现在还言之过早。 香港地铁投资王灏北京交通开往融资号线春天北京地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