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入制度只是一个开始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朱步冲)

三联生活周刊:请问在刚刚结束的沈阳全国2004年器官移植研讨会和维也纳世界器官移植大会上,专家们在推进中国器官移植的制度化方面达成了哪些意见?
陈忠华:在沈阳会议上,只是卫生部的黄洁夫部长以个人名义做了一个涉及器官移植伦理学与法制化的报告,专家还没有就此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在参加维也纳会议的3350名各国代表中,有47名中国大陆方面的专家。理事会就中国器官移植中存在的严重非法买卖现象提出了强烈批评,我个人在沟通中强调,虽然我们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些个别现象绝对不代表中国社会与政府的实际情况。
三联生活周刊:请问您是否参与了正在酝酿推敲中的《器官移植准入制度》的制订?如果有,能否描述一下您具体负责的范围?
陈忠华:现在有些媒体舆论非常心急,把正在由专家讨论的医学标准,或者法规的草案,当作已经或正在成型的法规法律,这是非常错误的。这个制度的制订必须由国家卫生管理部门作出决定,我们学术团体只是给出自己的意见,我们没有实施决定的能力。媒体中提出的所谓“自愿捐献,知情同意,自主决定,非商业化,公平公正”这些个标准不过是国际上针对器官移植问题的一些共识。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管理条例,就是在长沙、北京会议中指定的脑死亡诊断标准,这还是一个讨论稿,没有形成条例或立法。而在器官移植的管理方面,更没有任何公开条例。我个人认为,如果要实现器官移植的制度化,就需要做到“四化”,制订出四种法规,四个法规是指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条理、包含准入制度的器官移植管理条例、器官捐献管理条例和器官移植伦理学指南,四化是合法化、公开化、国际化与正规化。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国家立法与加强监管。
三联生活周刊:有些专家认为,未来规定的器官移植准入制度应实行脑死亡与心脏死亡双重标准,请问这个双重标准对于器官移植的监管与实施有什么样的影响?
陈忠华:这个双重标准其实上是一个医学判定标准,人可以自由选择接受脑死亡或心脏死亡为死亡标准。比如我们同济去年就做了一例,一位深度昏迷、利用呼吸机维持生命的病人家属表示选择脑死亡,新标准也算是完善了器官移植的伦理基础。只要器官来源非法化,那么我们就无法做到管理公开化。
三联生活周刊:卫生部近日作出决定,考虑将三甲医院评定与是否能做器官移植脱钩,请问这个决定将对中国器官移植的整体医疗水平和监管有什么影响?
陈忠华:器官移植确实不应该成为评判医院水平的标准,许多医院为了评级,自己,或者聘请专家做了一两例移植就不再做了,评上后一旦有人要求手术又不拒绝,这样的恶果是自身的医疗水平根本没有得到持续发展,也损害了患者利益。
三联生活周刊:“推定同意”原则对于器官移植制度化的作用是什么?中国需要作出那些努力,才能达到实施这一原则的要求?
陈忠华:推定原则的核心是,只要患者符合脑死亡标准,那么除非他生前在某些政府管理机关登记做出声明,就假定他成为了器官志愿捐献者。实施这个制度的国家主要有新加坡和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它最大的益处就是容易管理,并能够实现器官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不过这个制度距离中国还是很远,近期内根本达不到,这不仅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没有出台规章制度的缘故,更是因为中国社会大众的自主捐献意识还达不到这些国家的水平,需要政府对民众经过长时间的教育和宣传,才能考虑推定原则的实施。
美国的《脑死亡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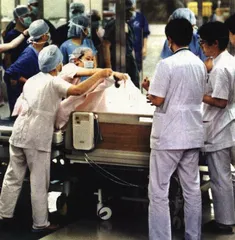
我国器官移植目前在数量上已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我国器官移植的情况

1968年,美国哈佛医学院已率先公布了脑死亡标准,确定了“不仅呼吸和心跳不可逆性停止的人是死人,而且包括脑干功能在内的所有脑功能不可逆性停止的人也是死人”。这就是说,患者如果已经脑死亡,即使靠人工设备仍能暂时维持心跳和呼吸,实际上已被视为死亡。这一概念已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1981年,美国通过了“脑死亡法”,当今世界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也都立有此法。但在我国,法律上对死亡并没有明确定义,而是遵循医学的解释,仍然把“心跳、呼吸停止”作为死亡的惟一标准。而对于器官移植来说,脑死亡的捐献器官的质量通常较高,移植效果好,采用通常死亡概念(呼吸,心跳停止)死者的捐献器官则质量较差,有的已经不能使用了。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的法律真空
李翊
器官移植是本世纪医学科学发展的最重要成果之一,许多危重病患者通过器官移植重获新生。在我国,器官移植近年来发展迅速,规模正在日益扩大。据国家卫生部统计的数字显示:截至2003年,我国累计完成器官移植5.5万余例。其中,肾移植5万多例,目前每年完成超过5000例;肝移植3000多例,仅去年就完成1500例。从总体上说,我国器官移植目前在数量上已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然而,在器官移植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相应的立法却几乎还处于真空状态,相关法律不完备成了制约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的瓶颈。2003年12月中旬,以“肝脏移植”为主题的东方科技论坛第36次学术研讨会上,国内器官移植方面的专家一致认为,我国“肝脏移植”中的最大问题是器官来源严重短缺,尸体供肝质量较差,而其原因则是我国对死亡标准的认定仍限于呼吸、心跳停止的临床死亡,脑死亡立法滞后。面临同样问题的不止是肝脏移植,还有肾脏、角膜等其他器官移植。对此,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黄洁夫教授说,“在这种状况下,如果相关标准、法规建设跟不上,就可能出现大问题”。
在立法缺位的情况下,一方面是众多有意捐赠人体器官者捐赠无门;另一方面是更多急需移植器官的病人因没有器官可以移植而不得不忍受病痛折磨。一方面是有意捐赠器官者死后因家属强烈反对遗愿难以实现,另一方面是医院害怕引来各种纠纷,对人体器官捐赠顾虑重重。一方面是志愿捐赠者无法面对繁杂的手续和各种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是非法人体器官买卖在暗中悄悄地进行。
黄洁夫在题为《肝脏移植的管理和有关立法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就器官移植整体水平而言,我国在术后远期生存率、基础与应用研究创新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造成上述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律法规建设与管理的滞后:一是缺乏技术准入制度,使得“肝脏移植”呈现分散混乱、无序竞争状态,使供体趋于紧张。二是监督管理不力,移植供者与受者的界定与权利义务不明确,移植中器官的选配、摘取、保存等环节应遵循的规则不清,对通过不良途径获取器官的行为失去控制,器官分配有失公允,供体器官不足、无保障机制,同时又有浪费。黄洁夫认为,目前我国相关立法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立法的指导方针应以我国器官移植现状与国情为基础,借鉴国外器官移植管理经验,遵循国际公认的伦理原则,体现人文关怀精神。立法宗旨应以治疗疾病、挽救患者生命、合理有效使用卫生资源为目的。遵循的立法原则应包括自愿捐献、知情同意、自主决定、非商业化、公平公正、人文关怀、技术准入等。同时,器官移植中的死亡判定标准应接受脑死亡概念,将脑死亡纳入死亡范畴,对死亡定义予以补充和完善,实行“两种标准并存,两种选择自主”的方针。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法学专家刘长秋更是对我国未来器官移植的法律体系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他认为,未来我国器官移植法律体系中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法律或法规:《器官移植法》、《脑死亡法》、《遗体捐献法》、《器官移植技术安全操作法》、《医用器官卫生标准》,以及其他立法的某些相关规定,如《民法通则》关于生命健康权以及身体权的规定等等。上述立法共同构成未来我国的器官移植法律体系,并分别在其中发挥各自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