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波民企建研究院之路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尚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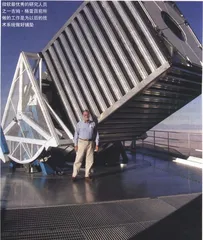
微软最优秀的研究人员之一吉姆·格雷目前所做的工作是为以后的技术系统做好铺垫
“中国企业创造的GDP是日本企业的1/3,而能耗上却几乎相同,技术研发是最重要的差距。”经济学者张欣告诉记者,“目前国内电器企业在DVD、背投电视等方面掌握的技术,都是90年代逐步从日本获得的,但是这种获得以后未必还会有,我们不自己研发几乎没有出路了。这就像50年代的航空制造一样,在抗美援朝中获得的米格15和米格19虽然当年很先进,但是当60年代没有新技术输出给我们时,整个70年代天空上只能用不断改进50年代的技术应付。”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1996年中国的研发支出仅占GDP的0.6%,现在这个数字增长到1.1%,而所有的研发资金来源中,只有39%来自政府,61%都是企业行为。2001年10月11日,曾经进行过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科技统计调查,结果
2000年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为896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已达到1个百分点。这个投入强度虽已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但却仅相当于一个微软加一个英特尔。企业替代政府承担新技术产品研发载体,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夏新研究院的院长李晓忠解释道:“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有它天然的优越条件。企业位于市场最前端,灵感来源于需求,企业从一开始便在科技创新领域中占据了先机,争当新技术需求的最先捕获者。其次,企业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之下,有内发的巨大动力使它自然而然地成为新技术发展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出资者;而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它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保证研发的持续性,对于科技创新而言,坚持不懈的投入至关重要。”
英国《金融时报》的西蒙不久前在《微软创新走老路》的文章中对微软研究院所引发的研究院现象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上个世纪60年代杜邦、通用电气、施乐、葛兰素等企业都通过专门研究院的方式在商业和技术上突破。但是80年代思科、甲骨文、英特尔和诺基亚却并没有依靠自己研究的方式,而是靠收购,同样取得了类似的商业成果。而目前全球只有微软特立独行地在使用60年代的招募科学家模式。譬如微软研究院的研究员吉姆·格雷正在忙于将世界各地的天文学数据库连接起来,构成他所称的世界望远镜,这项技术看似与微软的具体产品并没有具体关系,但是却在为20年后的大型分布式计算系统积累经验。爱立信中国总裁杨迈告诉记者:“有的企业在进行前端研究,譬如微软和IBM,还有的企业在将这些前端技术转移给大家,那就是爱立信,而还有一些企业在此后会把这些技术想法设法做成新产品,夏新等企业将会承担这样的角色。”李晓忠解释道:“国内的企业都已经注意到技术积累这个问题,但是具备研发气质的却并不多,即使是相同量级的企业、环境相同的企业,所作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企业可能觉得投入研发方面太多资金是不合算的。甚至很多企业依旧寄希望于走10年前的完全模仿路线。只有成立研究院这样的专业机构,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被动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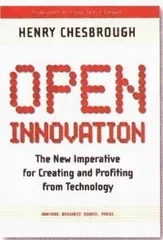
《开放式的创新》
实际上,与国际的企业研究院相比,国内这波研究院热潮更趋向于将技术转化为产品的工程院,而不是国际上简单意义的纯研究机构。经济学者张欣则认为国内研究院走工程院路线是折中的趋利策略,因为像夏新、春兰这样的企业去投入大量财力精力去研发10年后的技术并不现实,而着眼于三至五年的技术更具有经济效益。不久前约翰·科特撰写的松下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研究传记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借鉴。因为松下在50年前的景象与今日国内很多电子类企业非常的相像,约翰·科特这位哈佛商学院领导学讲席教授创造了“商业领袖与技术人文主义者”的概念,他在接受《纽约时报》读书版编辑的采访时说:“松下代表了这50年日本企业保持强大竞争力的原因,尽管我们之中的很多人仍然瞧不起来自远东的商业人士,但是这些东方商人却给西方现代企业提供了不同的案例样板,我没有看到松下有类似著名的贝尔实验室那样的能力,但是却看到他们对于实用前端技术的强大改良能力。”
此前采访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现任微软亚洲工程院院长张宏江时,他也提到了开发中的实际效用问题,他告诉记者:“当‘神州五号’上天时我马上打电话告诉我在美国的儿子,但是他们却并没有类似的兴奋,他们在美国感觉发射载人飞船升空,是很平常的并不新奇的技术,但是却并没有意识到航天技术的非排他竞争性。这就是我们今日做企业研究院的初衷。”哈佛大学出版社不久前出版了亨利·切斯布洛的新书《开放式的创新》,其中有一章亨利·切斯布洛特别探讨的企业研究院问题,在他看来,美国的企业研究院更多的承担了斯坦福大学这类理工院校的职责,而亚洲的企业研究院则更像大学里面的技术小组。夏新研究院的院长李晓忠并不像很多研究院那样避讳非研究院而是工程院的看法,他说:“工程院是出成果的地方,没有研究院这类机构的基础技术提供是不可能存活的,但是国内企业是很难有实力既做研究院又做工程院的复合研究开发,所以做工程性质的研究院更适合现实需要。”
而在《约翰·科特眼中的松下幸之助》这本书中则在企业研究院以外,又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松下创办的日本工业设计奖在技术设计领域颇有声誉,被视为像诺贝尔奖那样富有理想和人文色彩,但却又充满技术味道。尽管管理学者费尽笔墨将松下幸之助描绘成一位管理企业的专家,但是当1961年《时代》杂志采访松下幸之助时,松下却对《时代》记者说:“我想研究人性。”经济学者张欣解释道:“正是始托于研究技术本身的工业产品设计奖项,大大激发了企业技术人员,尤其是年轻人的设计潜力,这远非一种激励机制那么简单,就如同现如今抱着电脑试图做点什么的年轻人一样,20年前,抱着创造点什么新奇玩意的想法,无数人走向了这条工业产品设计之路。研究决不是一个企业推动那么简单,研发的气质是一个社会的取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