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228)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杨不过 老蓓 耳耳 袁越)
利多斯特发现
杨不过 图 谢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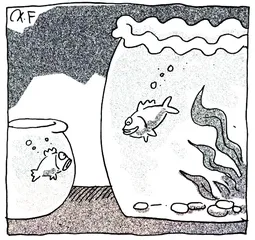
作为一个学文科的人,我一向不大瞧得起自己,觉得研究天体物理人工智能之类的人才值得崇拜,认为那才是对人类真正有用的学问,相比之下拿漂亮或者机巧的文字换口饭就容易多了。
但这个观点最近正被我自己推翻。我忽然发现,文学大师还是有过人之处的。某些情感在没领会过的时候认为是扯淡,但在某一刹那,自己会恨不得像秦王那样醍醐灌顶地大吼一声“我悟到了”。
最初看米兰·昆德拉的《笑忘录》的时候,对其中大段论文似的论述没有什么感觉,尤其是关于利多斯特。这是一个捷克语词,昆德拉说,在其他任何语言里都没有与其对应的词。我对这说法不屑一顾,觉得他故弄玄虚。
有一阵子我在一家很烂的杂志社工作,不过挣的钱还不算太少,所以也就勉强呆着。偶尔出差的时候我去见了一个非常喜欢的人,去了他在高盛公司漂亮得吓人的办公室,他显然如鱼得水,然后告诉我下个月要去纽约培训。我估算了一下,他的薪水大概是我的十倍。这时候我忽然感受到了那种叫做利多斯特的情感。
这绝对不是嫉妒,谁都不会嫉妒一个自己喜爱的人。也不是羞愧,他总自嘲自己是苍白的写字楼动物,觉得我过得很洒脱不羁,他以为我是那种天天带着笔记本电脑到咖啡馆写爱情小说的人,还对我羡慕得很。
昆德拉的解释是,利多斯特是由于突然洞察自身的悲惨而产生的一种极度痛苦。他说,治疗个人悲惨的标准药剂之一是爱情。而爱情实际上是一种要求彼此完全统一的欲望。比如说,你不愿对方有美好的过去可供回顾,说得残酷一点,你愿意对方生活在凄惨之中,而你是他悲凉生活中的一轮红日。
这样子看待爱情,似乎有点不够高尚,但人在成长过程中卑劣的一面会渐渐挥发出来。我还记得,《玩笑》里女主角爬到监狱的铁丝网上给爱人送一束鲜花,但最终是要我们知道,那些曾经被讴歌的爱情与青春,到头来都不过是玩笑一场。我曾经痴迷于动人的情话,后来才明白,在熟练掌握之后,语言只是一个技术问题。美则美矣,毫无灵魂。
那个故事里,城里的学生暑假时候在乡下勾搭上了屠夫的老婆,那个女人把他当作艺术的化身来崇拜。但当她偷偷到城里来看他的时候,发现她心目中神圣的爱人只不过是个穷学生而已。他出了丑,浑身涨满简直要爆炸的利多斯特。
我运气好一点,并没有出什么丑,可是我自觉地逐渐疏远了他。我想,到最后我们谁都不会记得,在十六七岁的年纪,我们曾坐在体育场看星星,两个人说起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相顾无言。这些陈芝麻烂谷子,还是忘了的好。
洗澡
老蓓
北京有句老话,说“三代为宦,方懂穿衣吃饭”。讲一个人若要培养起自己的品位,起码需要三代积累。洗澡也是如此。在这儿笔者要说的不是南方人所谓冲凉,也不是女士们的花瓣浴、牛奶浴等,而是天子脚下几代人造就出来的北京爷的澡堂子。
俗话说:“清汤面,浑汤澡”,讲究的是面要吃早上头一锅煮出来的,清汤挂水,吃的一个鲜字。而泡澡则绝对要等到夕阳西下,享受那被别人泡了一天的浑浊的池水。据说这样的水很软,不伤皮肤。在下澡池之前,一定要扯着嗓子喊一声:“好——!”大概是对极热池水的刺激的向往吧。但是地道的北京爷这一声定会喊得底气十足,撕心裂肺,不输给任何一个叫卖大王。待泡到浑身酥软的时候,便可以找师傅搓背了。师傅一定是扬州的最正宗,先是卷毛巾卷,毛巾在手上转几圈,最后留出个角往手心里一别,保证中途不会松动。然后在毛巾上沾一半冷水,举到被搓人的头顶,“啪啪”拍那么两下,铿锵有力,水珠打在人的脸上,你就知道,要开始了。就像全聚德的师傅片烤鸭,先要片下三片鸭胸的皮一样,搓澡师傅也会先在你背上横竖搓三下,以拉开架势,然后才开始正式搓。据说整个搓澡程序是有严格的位置及数量概念的,具体如何操作那是人家吃饭的家伙,笔者不得而知。但是笔者的一位朋友曾经有过这个的尴尬:此人在搓澡时要求师傅在某个位置多搓几下,遭到严厉拒绝,被告知不能坏了规矩。朋友百思不得其解,问加钱还不行吗?答曰:不行。又问,那我重新搓一遍呢?答曰:明天请早。如此古怪的规矩令朋友很困惑,但同时也领教了扬州师傅的厉害。据其描述,所有被搓下来的污物都整齐集中在肩窝处,在翻身时,又被不动声色地转移至腰眼。最后起身,床上没有一粒“漏网之鱼”。
北京的甘家口浴池是早年非常出名的,当时有名望的板儿爷及混混都曾在此宽衣解带,地位之显赫不下什刹海溜冰场和莫斯科餐厅。甘家口浴池还是北京最早经营桑拿浴的地方,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某天他正和几个朋友在小木屋里美美地蒸着,忽然闯进来一个人,拿着一瓢水就要浇,朋友不客气地制止,日:这儿都是“清蒸”。那人觉得冤枉:没碍着你们“清蒸”啊,我浇的是水,又不是酱油。
肇事方
耳耳 图 谢峰

那是一条通往金山岭长城的大道,平整而宽阔,阳光明媚,前方的一切尽收眼底:两边是青山,秋草在太阳下泛着金光,好像当年一个作家就躲在这里写成了《金光大道》。一些农民伯伯在修马路牙子,其中一个戴着白毛巾的端着一杆铁锹站在路旁,就像端着一挺机关枪的武工队员,就等我的车过去……
“吱——砰!啪!”车里顿时漆黑,挡风玻璃上盖满了沙子。在最关键的时刻,我的车仍然没有偏方向,停住时也没有熄火。是的,出车祸了,几秒钟前,那个戴白毛巾的农民伯伯在我距他只有十来米时突然决定冲锋到马路那边,他的身体像特技演员那样被车头挑起来,落在引擎盖上,又翻落在地,手里机关枪一样的铁锹把黄沙整个拍在了我的挡风玻璃上。打开车门,他就躺在距我车头两米远的地方,抱着脑袋,血一滴滴落在柏油路面上。
一个小时后他躺在密云县医院,是我送去的,没有了现场,那个鬼地方手机都没信号。老人76岁,他那坚硬的胯骨让我钦佩中国农民顽强的生命力,除了皮外伤,他就是用胯骨撞瘪了我的车帮子,造成骨盆内陷,算是骨折的一种,其他地方完好无损。村里人说,平常老爷子一百多斤的水泥包夹起就走,健步如飞,中午还喝了半斤多二锅头。
老爷子没有子女,一个养子来了,警察做笔录的时候,问“谁是肇事方?”我和那个老实巴脚的中年农民都答应“是我”。警察问我:“怎么是你?你不是撞人的么?”是啊,撞人的不是肇事方么?养子说:“我是他儿子。”警察给我看笔录上的登记,搞半天老爷子的名字是“赵世芳”。
作为肇事方的我和赵世芳的养子开始了马拉松谈判。那养子的确想多要点钱,但他的方式非常敦厚,我的条件他不答应,但自己又说不出个所以然,于是不停地抽烟。望着他饱经风霜的黑黝黝脸膛,我只有让他考虑。在一个多月过程中,我不停地去医院看望赵世芳老爷子,告诉他别担心,医院的一切费用都由我来。我还把桔子剥了送到他嘴里,老爷子眼睛里泪花闪闪。
我和赵世芳的养子最终在15000这个数字上达成了一致,因为没有人会给76岁的一个农民开出让保险公司相信的误工费证明。卷着裤管的生产队长在地里干活,被大喇叭叫回队办公室签字,骡子拴在门口。等我把厚厚一沓人民币递到养子手里,他激动得不行,他们全家一年辛苦下来也没这么多钱。他两手在裤腿上拼命擦了擦,才开始一张张数,赵世芳老爷子就躺在隔壁灶间。数完,他媳妇儿已经把一方桌菜做好,硬要留我吃晚饭,逼我喝酒,边喝边回忆一个多月来我们的交情。
临走,他们往我车后备箱里塞了一口袋小米,一口袋板栗,一再嘱咐:“一定来玩啊,一定要来。”
鬼魂说话
袁越
美国有一种职业,英文叫Psychic Counselor,姑且翻译成巫婆吧。她们声称可以通灵,所以能够替阴间的人给活着的亲属传话儿。我不信神,但出于好奇,我旁听了一次这样的“对话”。我想问问巫婆鬼魂们都说哪国话,因为我一直认为《圣经》不用中文写,那就说明上帝不在乎俺们中国人,所以我也就不用去信了。
“对话”发生在我的一个朋友家里。巫婆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太婆,得过癌症,头发在化疗后都掉光了,人也瘦得不成样子。当她知道我是中国人之后,便对我说,鬼魂用的是阴间的语言,她能听懂。然后她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告诉我说这屋子里有许多鬼魂正争着跟我讲话呢。
“我有一个叫刘思佳的朋友几年前死了,我想问问他是否喜欢我送给他的那本挂历。”我问她。
“他正好在我身边,他说他很喜欢你送的挂历。”之后她又开始描述我的亲人们生前生活过的地方,她提到了小村庄,村庄前的小石板路,屋子里挂着的一把雨伞以及一只老怀表等等,甚至还提到了西藏,说我死去很久了的外公想让我去西藏看看。我心里明白,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普通美国人所能知道的有关中国的一切,这些东西在我听来却很不靠谱。
大概她也意识到和我的对话不太容易进行,便很快便转向我朋友。她随便说了一个名字,我朋友立刻惊讶得大叫起来,原来这正是她姑妈的名字。
“她问你好呢!”巫婆说,“她说自己在阴间过得很好,叫你不要担心。”
她们俩聊了一个多小时,巫婆告诉我朋友,她的那些亲属都在阴间快活着呢。可我在一旁听得仔细,知道这巫婆只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学家而已。她总不把话说实,而且总是围绕着儿童玩具、宠物和衣服等常见的东西说事,猜中的可能性很大。不过,我的朋友却一直听得很专心,显然比我投入多了。最后她拿出100块钱,千恩万谢地送巫婆出门。
我望着巫婆佝偻的背影,突然明白了一件事:鬼魂们说的其实都是“人话”。人是有感情的生物,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巫婆们传话来告诉我们,我们死去的亲人们一切都好!刘思佳啊,请原谅我用了你的名字,虽然我从没有送给过你什么挂历,可我真应该送你一本的,上面有你喜欢的云南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