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个地方会出问题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于)


秦海璐(饰方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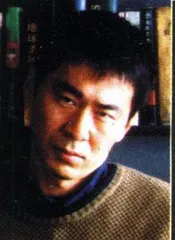
陈建斌(饰欧阳云飞)
方芳想作空姐,但色弱;欧阳云飞是名诗人,却再也写不出诗来。方芳说,想要去做一件事时——
《像鸡毛一样飞》试映时,据报道有观众退场,原因是实验性太强。孟京辉说有人不接受是件好事。这部电影的名字很早就传了出来,不少人期待着看一个个性和创作风格如此鲜明的话剧导演能拍出什么样的电影来,但孟京辉对观众的反应却没有什么期待。因为,正像他在《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演出后说的那样:“你根本不知道观众是谁。”在为这部电影而作的采访中,孟京辉说了同样的话。
影片开头就让没有任何准备的观众吓了一大跳——巨大的马雅可夫斯基光头像紧紧盯着观众,忽然一个西红柿或者鸡蛋样的东西砸到他的额头上,“砰”地一声。紧接着切欧阳云飞的近景,他的头上也挨了一下。再接着就是欧阳云飞一段恍恍惚惚的经历。他到北京看一个朋友,结果拿错了包,能确定身份的证件丢了。后面的事情几乎全都贴着荒谬走,像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梦,中间夹着一个略带伤感的爱情故事。
欧阳云飞的朋友陈小阳不写诗了,摇身成为时代弄潮儿,登上各种封面杂志,还当过IT精英。现在开了一家养鸡厂,专养下黑蛋的黑鸡。他穿着黑西装、白衬衣,带着黑墨镜,站在雪白的池子里迎接欧阳云飞,脚下是一群黑鸡。小镇里的人都有点奇奇怪怪的,当欧阳云飞在街道上走的时候,他肯定以为自己走在梦里,雪白的小镇街道,巨大的飞机从头顶飞过。小镇也没有别的人,除了骑单车路过的方芳,一个热爱诗歌和诗人的姑娘。不能写诗的欧阳云飞痛苦,他还想满足方芳对他的希望,一个卖盗版的人成全了他。他用程序写出一首一首的诗,成了名人,却发现人人都知道了他的秘密,都从卖盗版的人那里买光盘。最后,陈小阳不见了,方芳也走了,飞机的航向也变了。
把影片整理整理,也能说出这么一个故事来,但实际上,《像鸡毛一样飞》的故事很稀薄的,但与影片情绪有关的画面,其实也是影片的中心所在。欧阳云飞的恍惚几乎全部靠镜头语言交代出来的,在机场办公室里,他说他是诗人,办公人员满面惊异,一个人说他知道一个诗人高尔基,另一个说高尔基不是诗人,李白才是。镜头就架在欧阳云飞脑袋后面,观众就看见演员的半个后脑勺渐渐后退,离那两个人越来越远,两个人虚焦至一片模糊。当方芳对欧阳云飞说“你是我的颜色”时,画面突然跳到河边一片青草上。影片里有很多拍得很漂亮的画面,方芳站在大片的土地上,飞机从她头顶飞过,落下巨大的阴影,掠过银幕。孟京辉慨叹:“你说那飞机得飞多低才能有这样的效果。”
也许正是这些画面隔离开了一些观众。普通的观影习惯是寻找故事,尤其是看惯影碟的人。除画面外,《像鸡毛一样飞》里主人公的情绪也很难在大范围里引起共鸣。它是一部追求精致的电影,很多声效处理上的细节都故意藏在影片里。欧阳云飞的困境是一种普遍状态,但他的表达的方式却不是普遍的。那是一种整理过后、有一定品质的东西,是一部分人能体认的感受,却因之少了力量。孟京辉的话剧《恋爱中的犀牛》是一部缺点和优点同样明显的作品,马路能打动人,就因为他给人一种穷途末路的感觉,他毫不隐瞒,用极端的方法表达个人的感受。如果正像方芳说的那样,总有一个地方会出问题,那这个问题既在戏里,也在戏外。
《像鸡毛一样飞》并不会带给人晦涩的感觉,一些小插曲颇为好玩。欧阳云飞晚上正在天桥上走,忽然有个声音让他四周看看,看有警察没有,然后问他要不要光盘。欧阳云飞抬头一看,一个鬼头鬼脑的人蹲在天桥顶棚的架子上,就是这个人卖给他一盘名为POET(诗)的光盘。有些具有更典型的孟京辉风格:电工给新娘朗诵诗歌时,周围排坐得跟《最后的晚餐》里基督的门徒一样的人没有什么反响,当他宣布所有的保险丝都换了新的后,欢声雷动。其实,电影里所有人物的经历都像个玩笑。
哥们儿,我还有30年可以折腾——专访导演孟京辉
问:你拍这部电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现在这部电影能达到你预期的目标?
答:是期望把技术和脑子结合得比较好的问题,这部电影达到了百分之六七十吧。
问:在话剧和电影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转换是不是有很大问题?
答:完全不存在。说我以前是搞话剧的,那第一次拍电影的人之前什么都没干过,他们都不需要转换,我凭什么要转换?
问:你不介意别人说你拍了一部话剧式的电影?
答:法斯宾德和伯格曼拍的电影都像话剧,怎么了?这是好事啊。那些说这部电影像话剧的人看过话剧电影吗?国外这样的多了,他们有这个视觉经验吗?
问:那么,电影拍出来像什么不像什么根本不在你的考虑之内?
答:一部电影该归结成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你没有办法。可能大家习惯用以往的观影经验来看这部电影,这有什么意义?各部电影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问:我记得在试映时你说观众不接受是件好事……
答:是好事。我已经想得够多了,现在进了电影院,既然要交流,就该他们去想想了。
问:在你的作品里似乎一直都关系“困境”这个问题。
答:可能现在的人生活得太好了,但中间和背后有什么问题,大家看不到、感受比较轻浅的东西,是我比较关注的。我把它们拿来重新强化、变形,这些是我比较爱玩的东西。中国现在处在安逸和艰苦之间的转换期,其间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可以被艺术家谈论。
问:你作品的女性都是纯洁的、敏感的,有时候以一种拯救的姿态出现,但最后很少有成功的。这样看起来你的作品都有很纯情的一面,她们是你的作品里很柔软的一个核,尽管你的话剧外表看起来冷嘲热讽。而且她们看起来都是细眉淡眼型的。
答:明明(《恋爱中的犀牛》)、企鹅姑娘(《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和方芳都有一种面目,就是牺牲精神,把自己的心绪寄托在别人身上。可能这种女性是我比较希望有的。
问:你把马雅可夫斯基的头像放在了片头……
答:我对他有特别的偏爱。他是一种艺术生活的写照,我们达不到,但激动也很羡慕。别人都激动完了,我还能寻找到激动的感觉,挺好的。
问:但有人说在《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看不到激动……你在意别人反对的意见吗?
答:我挺在乎别人反对的意见,但也无所谓。我都被反对10年了,也这么多年了。其实反对的也不多。
问:你这部片子有唯美主义倾向?
答:我觉得不是唯美,是唯形式感。一个人由于背景等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入手点不一样。有人从故事入手,有人一下从一个小情感进入,还有人对结构敏感。我是必须先找到一个大的形式感。每一种方法都可以进入,也都可以成型,但质感不同,我的这个质感比较强烈。形式也可以传达出情绪和意味。
问:廖一梅写的爱情故事都有一种绝望在里头,因为里面的两个人总也无法交流。
答:……到头来是绝望的。她是个悲观主义者,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里面的人看起来交流得再好,其实也是危机四伏。
问:你会不会有灵感枯竭的时候?在《臭虫》和《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后有这样的评论。
答:没有。哥们儿,我还有30年可以折腾,可以去颠覆。想想这个就让人高兴。

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