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娱自乐酷视流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王晓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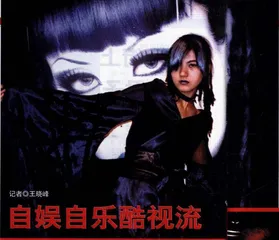
1993年,记者在采访中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个12岁的杭州女孩,独自坐飞机来到北京,就为能看到著名歌星刘德华一眼,并且把她刻的“刘德华”印张亲自交给她的偶像。当时她住在崇文门饭店,刘德华住在昆仑饭店。刘德华在首体彩排,这个女孩精确地算出了刘德华从首体回饭店的时间,刘德华回饭店时的路线和途中能遇到几个红灯,期间花多长时间,然后再精确算自己从饭店到刘德华下榻处行走的时间。经过反复测算后,她相信,当她走进昆仑饭店大堂时,正好能遇见刘德华。那时候北京还不太堵车,小女孩的“阴谋”得逞了。“当我走进大堂时,看见刘德华正往电梯口走去。”小女孩陶醉、自豪地向我讲述着这个不可思议的经历。
这是当时内地出现追星热中发生的众多大人们匪夷所思的事件中的一件,也就是从那时起,社会上出了一个“少数民族”——追星族。如今,追星族已见怪不怪,那个12岁的小女孩也已长大成人,人们也不再像多年前那样去关注、质疑这个族类,时间总是能让人们变得宽容。
2001年9月25日,有400余人聚集在杭州一家娱乐城里,他们衣着古怪、奇特,在舞台上,一群打扮得更夸张、妖艳的人在表演,局外人搞不明白他们在干什么?但台下每一个人都清楚,这是他们最喜欢的真人模仿秀(Cosplay),他们还给这个词起了一个更好听的中文名字:酷视流。
2002年4月3日,在上海师范大学礼堂,第一场真人模仿秀大赛让这个民间活动变得正式起来,一个新族类就这样浮出水面。
真人模仿秀很早就在欧美流行,比如曾有人搞过一次模仿卓别林的比赛,结果真正的卓别林只获得第三名。还有,在美英等国,每年都要举行模仿猫王或迈克尔·杰克逊的比赛。
酷视流实际上是另一种追星现象,早期追星族的特征是,疯狂追逐崇拜的明星,收集与明星相关的各种物品,但最多也不过是和明星合影、吃顿饭而已。而酷视流已不再是单纯、单向的追星,而是通过角色扮演,让自己“实现”做明星的梦想。
这种酷视流在日本比较发达,最早是一些喜欢动漫的同仁凑在一起,模仿动漫中的人物、形象,后来又有人模仿电子游戏中的形象。随着视觉系摇滚乐在日本兴起,人们又开始模仿视觉系乐队里的成员。所以,今天的酷视流,模仿对象基本上以象、电子游戏形象和视觉系摇滚为主。随着哈日族潮进入中国,酷视流也成了哈日族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约两年前,内地开始有酷视流,近一两年,酷视流在上海、广州、杭州和北京等大城市十分活跃。尤其是上海这个喜欢日本文化的城市,酷视流的团体多达几十个。
张磊是上海一家音乐杂志的编辑,一直喜欢欧美音乐,在年近不惑时,突然对酷视流发生兴趣,他成立了一家“星船文化”公司,搞起京沪两地的酷视流大奖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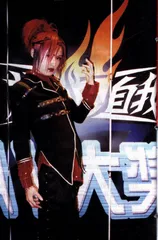
“我们公司以前在上海搞过北京一支视觉系乐队‘银色灰尘’的演出,发现喜欢的人很多。上海经常参加酷视流表演的有一千多人,后来我们把这些团体带到杭州,发现也很受欢迎。有一支日本视觉系乐队‘灰色银币’来上海演出,歌迷们提前两天就排队买票,由于不对号入座,所以又提前两天排队入场。门票300元一张,有些人看了两场,乐队从日本带来的纪念品非常贵,但在现场却卖得非常好,这在以前非常少见。”这是促使张磊搞正式酷视流大赛的基础。
这个酷视流怎么玩呢?其实就是模仿者把自己打扮成偶像那样,发型、服饰、动作、语言、神态、唱歌、弹奏乐器等都要模仿得惟妙惟肖。模仿得越像,观众的印象分就越高,自己的满足程度也越高。另外,对动漫模仿要比对视觉系的模仿更难一些,因为自己要写剧本、表演,不过这些都难不倒他们,北京的一支酷视流团体竟一口气写了4集剧本。为了达到崇拜目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出来。
为此,记者又采访了北京两个专门从事酷视流表演的成员。
皇雪姬,女孩,22岁,在某公司做市场营销,1997年开始喜欢日本音乐,从去年开始从事酷视流表演,并成立了“璀璨”社团。“我们模仿,是对他们有很深刻的感情,很多人做Cosplay,从开始不能接受到最后为之疯狂,也是一种满足。我们做的时候很投入,这是一种美学贯彻,思想表达,是模仿给我们带来的快乐。”皇雪姬虽然“出道”时间不长,但她先后模仿过三位日本视觉系乐队的形象:Malice Mizer乐队的Mana、“灰色银币”乐队贝司手Toshiya,还有Due~Le~Quartz乐队的Miyabi。
还有一位男孩郭子,目前在上大学。从事酷视流表演的人大都是女孩,男女比例基本上在一比五左右,很少有男孩从事这种表演。不仅在国内,日本也是这样。郭子说:“男生喜欢日本流行音乐的比较多,喜欢视觉系的人少,另外还和目前中国的现实有关。人们都很保守,你这样做会有人说你变态,所以很多男生不好意思表演。不过我的同学可能会说些不好听的话,但是我不在乎。”
与一般的追星不同,酷视流在追星的同时,自己也能成为明星。比如上海有个模仿者,每次主持人报出她的名字时,台下边欢声雷动。这一点,是那些普通追星族望尘莫及的。酷视流与一般追星现象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可以二次创造视觉效果,观众可以通过真人与模仿者之间的异同比较,达到愉悦目的。它丰富了追星内容,甚至是追星者的生活方式。皇雪姬说:“追星与Cosplay在心态上差不多,但不一样的是,做Cosplay的v人,生活中也会带有一种感觉,思维与视觉系里的人思想上已经融为一体了。在生活中往往能体现出来。”这就是酷视流给“8字头”年纪的人带来的快乐。郭子说:“去年圣诞节,我第一次参加Cosplay,化完妆之后像变了一个人,感觉特别好。”
而视觉的再创造又可以带动时尚潮流,虽然那些夸张、妖艳的服饰和化妆不能让他们直接从舞台走到街头,但经过改装、精简的服饰和发型早已遍布城市街头。
在采访中,记者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个性”。张磊说:“这些歌迷都很偏激、有个性,喜欢酷视流的人都喜欢玛丽莲·曼森,并且都讨厌韩流。”皇雪姬说:“毕竟视觉系的人离我们很远,而他们的个性都是我们自己揣摩出来的,每个人对他们的理解都不同,都会融入到自己的个性中去。”郭子说:“我们不单单是模仿,还有自创性,这就是展示自我的方式,有些自创的内容比Cosplay还要好。”在模仿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个性,这话听起来有点别扭,但却是“8字头”们面临的事实。既然已经有“7字头”的人靠模仿专家、学者成名,晚辈们靠酷视流模仿出自己的个性又有何妨?毕竟,这只是他们生活中经历的一个特殊阶段而已,就像郭子说的这样:“我没有太往深里去想,可能就是追星吧,艺人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将来肯定不会去做这个。”
酷视流是一件投入很多的活动,如果要模仿得逼真,就得在服饰、发型上考究一些。很多视觉系的艺人着装、发型非常有个性。为了能达到模仿效果,很多模仿者只能到戏服厂或香港订购,或者自己动手来缝制,所以,投入几千元是常见的事。皇雪姬为了模仿Mana,专门做了一件欧洲中世纪宫廷大礼服,为此,她在这方面先后投入了3000元左右。但毕竟她已经工作,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大多数学生的这笔开支只能由父母承担。酷视流一族是各类追星族中的“高消费群体”。
那么作为父母对子女的这种高消费追星是否支持呢?张磊告诉记者,大部分父母反对孩子玩酷视流,担心他们影响学业。但是也有一些父母很支持自己的孩子,甚至陪同孩子前来报名参加比赛。皇雪姬和郭子的父母都很支持他们,“他们认为这是我的兴趣和爱好,所以从不干涉”,皇雪姬说。
但所有这些人都不希望自己的兴趣让单位知道,张磊介绍说:“我们搞比赛的时候,日本读卖电视台来采访,并且到一些表演者家中去采访。但当电视台提出去单位采访时,都被拒绝。”皇雪姬也告诉记者,她在从事此活动时,一直没有让单位知道。这些人的顾虑是显而易见的,毕竟社会上更多人对酷视流还不理解。这次在北京举行的“极炫自我Cosplay大奖赛”上,主持人曾经问一个观众,你怎么看待他们?这位观众说:“很受不了。”他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人。
在采访中,当谈到为什么对日本文化这么感兴趣时?皇雪姬和郭子的观点完全一样:日本文化新奇,所以让他们感兴趣。皇雪姬说:“这个民族的发展让我很感兴趣,日本文化是从中国文化引申出来的,又融合了西方文化,形成了自己的东西。这个民族对外来文化有选择性的包容,他们的民族情结和民族魂让我感兴趣,目前的中国文化就缺少这个,没有信仰。另外,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停留的时候多,前进的时候少。”
“酷视流其实就是自娱自乐的活动。”张磊说。当这种自娱自乐以一种社团方式出现时,实际上就已经变成了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