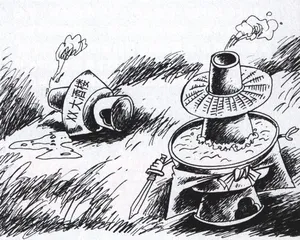生活圆桌(191)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喜之郎 Harold 杨不过 无忌)
儿子
喜之郎 图 谢峰
星期六上午我在超市闲逛,旁边有一汉子,推着购物车,车上坐着一胖小子,穿着开裆裤露着小鸡鸡盯着货架上的各种食品。那汉子的电话突然响了,他接电话声音洪亮:“我呀,我正带儿子买吃的呢。”
我在旁边立刻羡慕得要死,听听人家的口气,多么豪迈。
每个星期六我都幻想能有个儿子抱着出去溜溜,可到星期天晚上,这幻想就因又一轮工作的来临而停止。这么说有点儿重男轻女的意思,有个闺女也行。
我知道一汉子长得又黑又壮,生了个闺女也特别结实,而且跟他爹一样酷爱吃肉。有一次他爹带她去吃朝鲜烧烤,当爹的自己要了盘狗肉吃。他家里养了条狗叫“小小”,那闺女和“小小”感情浓厚。谁料想那闺女非要尝尝,尝过之后说太好吃了。回家的路上还不停地问:“爸爸,咱们什么时候再去吃狗肉呀。”爸爸说:“吃吃,咱回家把小小杀了吃一锅。”闺女说:“真的吗?那太好了。”
我知道个儿子,她妈教他说话采用的是双语,英语汉语一齐上,所以这1岁半的儿子不太爱说话,估计是脑子里面正转悠着是用英语还是用汉语说呢。他妈可以一边开车一边哄副驾驶座上的孩子,有一天路过中央美院,他妈说:“你要想学画画咱们以后就上美院好不好?”儿子对艺术好像没兴趣,不说话,他妈就说:“你不喜欢画画呀?好多男的不喜欢画画可喜欢找个画画的女朋友,那以后给你找个搞艺术的女朋友好不好?她们虽然穿得破点儿可长得还行……”那儿子不胜其烦,说道:“好好。”
我喜欢沉默的儿子,也见到许多父母在儿子面前变成话痨。他们似乎执意要把儿子训练得特懂礼貌,逮着谁就让儿子叫叔叔阿姨,儿子如果不叫,父母还做出一副生气的样子。其实,当爹的遇到他讨厌的同事或邻居,应该对抱在怀中的儿子说:“儿子,看看,这是一个大傻逼,以后长大了你会发现天下有许多傻逼,叫他,傻逼。”
可惜,如果我抱上了儿子不敢这样教他,但我至少可以教他沉默和矜持,对这个荒唐的世界视若无睹一言不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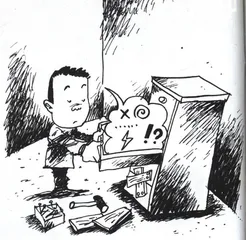
缅怀冷兵器时代
Harold
电影《霸王别姬》里段小楼看见那把宝剑,得意地对陈蝶衣说要是当年霸王有这么一把锋利的宝剑一定能先把刘邦杀了。项羽的悲剧当然不能改变,即使改变了也会以刘蝉那样的喜剧形式出现,可是喜形于色的段小楼表达出来的那种男性对冷兵器的热爱几千年都没有变。
我喜欢那些描写古代欧洲战争的电影,比如早一点的《勇敢的心》、《圣女贞德》,近期的《角斗士》、《战神传》,说白一点是喜欢其中的战争场面。两军对垒,双方一字排开,先命令弓箭手放箭,一时就箭矢如雨,中者立毙;然后吹号角,双方马队在平原上面对面地冲锋。步兵嗷嗷呼啸着跟上去绞杀,刀和刀叮当碰在一起,肉和肉砰砰撞在一块,兵刃、鲜血和残肢断臂在眼前乱飞,生死寄于一线之间。每次看到这些导演精心设计的宏伟场景,我都大呼过瘾,仿佛能透过战争窥视到支撑士兵们战斗的不同意志和信念之间的搏斗。
除了痴迷于这些电影,我还曾经迷恋刘兰芳说的《岳飞传》和单田芳讲的《三侠五义》。评书对于战争和比武的描述没有电影那种直接的视觉刺激,但是留下了想象空间。我老也忘不了《岳飞传》里面“岳云锤震金蝉子”一节,岳云本来实力不如金蝉子却凭借智慧战而胜之,难得刘兰芳把岳云的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简直可以同“田忌赛马”一起成为运筹学的范本。
同样有趣的是冷兵器时代战场上的贵族精神。最有名的是至今仍然被当作笑柄的宋襄公,他放弃在敌人渡河时一击而溃的机会,结果被楚人打得落花流水,雄霸天下的梦想也就此告终。即使在两军对阵以后,将领也还可以选择“武斗”还是“文斗”,武斗是不讲人数多寡,不择手段乱战一气,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文斗要比勇气、赛智慧,总之是拼综合实力。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侠客们出于对对手的尊重和对自己的自信,从来不会拒绝处于劣势的一方提出来的“文斗”要求。我想这里贯穿了太多的人文理想,后来不管是国产还是港产动作片总是以正邪双方抛掉武器的肉搏结尾,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目的。这样的结束能使读者畅快淋漓、解气解恨,但真实的历史却往往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没有那么多戏剧化的矫揉造作。
冷兵器时代,战争的胜负对于武器的依赖不像现在那么严重,但我中唯武器论的毒太深,执著相信兵刃好坏即使在冷兵器时代也能够决定输赢。比如我认为玉娇龙要是没有那口宝剑就未必能在武林群豪面前占多少便宜。对于冷兵器好坏,我也有自己的信仰。开始我有点盲目崇拜那些使锤的将领,那种兵器是权力的象征。上中学读李白的《侠客行》,才念到“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我就已经佩服得不可收拾了。后来历史老师讲喜峰口战役,荷枪实弹的鬼子居然败给操着传统大砍刀的中国士兵,长了中国人志气灭了东洋人威风,我就改弦更张相信刀才是兵刃之神、男人最爱。
为了挽留残存的男性精神,我现在每天身上不忘带着兵刃——那把挂在钥匙链上用来削水果和开啤酒瓶的冒牌瑞士军刀。
婚礼
杨不过
我是个早早下定决心要晚婚的人,每当逛街时看到那种耀眼夸张得平时穿不出去的衣服,总要喜滋滋地想:等有朋友结婚了,我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参加婚礼。
这种对婚礼的奢华印象多半来自于外国电影,那里面的婚礼总是大片的草坪、整车的鲜花、美酒、乐队、露天舞会,不但新娘子仪态万千,连客人也个个光彩照人。当然不仅仅胶片里才会出现,大帅哥布拉德皮特结婚时租下的那个小岛,同样也叫天底下一多半女人咬牙切齿,不过看在女方在《老友记》中还算可爱,我暂且放下了这份遗恨。
对我这样的女光棍来说,婚礼的诱人之处还在于,说不定能遇到个把帅哥开始一段艳遇。大学毕业两年后,终于有个同学要结婚了,老同学们合计了一番,还是决定非常庸俗地凑钱买个屏幕超大的电视机作为新婚礼物。这时候我已经觉得不对劲了,在电影里,礼物都是鲜花巧克力红酒啊。
她结一次婚,却办了两次婚礼。先是回乡下老家,穿一身红袄红裤,假模假式地扮了一次小媳妇,程序为抢亲、拜堂、摆酒席、见七大姑八大姨等等。回来之后,作为单位里的适龄青年,又被迫参加了一次集体婚礼,和几十对新娘新郎冷呵呵在风里站了大半天,等待着领导热情洋溢并且故作幽默的冗长发言赶紧结束。最好笑的情节是,婚礼前男方单位给女方单位写了一封“求婚信”:兹有我单位××与你单位××恋爱关系成立……
这两次婚礼我都没参加成。几个星期后两口子设宴款待我们,我从单位赶到时大家已经酒过三巡。我穿着灰不拉唧的T恤仔裤,满头大汗,灰头土脸,席上一张张暧昧的笑脸均已相识超过五年。酒足饭饱之后,我感慨道:这真是长久以来最丰盛的一个大饭局,而压箱底的那件漂亮的露背装是没机会穿了。
一直到读过美国著名的老垮掉派诗人格雷格利·柯索的长诗《结婚》,我才对她的婚礼彻底释怀:
“我该结婚吗?我该好好做人吗?/等到她要把我引见给她的父母/背要挺直,头发再梳一次,往死里勒紧领带/我能双膝并拢坐在她家的三层沙发上/而且一直不问洗手间在哪里吗?/哦上帝,哦婚礼!她的一大帮亲戚一大帮朋友/和我的那几个可怜兮兮破破烂烂胡子邋遢/就只知道等着去喝酒去吃东西朋友—/还有一个牧师!他正打量着我好像我正在手淫/他问我你愿意娶这位女士做你的合法妻子吗?/我吻新娘那一大堆野汉子把我掴到后边/她是你们大家的,伙计们!哈哈一哈哈!/而在他们眼里你会看到一个淫荡的蜜月在等着呢……”
菜在江湖
无忌 图 谢峰
在重庆吃来吃去,最喜欢的,还是江湖菜。我说的江湖菜,是那些还真正留在江湖的菜,而不是搬进大酒楼,由一级厨师做出来,装在考究的盘子里,再由漂亮的穿着道具一样中式对襟衫的小姐端上桌。比如来凤镇的红烧鱼、白市驿的田螺,特别是渝北区到长寿的必经之路上,一家夫妻店做的水煮鱼,那真是一绝。多少年前的事情了,我们走进那家小店,点了鱼,老板麻利地洗、剖、切片,然后对里屋喊一声:“还是你来下锅吧。”老板娘正在奶孩子,听了这话,把孩子交到老板手里,就站到了灶台边。没多大功夫,一脸盆鱼上了桌,一位淑女说:这个怎么吃啊?没人理会她,大家吃得一句话都不说,很快,我看见那位淑女的脸也埋进盆子里去了。味道说不上特别,不过是麻辣鲜香嫩,但是,大家都像给施了魔法,筷子停不下来,吃在嘴里,看着脸盆,你争我抢,都忘了大家是朋友了。风卷残云之后,一个电影发烧友说:“这个老板娘一定看过《红高粱》,姜文酿酒撒了尿,她烧鱼挤了喂孩子的奶。要不然,鲤鱼不可能这么好吃!”
现在多是在一些宣称自己宏扬饮食文化的大酒楼里吃饭。这些地方都刻意地给人造成一种你身在大自然的假象,比如原木的楼梯、桌旁翠竹的掩映,看上去“小芳”一样质朴的服务员,还有低回的民乐。菜谱上的那些名字引人遐想,但是,不知为什么,那些菜一律让我吃了上顿不想吃下顿。菜还是江湖菜,但一进酒楼,就有了股匠气,少了还在江湖时那股自由自在的鲜活劲儿,如同和唱片公司签约后的摇滚歌手。
同样道理,吃火锅我也只喜欢一些路边店,三拖一那类的。不是说大酒楼的火锅不好吃,恰恰相反,大酒楼的火锅好吃得简直没有悬念,各种调料就像用天平配出来的,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但是,对等的,也不会有惊喜。而路边店就不一样,每一位来吃饭的人不是被老板当作上帝,而是爷爷。味道也不是每次完全一样,遇上哪一次发挥得特别好,你表扬他一下,他顺着那根看不见的竹竿往上爬的样子精彩得很。而“爷爷”哪次吃得不满意,把老板叫过来,他那痛心疾首的样子,就差给你写份检查了,走的时候又是发烟又是打折,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海涵,一定要再来。
每一次去熟识的小店吃火锅,心情都很特别。像是赴一场冒险,像是奔一个赌局,一如被浓缩了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