熵增时代的自由分子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三联生活周刊)
以晚上7点为基准,前后振幅半个小时内,连岳只要在家里坐着,就能打个盹。他精准地形容:“打盹是困意的突然来袭,因此它有睡眠没有的快意,一秒、半秒,或者更短的时间单位之前,清醒还站在自己身上。忽然就有一把阴险准确的枪击中了它,人瞬间只能以全无防备的姿态放弃与意识的对抗。”
在工作了10年之后,连岳选择了彻底离开,他厌倦了自己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当一个人有太多的奢望,对权力有过分的执著之时,他就慢慢平庸了,失去所有的灵气和光芒。“你控制不了环境,但你可以控制你自己。”与王小波辞职在家里写作的时候相比,现在的谋生方式容易得多。连岳继续写他的专栏,他对生活并没有更多的物质要求,他已经有了基本的东西,也不打算追求更大的房子和诸如此类。他喜欢和生活没有任何逻辑联系的东西,非常遥远的,比如听佛——每天连岳都会看一个小时的佛教电视台,系统地看自己计划的书,泡功夫茶,和朋友聊天喝咖啡。连岳用“清凉”形容自己目前的生活。年轻时的连岳常常驾驶一辆挎斗摩托车狂奔在厦门街道,热爱喝酒、打架,情绪很容易被撩拨起来,“我甚至喜欢过《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1997年王小波的死对我是个非常大的打击,在两个月内,我读完了几乎所有他的作品。之后觉得旧有的世界多少被颠覆掉了。”连岳说,“我觉得,我们是在传统教育体制下智力方面非常有缺陷的一代人。实际上王小波说的不过是一些常识,这些常识本应早已普及了——比如说判断一个东西的好坏最重要的就是经验。那一年,我已经27岁了。”
看王小波的时候,连岳觉得自己笨,“还不如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和其他聪明人一样,连岳靠的是虚荣心生活,一觉得自己笨,就像被点了死穴,“我只好把王小波推崇的人一一找出,先是杜拉斯,再是奥威尔,最后到了罗素。”罗素15岁开始思考哲学,在日记里理性地否认了宗教教条,连岳30岁的时候还没思考过哲学,而立之年的罗素已经在写《数学原理》了,罗素活到了96岁——按照这样的推算,连岳说自己得活196岁才能心理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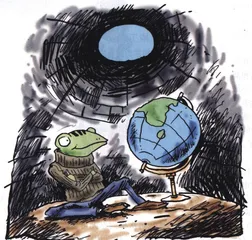
连岳极喜欢自己目前的状态,他几乎感觉是自由的:“所谓的自由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要挟你了。这是我认为的自由。物质,荣誉,工作,理念,我不为任何东西所要挟。人和人的自由状态不同,但是对于我来说,自由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要求你、要挟你。”
连岳酷爱打盹,目前的状态对于他来说是休息数年,或者长达20年的打个盹。连岳清楚,打盹也是“一种对状态的自我满足,一种与环境的妥协和同谋”。
对有命名癖的人来说,读王小波的人包含了许多的“一代”:红旗下的蛋/碎片中的天才一代/志大才疏的一代/游走的一代。李皖在《这么早就回忆了》中描述了一些似乎更深刻的特征:幻想甚至梦游的气质,天生的距离感,极度矛盾,表达不清,边缘的,观望的,生在城乡结合部,天然的感伤;距离是这代人最核心的东西,朦胧是他们面对世界的一种方式,对已逝的含情脉脉,对现实的保持距离,对自我倾情,对未来忧心等等。
一个已经不年轻的60年代朋友说:“不是只有年轻人才忧伤的。很多人都很忧伤,比如我的父母。”比上述60年代更年轻的则是一些患有“牛B在路上”的70年代焦虑症患者,一个70年代的年轻朋友陈毅聪理直气壮地说:“我之所以无法变得超脱、浪漫,无法诗意地栖居在《我的阴阳两界》里面的阴的世界,是因为我已经可以自由地选择平坦的市俗之路,我没有必要以矫情的姿态寻求安慰,标榜叛逆。现在不是中世纪,骑士时代结束了,我们有必要与风车大战五百回合么?”
4月1日罗大佑来北京,准备在北京建设他的音乐工厂。这让人回忆起两年前的罗大佑演唱会,从北京发出的专列,北京飞往上海的航班上拥挤的人群,盛况空前的演唱会,你看到那些25岁到35岁的年轻人,他们和罗大佑一起制造了一个具有文化狂欢又具有怀旧仪式感的空间,如今同样的这群人准备着出发去韩国看世界杯。他们打定主意,遵循日常生活简单化、追寻快乐的原则。有些时候人们表现得很随便,因为他不匮乏了。当人们的匮乏感消失之后开始表现出一种自由精神。然而这种不匮乏感背后的自由和王小波所写的时代是多么不同。熟悉王小波的艾晓明说:“小波写了真正美好的爱情和性,写了他的人物如何地想要生活在一个可以创造发明,可以爱,可以探讨人的一切自由的可能性的时代,而这个时代永不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