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里的村庄
作者:钟和晏(文 / 钟和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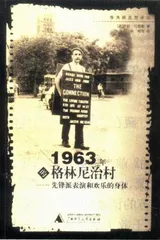
《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
萨利·贝恩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11月第1版

《纽约琐记》陈丹青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1年8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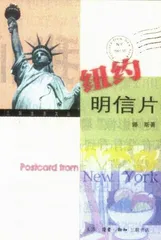
《纽约明信片》娜斯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10月第1版
对叛逆放纵、坦率自信的60年代心存迷恋的人,仅仅看到《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这个书名就足以打动他们。暗黄色的封面照片上,一个工人模样、身背广告牌的人正用近40年前的陈旧目光茫然地注视着你,而这本书似乎更具诱惑力的副标题是“先锋派表演和欢乐的身体”。
选择格林尼治村来探讨美国60年代的文化主题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是因为在作者萨利·贝恩斯看来,这个当时各种门类的年轻先锋艺术家聚居之地是福柯术语中“异托邦”的最好代名词,一个既反映社会又对抗社会的真实空间。而1963年则代表了50年代与60年代过渡阶段艺术最多产的一年。那一年,将现代艺术带到美国的1913年军械展览会再次开办;安迪·沃霍尔买了他的第一部电影摄影机并在他那间著名的“工厂”里和同伴们用画画、拍电影、做爱和吸毒消磨时间;作为同性恋地下活动中心的西诺咖啡馆和非裔美国人艾伦·斯图亚特的妈妈咖啡馆不仅为实验戏剧提供表演场所,同时也担负起滋养艺术家身体的责任;而在未来20年里支配着后现代舞蹈发展的贾德森舞蹈剧团还刚刚诞生。
萨利·贝恩斯是威斯康星州大学的戏剧和舞蹈教授,她显然无意在这本充满概念、引文和大量人名的学术著作中将已然是神话的“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再次神话化。在略显繁复乏味的阅读过程中,与忙碌的先锋艺术家们沿着杜尚早在1917年用一个小便器所指明的道路,尝试各种生产自由和平等的反艺术活动相比,一些让我印象更深的事实是1963年美国国家对艺术的资助问题成为政治关注的中心点,福特基金会曾启动了一个高达800万美元的使芭蕾美国化的项目。“即使在古巴危机最紧要的关头,赫鲁晓夫还在歌剧院中度过了4个小时”使美国人深感不安,所以当时的纽约市参议员贾维茨在国会的发言异常直露:“在共产主义集团和自由世界之间的竞争中,艺术已经成为决定国家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中国画家陈丹青在80年代初带着几十美元和“去美术馆看原作”的惟一热望到达纽约时,那个“都市里的村庄”早已成就了无可辩驳的“国际艺术中心”地位,安迪·沃霍尔已是亿万富翁,无所不在的后现代文化变成了日常的生活方式和景观。
当陈丹青十几年后回国授课讲座时,常常包围着他的是关于“如何打入美国的主流文化”、“中国艺术家的整体素质以及在世界形象上的优劣”之类的问题。而陈丹青千篇一律的答案总是反问道:“你见过哪位西方人发誓一定要打入中国主流文化?”或者“欧美艺术家会在乎他们的整体素质及在世界形象上的优劣吗?”关于西方、当代和艺术,未曾迈出国门的人有太多的求知欲。所以有一天陈丹青边看国内电视剧边想起一篇要完成的访谈稿子时,他在《纽约琐记》中写道:“那访谈的话题是‘中国油画在世界’,我出了国,大概就算在世界吧?哪里晓得我在纽约某座公寓的灯光下瞧着东北连长献身救姑娘。”
波希米亚天堂Greenwich在今天又是怎样的景观呢?《走过格林威治村》的娜斯感叹说:“今日的西村与昨日相比,大有迪斯尼化了的味道,到处是对另类生活无力尝试又充满好奇的中产阶级游客。”
事实上迪斯尼这三个字也几次出现在《纽约琐记》中。当1994年纽约政府在迪斯尼集团的资助下整建时代广场时,陈丹青和他的国际同行们被迫迁出租金低廉的画室大楼时他说:“我窗户对街的大墙上画了迪斯尼卡通广告,那只大白兔造型日后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超级势力,轻易打败了楼内全体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
而被问起最喜欢美国的哪一位艺术家时,安迪·沃霍尔总会说是沃特·迪斯尼。 艺术陈丹青纽约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