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的资源世界
作者:陈晓(文 / 陈晓)
 ( 在南海上捕鱼作业的马来西亚渔民 )
( 在南海上捕鱼作业的马来西亚渔民 )
造锅运动
几乎所有地质学家提到南海时,都会把它作为一个海洋家族中的年轻人。相比离它最近的大洋——具有上亿年历史的太平洋,南海正式成型才6000多万年。可是对渺小的人类来说,要叙述南海的故事,还是不得不这样恭敬地开始: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被地质学家称为“中生代早期”的年代,今日南海的所在位置还被古太平洋一统天下。印度和澳大利亚还同属一支,被共称为印—澳板块。它们孤独地漂浮在古太平洋浩渺的海水中,但不甘寂寞地向华南地块所在的大块陆地的位置前进。其中印度所在的印支地块走的速度比较快,因此在亿万年前的某一天,它脱离了印—澳板块,率先完成了与华南地块的缝合。这是南海的“前传”。从遥远大洋上异军突起的印支板块,封闭了这片海域的西部和北部边缘,使古南海呈现出一个海湾的雏形,东部与古太平洋相接。接下来,随着地壳运动,同时向华南地块俯冲的还有在东南一线的台湾浅滩、东沙群岛、中沙群岛等等,对古南海海湾逐渐形成围堵之势。
这波缝合的地壳运动之后,这一片海域又出现了一次拉张运动——这是南海形成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一次地壳运动。在华南地块的边缘,一大片陆地沿北东向拉裂,滚入浩瀚的海水中。脱离华南地块的陆地,向南漂移,形成了今天的南沙群岛。它和华南陆地之间的海域,便是今日的南海海盆。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边缘海地质研究室的研究员阎贫告诉我们,海域内油气资源的生成条件是:有锅——凹陷的地形,有火——形成油气的挤压和热量,以及有防止油气逃逸的锅盖。而南海这次拉张性盆地的形成就像是一次“造锅运动”。
这是一口底部深但外延区域绵长的“锅”。如果不考虑边界偏菱形的形状差异,南海的构造有点像一顶不规则的草帽:帽檐是缓坡型的绵长大陆架,然后是陡峭但深邃的大陆坡,中间是深陷的海盆和洋壳。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前总工程师姚伯初墙上的一幅彩色南海卫星地图,能更形象地表现南海特殊的地质结构:最宽阔的部分为白色的大陆架,尤其拉裂的创口处——西北和东南边缘,前者的大陆架宽度为200~300公里,后者的宽度更在300公里以上。由于大陆架是陆地上的沉积物堆积而成,而华南地区多矿的原始地貌决定了拥有世界上最广阔大陆架的南海海域是含有机物最丰富的海域。而有机物是油气、矿产、海洋生物、鱼类等所有资源生成的基础,在这一点上,南海有着最优厚的先天条件:有丰富的有机物来源,还有最广阔的沉积空间。
白色大陆架之后,是黄色的大陆坡。这是从陆地入海的一段距离。虽然在卫星地图上,黄色区域的宽度相比大陆架大为逊色,但它的厚度却达到4000米以上。作为油气的另一个产区,陆坡与陆架有相同的油气形成条件:从陆地沉积而来的丰富有机质,广阔的生成和存储空间。而且陆坡与陆架大约以1100米水深为界。在这个高度的水深以下,低温与高压还可以促成另一种重要资源“天然气水合物”的生成。
 ( 马来西亚汀娜湾的渔民 )
( 马来西亚汀娜湾的渔民 )
4000米以下就是大洋盆,这是其他边缘海不具备的深度条件。南海的广阔面积以及水深,使它同时拥有陆壳和洋壳,因此具备两类海域的资源种类。“大洋底比较瘦,没那么多有机物。它的物质一般是靠地底的地质变化,比如海底火山的喷发,形成地球内部的物质。洋峭里的物质变化是化学沉积。这是一种非常慢的沉积,每100万年才3.5毫米,但会形成大陆架和大陆坡等地带无法形成的资源铁锰结核。”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赵焕庭对本刊记者说。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前副总工程师姚伯初告诉我们,自华南陆地的大拉张后,南海海域的地质构造基本停止,“大锅”初具雏形。但东边频繁活动的板块,还在塑造着这个大洋盆的海底结构。“拉张型海盆形成后,东边的地块也并没有停止。它们对南海海域形成挤压,结果是东边的地形和南北部非常不同。在临近南海东南端的苏禄群岛附近,可以看到标示海水深度变化的线条非常密集,说明由于地块的挤压,这边的海水由浅变深的距离非常近,只有几十公里。”阎贫对本刊记者说,“直到今天,东部边界的板块对南海海域的挤压都没有停止。台湾的大地震、菲律宾的火山,还有印尼最近的火山喷发,都是挤压作用正在发生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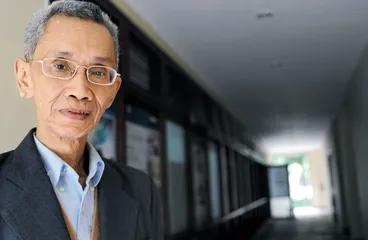 ( 陈铮 )
( 陈铮 )
这些地质活跃分子对南海不间断骚扰,一方面塑造着海底沟壑纵横,隆起与凹陷相间的复杂地形,一方面也对南海海水中丰富的有机质形成挤压作用。“这是油气生成的必要条件之一。”阎贫告诉本刊记者,“而且油气在挤压和热量的作用下形成后,还需要储存空间和盖子。东边板块的活动也达到了这一目的:一挤,平的地层就会鼓起来,地裂的缝隙就被封住了,就像一个碗扣过来,盖住了油气。”
中国的“波斯湾”
 ( 姚伯初 )
( 姚伯初 )
姚伯初告诉本刊记者,他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对这片海域的认识。那时候,对南海的地底构造还并没有认识清楚。只知道这是一个大海盆,因此具备油气生成的条件,但具体沉积盆地的位置,资源量多少,并不清楚,要进行精准的探测又捉襟见肘。“海洋探测是非常费钱的。”研究南海珊瑚礁的赵焕庭对本刊记者说,“20年前出海,我们就比喻,出海考察的费用相当于船一离开港口,就有一个人站在船头撒10块一张的钞票。”
因此,南海的第一个油气勘探点是根据地质规律类推的。“按照当时地质规律的推断,从大庆到北部湾,应该同属于北东向沉积带。”姚伯初对本刊记者回忆,“最初的油气勘探就从北部湾开始,这是南海海域西北角最接近陆地的一片海域。”
 ( 赵焕庭 )
( 赵焕庭 )
但在北部湾最初的探索并不成功。“由于处在欧亚、澳大利亚、太平洋板块的交汇地带,南海海底的断裂很多。”赵焕庭对本刊记者说。这本来是生成油气的有利条件。“很多断裂随着地质运动,断裂处出现下沉,在大的海盆内,又形成小的盆地结构,并随着地壳的运动,封闭起来,形成储油层。”姚伯初告诉本刊记者。但这种地质结构的另一面是,让油气的集结位置相对分散,找到确切的出油点并不容易。由此,位于北部陆坡,后来第一个出油的珠江口盆地一开始反而被忽略了,“因为珠江口盆地距离北部湾距离很近,按照隆起和断陷规律出现的规律,北部湾是盆地,珠江口盆地所在的位置就应该是隆起”。
但事实证明,南海复杂的海底结构,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地质规律。1976年,珠江口盆地打了5口井,采出了石油。阎贫他们的地球物理探测工作还发现,在这个约5万平方公里,最接近华南陆地的沉积盆地内,“还存在至少4个次级盆地,以及无数三级盆地”。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珠江口盆地已经贡献出了20多个油气田,且石油年产量保持在千万立方米以上。
 ( 南海海底美丽的珊瑚礁 )
( 南海海底美丽的珊瑚礁 )
但北部陆坡还不是南海油气资源最丰富的海域。姚伯初说他最青睐的是万安盆地,这是位于南海一系列盆地中最靠近西南方向的盆地,除了共有的满足油气储存结构的地理条件外,这里另一个有利条件是“水很浅,只有100多米”。姚伯初对本刊记者说,但由于边界问题,万安盆地最终只成为科研工作者的一个梦想。姚伯初给本刊记者出示了一幅地图,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井字形线路,代表着科研考察所到的区域。他说:“用地球物理的方法,已经对所有海域进行过调查了。”阎贫是边缘海地质研究室的研究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用地球物理的方式对海域进行探测:“以50米乘以50米的距离定点,进行海洋地震探测,确定海底资源的可能性。因为河流冲击是持续的,所以泥沙的堆积是有节奏的。我们用海底气枪,放出巨大的声响,响声在水面下传导,根据返回信号的强弱,确定是否有油气层的存在。如果不含油气的地质,密度大,比较硬,声波的传播速度就快。如果含油层就比较黏乎,传播速度就会降下去。”
这是一个在原理上简单但操作非常枯燥而且耗费时间成本的探测。从70年代开始,科考船就携带着海底气枪,船尾拖着长约2000米的接纳信号的电缆,日复一日在广阔的洋面上进行巡航探测。虽然每天的工作内容相同,但考察员也没有松懈的时候。“气枪的增加气压为130个大气压,因此需要人一直看着它,以免出现安全事故。给气枪加压的空压机用一段时间要休息,还有记录海底传回信号的外置磁带机,记满一个带子大约半小时,因此需要人定期去更换磁带。船后拖着的电缆也是一个障碍物。做地球物理探测的船,因为所需要信号比较粗略,电缆长度只有2000米。如果是工程探测,则需要6000米的电缆。为了避免对别的船只的航行安全造成隐患,也需要安排船员盯着。”阎贫对本刊记者说。
在这些方格式的密集扫描航行中,阎贫和同事们收获了很多海洋的信号。比如南海陆架总面积180万平方公里,其中已知的含油盆地就占到了85万多平方公里。尤其南沙的曾母、礼乐滩及安渡滩至永署礁之间,盆地不仅多,而且大,面积动辄几千平方公里,还有几个都是上万平方公里,预示着南沙地区还是前景不可限量的富矿区。根据这些从海里传回的抽象信号,南海石油的地质储量被估算为230×108~300×108吨之间,甚至被一些乐观的地质学者称为第二个波斯湾。
“但在探测过程中,也收到一些难以解读的信号。”阎贫对本刊记者说。印象最深刻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南沙做海底地震波探测时,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波段。“它和海底的波段相似并平行,但却可以穿过沉积物的波段。按照常理,一般不可能出现跟另一个固体物体打交叉的波段,除非这里存在一种不同的固体物质。”
这个让研究人员困惑的地震波,直到1992年,姚伯初去美国访问以后,才解开谜底。
可燃冰的秘密
姚伯初的电脑里存着他1992年访问美国地质调查局时的资料图片,其中有一张是一大段黑色的海泥,黝黑的泥体上,透着密密麻麻的白点。这是姚伯初第一次看见“天然气水合物”的实物。
天然气水合物是甲烷等天然气在高压,低温条件下形成冰状固体物质,后来被媒体形象地命名为“可燃冰”。它是浓缩性的甲烷,在标准温差下,1立方米甲烷水合物可以释放163立方米甲烷。放眼全球,天然气水合物可产生的能量相当于地球上石油、煤和其他生物中碳的总和的两倍。姚伯初告诉本刊记者,天然气水合物的生存条件是高压低温,温度不能高于25摄氏度。体现在海域中的位置就不能高于水下300米,但也不能深入大洋底部。因为太深的地方是一个氧化环境,也无法形成天然气水合物所需要的基本物质甲烷。综合这几个条件,充满丰富有机物的海洋大陆坡是一个适宜的环境。
美国获得这块“天然气水合物”的地点就是东海岸的布莱克海台。但对姚伯初来说,比实物更有价值的是美国人获得这块海泥的信号——布莱克海台上的地震剖面:一种与海底平行,但穿过沉积物的地震波。这和阎贫他们在南海发现的无法解读的地震波完全一致,姚伯初把它命名为“似海底地震波”(BSR),这是天然气水合物存在的典型信号。
当时美国政府也并没有意识到它的能源价值,而是把它作为一系列海底事故的罪魁祸首。“由于海平面的高度并不是稳定的,如果出现大面积的海平面下降,有的位于浅水区的天然气水合物,因为不够300米深度而会融解。固体物质融解为气体后,造成陆坡的坍塌,拉断了一系列海底电缆。美国人在检查事故原因时,才发现了这种物质。”姚伯初对本刊记者说。
姚伯初回国后,利用对南海进行油气探测时获取的标本,开始了天然气水合物的研究。他说,“我在1998年利用我们在南海采集的大量地球物理资料,追踪和解释了约1万平方公里的地震剖面,发现这里存在天然气水合物的地震证据BSR。2001年又用世界上通用的公式估算出南海天然气水合物的资源量达到643.5亿~772.2亿T油当量,相当于我国陆上和近海天然气总资源量的1/2”。
这是一个让人振奋的潜在资源。中国真正寻找到“天然气水合物”直到2007年才实现。在姚伯初的电脑上,有一张水合物岩心放大为5厘米的剖面图:上面丝丝的白色物质就是可燃冰。“发现的地点在南海北部的神狐海域,通过地震波探测,发现了BSR。因为气体总是往高处走,就在BSR出现的陆脊处打了8个点,有3个点采到了‘天然气水合物’。其中含量最多的第二个点,含气量达到40%。”姚伯初对本刊记者回忆。
随着天然气水合物的发现以及对其特性的认识,另一个南海海底的秘密也被解开了。“1998年,在南海西边的莺歌海盆地,为了搞清楚海底的含气带,决定聘请一家外国公司进行海底探测。为了获得精确的信息,其中一个重要步骤是将装有很多检波器的电缆贴着海底,用船拉动收集海底信号。海底的软硬对于这项工程的可行性非常重要。如果凹凸不平或者太硬,会造成电缆断裂,计划难以进行。”阎贫对本刊记者回忆。一开始进行海底地质探测时,取到了很多泥沙,因此提供给外国公司的地情是软底。但工程进行后,电缆在海底一拖即断,损失很大,造成工期延误。最后只好用一种很笨拙的方法,同时起用两条船进行测量:一条船携带海底气枪放炮,一条船装电缆。等电缆完全在海底铺平后,这条船再往回走,把电缆卷起来,不敢再拉动了。但这种方法的进度非常缓慢,这个项目就这样放了十几年。
这个让研究人员迷惑的电缆莫名断裂事件,也是在“做天然气水合物的过程中理解的”。阎贫告诉本刊记者,“海底的原始沉积确实是泥沙,但是天然气水合物会随着泥沙的走失融解,出现气体泄漏。而水中有很多微生物,比如嗜甲烷菌,是以甲烷为食物。它们在消化甲烷的过程中形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又跟海水中的钙结合成了碳酸钙,在气体泄漏的裂缝边形成了很多固体的结壳。它们在海底电缆拖动过程中,造成电缆的断裂”。
那些鱼类
南海的海域深,海水温差大,“上层平均温度为20摄氏度,接近中央海盆地带的水温只有两摄氏度,因此热带和冷水性鱼类都在这片海域共存。全中国3000多种鱼类,南海就有2200多种,占全国鱼类物种的2/3”。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陈铮对本刊记者说。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早期对南海海域进行大规模科考时,他担任生物和渔业资源分队队长。陈铮告诉我们:“按照所有海域的规律,大陆架是鱼类产量最高的区域,我们现在食用的经济型鱼类,主要来自大陆架。”
宽阔的大陆架是南海的一大地理标志,这不仅是它有丰富油气资源的地理筹码,也是鱼类的丰产区。“鱼类喜欢生活在土堆周围容易形成漩涡的地方,因为这种水流区域的生态链特别适合它们。”陈铮对本刊记者说,“水流流动频繁的地方,有机质交换特别丰富。有机质分解成营养盐,再培育出藻类等海洋植物,养活小鱼小虾。食物链由此起步,最终形成大的渔场。”南海的大陆架显然符合以上所有特征:它复杂的、沟壑纵横的地理结构,滋生出大量的漩涡海流。从陆地和海水交换而来的大量有机质,不仅沉积为珍贵的油气资源,也为鱼类生存的基本物质营养盐提供成分。如果以上条件又集中在一块宽阔的陆架上,那就是高产渔场的诞生地。
巽他陆架就是这样一块区域。它是靠近南沙地区最宽阔的一块陆架,“相当于3个东海的面积”。陈铮对本刊记者说。他是上世纪70年代末进入这块海域的,因为“北部靠近陆地地区的鱼已经被打完了,不得不进入休渔期”,陈铮的任务是需要在南海寻找到新的替代渔场。
巽他陆架距离陆地约4天半的路程,因此每次出海就是20多天。陈铮和同事们用了1年多的时间进行拖网普查。“海上工作条件也很艰苦,每人每天只有两口盅的饮水量,但这里就是我们的工作车间,家里只是旅馆。”陈铮对本刊记者回忆,“我们采用的方法是拖网测量。水深100米的地方,要放4倍于海水深的钢绳。拖网在水里一拖就是4小时,根据每网的产量,如果平均下来超过当时渔业公司平均每小时150公斤的渔货量,这里就成为高产渔场的可能区域。接下来渔业公司就要出船进行详查。”陈铮和同事们在这片海域收获到产量最高的网次,渔货量是平均水平的两倍,“拖网4小时,可以得到1吨多的产量,这是相当高的”。
陈铮说,他和同事们在海上待了一年,没日没夜地撒网,“经过1000多个网次的资料,终于确定了4个可能的高产渔场”。陈铮说,渔业公司应用他们的发现,3年在这几个渔场获利一个亿。直到今天,整个华南地区的食用鱼,都还是倚靠巽他陆架的这几个发现于20年前的渔场不间断捕捞。“这里没有休渔期。”陈铮对本刊记者说。
在巽他陆架的近旁,还有南海最大的一片珊瑚礁群岛。南海是世界上珊瑚礁最为密集的海域之一。“因为能生成珊瑚礁的珊瑚虫,在海水50米以下就不会生长了,阳光对它们的生存非常重要。南海的海水能见度非常高,水下几十米都能看清楚。而且由于地处低纬度,每年有两次阳光直射的时间。因此珊瑚的生长特别旺盛。”赵焕庭告诉本刊记者。
在一片海域,所有的资源并不是孤立的,它们和这片海域的阳光、海水、季风一起,相互构成对方存在的条件,共处在一个生生不息的系统里。而珊瑚礁可能是连接这个系统的枢纽。“它有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包括了海洋食物链的最低端,也包括了食物链的最高端。”赵焕庭对本刊记者说。珊瑚礁的多孔结构,不仅为油气的储存提供了条件,还成为一些名贵鱼种的生存场所。“珊瑚礁周围,涡流特别密集,生物量繁多。而且一些名贵鱼类对自己的饲料有选择性。比如石斑鱼,它是肉食性鱼类,喜欢吃小鱼、磷虾,而这些饲料都集中在珊瑚礁。珊瑚礁对鱼类生态的发散性,可以覆盖到岛礁周围40~50米左右的地方。”陈铮对本刊记者说。
陈铮说他在海上这些年,吃过了各种各样的鱼,品尝过最鲜美罕见的鱼类都是生存在岛礁区域的,比如龙头鱼科的青眉,还有石斑……这是珊瑚礁的馈赠,但有时也会有危险。“我们捕到过1米多长的石斑鱼,脊柱骨就有大酒杯口那么粗。船员很高兴,就去炒着吃,把肝脏也吃下去。结果浑身发红发痒、头晕,最后不得不返航去医院。”陈铮说,船员们中了“雪卡毒素”的毒,这是珊瑚礁特有的一种毒素。生活在岛礁区域的大鱼摄入量大,肝脏中储存的毒素就多。
在南海,所有暗沙群岛和露出海面的灰沙岛,下面支撑它的都是千万年累积而成的珊瑚礁石。人类已经在这些岛上建起了可以接纳波音737起降的中型飞机场。赵焕庭告诉本刊记者,飞机着地瞬间的力量达到20吨,这是易脆的珊瑚礁石难以承受的。为了修建这个机场,从外面运的石材,用压路机压成厚厚的粉末,夯实在珊瑚岛礁的表面。丰裕的珊瑚礁石让南海的丰裕资源有了更可能被开发的行动支点。■ 大陆架世界南海地质南海美国资源中国南海珊瑚海水温度陈铮海水密度南海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