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都有一个麦兜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孟静)
 ( 电影《麦兜响当当》剧照
)
( 电影《麦兜响当当》剧照
)
陈可辛说过,《麦兜》是一部文艺片。言下之意,它不具备商业片的票房要素。但第一部《麦兜故事》在香港地区上映时,与《千与千寻》对打,彼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弥漫在小猪身上淡淡的哀伤和一点点光亮应合了沮丧、失意的市民心理,票房竟击败了对方。创作第二部《菠萝油王子》时,又遇到“非典”,作者谢立文告诉本刊记者:“香港和我自己还有麦兜的心情都很差。”谢立文的香港情结此刻表露无遗,他、麦兜、香港是一体的,从不曾分开。它的第4部,也是第一次由谢立文本人做导演的《麦兜响当当》即将上映前,该片的宣传负责人刘咏说:“麦兜没有刺激小孩的东西,虽然放在暑期档,但它并不是一部儿童片,它的观众很多是年轻女性。”
1988年出生的麦兜已经20岁了,但它还是那只“死蠢”的小猪,生长在很普通的单亲家庭,最好的朋友是表弟麦唛,最大的愿望是去看马尔代夫的蓝天碧海,但妈妈只带它去过太平山顶。它成绩不好,考试得“H”却以为自己离“A”已经很近。就是这样温柔、笨笨的小猪,却是香港名片,基本上所有的大活动都有它代言。
麦兜的妈妈不是麦太,它的父母叫谢立文与麦家碧——金融大都市里的两个异类,谢立文负责故事创作,麦家碧绘图和处理一切外务,经过20年的工作,生产了无数关于麦兜的绘本、电影、动画及各类衍生产品。很多人觉得麦家碧讲话慢慢的好像麦兜,但真正的麦兜住在谢立文心里。在这次来大陆前,他没接受过任何采访,也绝不拍照。这次首度开腔,相对活泼一点的麦家碧开玩笑说:“回去会被香港记者打死。”与他们合作的接力出版社的编辑说,如果合影时不小心拍到谢立文,他会非常惶恐。
谢立文的样子很平凡,灰色老头衫,黑框眼镜,无论什么重要场合都趿拉着拖鞋。他能听但不会讲国语,去趟广州就是出远门,惧怕飞机和酒店,最爱去的地方是菜市场。他们夫妻的思维方式都很像小孩子,麦家碧来北京嚷嚷着要吃烤鸭,结果看到一只只油光光的鸭子裸体排队,挂在烈火熊熊的炉里,麦家碧就说:“这里是鸭子的地狱,我们快走。”
谢立文创作的第一只小猪不是麦兜,是麦唛,“它有一家四口,原来的故事是一群小朋友收养一只宠物”。男主角是位小男孩,但在创作过程中,他发现小猪更有生命力,而麦兜比麦唛的故事,更脱离传统,更有社会性。整个交谈过程中谢立文都很谦虚,他不肯承认自己看很多书,虽然有人佐证他到大陆来疯狂扫书;也否认自己关心时事,尽管漫画里展露了他的关注。唯一的一句豪言是:“麦兜的现实性超越所有童话故事。”

20岁的麦兜依旧生活在春田花花幼稚园,它的外形没有发育,但那颗心并不只属于小孩子。“麦兜要求我继续创作它,它的慢、纯真、朦胧,更大部分是香港的反面。香港人对自己、对社会要求很高,你一定要达标。麦兜不是没有要求,而是不对别人做要求。它的贫穷、单亲、考试成绩都是我想探讨的问题。香港人喜欢麦兜是因为从它身上可以寻找一些失去的东西。如果仅仅是小朋友,饿了就哭,它长大后会变成怎么样呢?麦兜只是一个比喻,每个人都是长大了的小朋友,与社会相比,人是很脆弱的,社会是一块铁板。”
他从没把麦兜当做一个虚拟的漫画人物,而像自己的儿子。“你们看到麦兜的忧郁是我对它的担心,它要长大所以我更担心。香港人太追求成功了,我不是鼓励失败,我常常好奇发展到什么地步才是成功,追求积极的、自己的成功定义,而不是别人的。”谢立文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孟子讲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他本人就是住在麦兜心里的成年人,刘咏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麦兜,《功夫熊猫》塑造的是美国救世英雄,麦兜是香港平民,奇迹有可能一辈子不会发生,可生活还是要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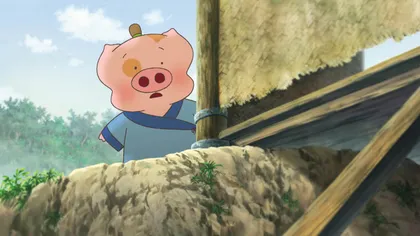
香港人有一种特别的自豪感和特殊的失落感,这建立在它的殖民历史上,很多香港电影里都解释了这种香港精神,但谢立文的理解和他们不一样。在某一集绘本里,谢立文引用了香港的一个传统——抢包山,这个从清朝遗留下来的游戏的规则是:太平清醮期间,长洲北帝庙前会有3个挂满包子的包山,每个包山挂上了约1.6万个包子。包子名为“幽包”,是一种曾被供神的印有红色“寿”字的莲蓉包,又叫“平安包”。不分男女,只要你有能力和毅力,都可以去抢包子。这种竞争激烈的活动危险性很高,曾因导致多人受伤停办过,在市民强烈要求下又重办。“抢包山是一种宗教仪式,香港精神不是茶餐厅、黑社会那些,香港精神是活泼、活力、多元化、包容性。”但在这包容下又竭力维持着自己的传统和秩序,“这不仅仅在香港,是闽南文化、南方沿海文化的共同特性”。
因为语言障碍,谢立文表述得不是很清楚,但能看出来他和其他香港文艺工作者的区别,他很少出门,但并没有把自己囿于小岛。《麦兜响当当》的故事发生在武汉,为此谢立文去了一次武汉,电影中的麦太对“鸭脖子”、“热干面”如数家珍,这只是贴近内地观众最微小的细节,并且这部电影在内地的公映时间比香港要提前20天。第一稿的名字叫《麦兜武当》,创作于3年前,那时还没有《功夫熊猫》。麦兜的先人名为麦子仲肥,是一位发明家。随着麦子的足迹,制作了一幅活动的三维《清明上河图》,这场1分多钟的展示经过“故宫”专家的审核,花了一年多时间,以至于影片推迟上映。剧情三两句就能讲清:麦兜到道家发源地武当学功夫,参加了“国际幼儿园武术大赛”,这一路上它见到、听到、感受到了很多。
 ( 麦家碧 )
( 麦家碧 )
谢立文借助武当学艺的故事,阐述了他的哲学思考。道长教麦兜“推手”时说:“能如水磨推急缓,云龙凤虎象周旋。”他把老子的精华传授给麦兜:“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一段对麦兜和观众来说,也许过于艰深,但对谢立文来讲,童话从来不只是童话。“要你明天充满童心,你也可以做到,只是需要很大勇气,去改变自己。当你面对社会要求和奇异目光时,你究竟会怎么做?我永远不会填这个答案,而是要读者去反思。”
谢立文创作过一个漫画形象叫“屎捞人”,也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创意。一坨小屎人,以手纸做围巾,以夜壶当帽子,在下水沟里活动,每天都担心会被一股急流冲散,愿望是能够做花肥,让自己的生命为他人谋幸福。他生活在最黑暗、最卑微的地方,脆弱、悲情、自嘲、浪漫又荒谬。他比麦兜还可怜,小猪还可以被妈妈哄着,去不了马尔代夫总可以爬上太平山看看灯海。屎捞人的梦想只是看看花,看看外面的世界。谢立文说:“这是一个自我肯定的故事,万一生出来就是坨屎,自杀还是继续生存做一坨好的屎?人在迷茫中才会想这个问题。每个作者都这样,金庸也会想透过作品讲一些东西。”
成功的童话都有现实寓意,刘咏也是《喜洋洋与灰太狼》的宣传负责人,这部制作极其粗糙的动画片在迎面碰上与《赤壁》的PK中,一度把《赤壁》逼到了200人的小厅,而它占据着600人的大厅。有句口号是:“嫁人要嫁灰太狼,做人要做懒羊羊。”“结婚几十年全家没吃过羊肉,开荤就是青菜三明治夹毛毛虫,为了让老婆孩子吃上羊,灰太狼屡败屡战,对老婆打不还手,堪称21世纪新好男人。”刘咏说,片子成功基于它符合当下主流价值观。同样的,麦兜身为一只小猪,但它并不蠢,电影里麦太带它参加智商提升班,老师说:“它只是单纯。”
“单纯的人有几个能成功呢?麦兜打动人的正是它略微的灰色。”■ 每人一个香港动画中国电影麦兜麦兜响当当喜剧片香港电影家庭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