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尔曼的法律史研究
作者:薛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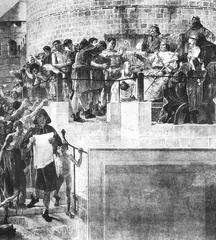
( 12 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六世向巴黎市民颁布第一个王室宪章 )
法律与革命
伯尔曼分别于1942和1947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和法学士学位。他写了25本书、400多篇关于俄国文化和比较法律史等方面的论文,曾经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执教37年。
伯尔曼2006年在接受亚特兰大一份报纸采访时说,他跟所有孩子一样,很小时候就开始学法律了:“一个小孩说,‘这是我的玩具’。这是物权法。一个小孩说,‘你答应过我的’。这是合同法。一个小孩说,‘是他先打我的’。这是刑法。一个小孩说,‘爸爸说可以的’。这是宪法。”
当年他决定研究苏联的法律时,没人能教他,那还是一片学术上的处女地。他就开始自学,从学俄语开始。因为会俄语,1958年,他代理了柯南道尔的财产官司,他希望从苏联出版柯南道尔小说要付的版税中抽取一些作为报酬。他在莫斯科市法院打赢了官司,但在官司被上诉到俄罗斯联邦高级法院后他输了。
伯尔曼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出版于1983年的《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其中的结论在许多方面与惯常的先入之见有冲突。首先,他反对强调西方各国法律独特的民族性格和独特历史,认为存在着一个西方各国共同拥有的法律传统,历次革命对西方法律体系造成了剧烈冲击,但革命只是更新了它,而没有彻底推翻它。所有西方的法律体系都有共同的历史根源,都具有法律高于政治(君主也要受法律约束)、在同一社会内部存在各种法律体系的共存和竞争等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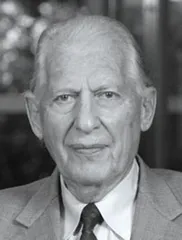 ( 哈罗德·伯尔曼与《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
( 哈罗德·伯尔曼与《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
其次,传统上把西方历史分为古典时代、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灭亡、中世纪以及近代(始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他认为这种分法将中世纪贬低为只是近代得以涌现的背景,而西方法律传统源泉恰恰在中世纪。
2004年伯尔曼出版了《法律与革命:新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伯尔曼已经计划好了他的“法律与革命”系列的第三卷,乃至第四卷。至于能否完成,他曾经说:“那取决于上帝——看他想不想看了。”
伯尔曼说,各个民族的风俗和惯例演变成法律,然后地区性的、多样化的法律体系又稳步演化为普遍性的西方法律体系,在世界法的创制过程中,西方也将扮演带头的角色。由于这种理性主义的倾向,为了说明这种演进过程,为了辩称美国革命“半是法国的、半是英国的”。他错把法国革命说成是发生于美国革命之前,另外,如英国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在《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一文所说:“早期的美国人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依靠自己开展政治创新,独立伊始的美国明确地反传统。美国独立的奠基者拥有欧洲的思想传统和本土政治习惯与经验两种资源。但是,如历史所示,欧洲传统对美国的馈赠(哲学上和宗教上)一开始就被显著地理性化了:他们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拥有的一切都归功于自己的努力。”
从惯例到法律
在中文中,“法”这个字,左边是水旁,表明古人强调法乃是自上而下颁布的。这跟“法律是一种统治工具,一种实现立法者意志的工具”的说法是一致的。而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指出,法律不仅仅有自上而下的传播,也有自下而上地传播的一面。“法律渊源不仅包括立法者的意志,也包括公众的理性和良心,他们的习俗和惯例。”
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阶段,罗马天主教会努力建立绝对的统治。各国国王也寻求绝对的王权。教会与国王不仅互相竞争,他们还面临来自城市、封建领主和商人的立法过程的竞争。因而西方的统治权非常分散,多方竞争使谁都不拥有绝对的权力。法律就不是统治权的产物,“西方法律传统部分产生于基层团体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社会和经济互相联系的结构。相互关系的行为模式需要规范:惯例被转变为习惯、习惯最终又转变为法律。后一种转变即习惯到法律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威的出现。于是,法律成了被改造的习惯,而不只是立法者的意志或理性”。
2006年美国经济学家唐纳德·布德罗(Donald Boudreaux)在《自发秩序和法律》一文中对这种理论做了生动的阐发:“亚当·斯密注意到,我们能吃到晚餐,不是因为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因为他们关注自己的利益。他解释了每个人的自利行为跟其他人的自利行为结合起来之后,带来了一个和平、高效、复杂的未经任何人设计的经济体系。这种经济体系是看不见的手的结果。分散的、自利的行为能不能产生法律呢?答案是肯定的。”
他举例说,在假期购物季,当你在商场的停车场寻找车位的时候,注意一下当你看到有辆车正要离开时的情形。如果没有别的司机看到这个车位,你开过去,并给正在离开的司机留出足够空间供他开走。你也许还会打开转向灯,告诉别的可能会靠过来的司机那个停车位你要了。当别的司机真的开过来的时候,看到你的车正等着那个停车位,他们都会因为错过了这个车位而感到失望,但他们不会跟你抢。这里存在一个物权制度,没人把这个规则写进条例,甚至也没人意图制定类似的物权,停车场上人们的日常互动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习惯,即最先看到要空出来的停车位的人可以通过靠过去来伸张他的所有权。最先发现车位的人期望别人尊敬他这种权利,通常他这一期望都不会落空。
这就是一个自发法律的例证。这种法律是未经计划而出现的,但又因为被广泛遵守而能将摩擦减少到最小。“可能会有人反对给如此平常的不过是出于礼貌的要求贴上庄严的法律的标签。但称之为法律是合适的。公平、公正的法律是那些能够给我们提供追求自己的目标的空间同时又尽可能地让我们避免互相妨碍的惯例。有人说只有主动制定的、正式颁布的才叫法律。但稍微想想就知道这种说法不正确。很多政府官员写下来的规则其实不是法律。老实说吧,在明知是限速55公里的路段你有没有把车开到时速60公里?如果是这样,你就明知故犯了明确地标出来的限速55公里的规定。可实际上,真正的法律不是这样的。真正的法律说,在路况和道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的时速可以超出限速5到10公里。这种真正的法律并没有写在任何地方,但大多数司机和高速公路巡警都知道并遵循它。”
法律和道德的分离
伯尔曼概括了西方法律传统的十个特征,第一个特征便是,西方的法律虽然受到宗教、政治、道德和习惯的强烈影响,但政治和道德本身并不是法律,法律有其自身的特征,具有某种程度的自治。
法律和道德分离后,西方强调的是法律的积极作用,中国古代强调的却是法律的不足。伯尔曼说:“从耳闻目睹中,我得知在中国影响深远的儒家道德把法置于礼之下。古代圣贤确立了崇高的礼,它与人的内在情感和天地之序相一致,规范家庭、朋友和君臣的人伦秩序;礼的道德是利他的;各种礼仪为生命增添诗意和美感。反之,法被认为是由现代人的命令和规则组成的,用以节制他们所管治的社会的活动;它是机械化的、不带情感的,它缺乏普世有效性;法不同于礼,它不是根源于人的内在情感。儒家礼重于法的思想并没有妨碍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向西方取经发展某种法制,然而儒家的礼法之分和以礼为尊的思想,却会妨碍中国全面参与我所称的世界社会法的发展。”
伯尔曼大概担心“以礼为尊”会导致轻视乃至排斥法律。但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指出:“读书人应试做官后,便不能不懂法律,不应用法律。听讼成为考核成绩之一以后,读书人自不会反对法治。法家固然绝对排斥礼治,儒家却不曾绝对排斥法律。”
“礼与法都是行为规范。礼是借教化及社会制裁的力量维持,一个人有非礼的行为,所得的反应不外乎舆论的轻视、嘲笑、谴责或不齿,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制裁。法律是一种积极的或有组织的制裁。但礼未尝不可以借法律制裁来维持、推行。同一规范,在利用社会制裁时为礼,附有法律制裁后成为法律。成为法律之后,既无害于礼所期望的目的,也不妨害礼的存在。”■ 尔曼研究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