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隐
作者:苌苌
( 张北海,本名张文艺,祖籍山西五台。1936年生于北京,长在台北,攻读洛杉矶,任职联合国,现定居纽约,因一系列“纽约随笔”闻名海外,2000年发表长篇小说《侠隐》。 )
《侠隐》的背景是上世纪30年代的北京,男主角李天然刚从美国回来,在阔别5年的北京城里游荡,寻找他的仇人。故事是虚的,细节是实的。李天然每天步行,从干面胡同到东四北大街,从隆福寺到西四,在北京生活的人对这些地名备感熟悉,每每捧读,就看见一个着长袍马褂的小伙子在那些灰色的胡同里穿行。张北海的文字质朴,但很有味道:“说是入秋了,宝石蓝的九月天,还是蛮暖和的。”细节令人印象深刻,说“李天然坐洋车回家,拉车的要五角,老仆役老刘正蹲门口,掏出两毛给了车夫,‘两毛都多给了’。李天然怪自己事先没说好价钱,又多给一角”。各层次人的性格都出来了。还有股不动声色的贫劲儿,东单十字路口的交警坐在高高的岗亭里,拿着扩音喇叭喊:“奔东的洋车快着点儿。”
阿城在台北麦田版《张北海作品集》(2006)的序文里说他“看重《侠隐》是因为它颠覆了以往的武林小说。在旧武侠小说的作者都成了大师之后,总要有新人抖擞一下吧”。又说文字是“那种贴骨到肉的质感”。这位李大侠一身好功夫,总是速战速决,就是有点馋,逛隆福寺,买兔儿爷,吃炒肝、灌肠,八成是“丰年”家的吧。蹲守死敌的据点,还不忘买块烤白薯。到了西四,喝碗羊肉汤,他大概去的是西来顺,饿了,想吃“大酒缸”,说起“大酒缸”,记得唐鲁孙先生书里提到过,好像是一类酒馆的统称,一个叫“三义合”的在西四附近,现在连块砖都没有。李大侠还爱美,回国了,发觉自己的西装不合时宜,就去做新衣服,结果和寡妇裁缝一见钟情,三天两头跑去做长袍,做完单的做夹的,做完夹的做棉的。再不成,就做块手绢,让人家给钩顶帽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老北京人知情守礼的刻画细致入微,那份客气,不输日本人,那样讲礼,西方人比起来都成了蛮子。小说里的人物性格比较单薄,黑白分明,复仇的大线索倒没什么要紧,就是写老户人家怎么过日子,平时吃什么,穿什么,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去别人家做客应该什么做派,乔迁了送什么礼,主佣之间相敬如宾,佣人关心主子,主人体谅佣人。老北京人的日子真温暖,或许作者有一个下意识心愿,就是借这部现代武侠小说的叙述,将他那一代和再上一代的一些信息传达给今天年轻一代。在没多久的从前,北京曾是如此模样,有人曾如此生活,如此面对那个时代的大历史和小历史。对于这一猜测,作者在专访中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笔名和北海公园有关么?
张北海:没有关系,好念好记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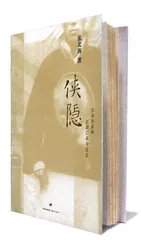 ( 《侠隐》 )
( 《侠隐》 )
三联生活周刊:小说创作时期,你的生活工作状况是怎样的?
张北海:1994年,我的盲肠炎转为腹膜炎,在医院里休养了9天。那年我58岁,在病床上想到还有两年就要从联合国退休,才又反省我30多年来有关美国的非虚构写作,是否应该探求一个新方向。我从小就看武侠小说,尤其因时机关系,欣赏上世纪30和40年代几位大师,如郑证因、白羽等前辈的作品。同时,又因我从小就读外国学校,也很欣赏西方武侠类型的故事,如西部电影和私家侦探,以及《超人》、《蝙蝠侠》等连环画,这些种子,多年后在我脑海中发芽。
因我生在北京,为了认识我生长的故都,手边早已收集有上百本关于老北京的中英文著作。出院后,我比较认真地在北京、香港、台北、纽约,收集所需资料,并开始做笔记、构思,这项工作进行了两年。1996年退休即在纽约家中开始动笔,我为自己订了一些工作纪律,即使写不出一个字,也必须在书桌旁“胡思乱想”。这样,小说42回的每一回,我都曾一写再写,一改再改,再又重写了至少两三遍,直到2000年完成。写作时间和字数没有定,但至少每天工作8小时,写500字,而且多半要搞到凌晨三四点,那几年的写作投入,可以说是到了忘我的境界,以至于有天下午出门,突然感到万分惊讶——“怎么北平今天有这么多外国人!”(你会梦见笔下的主人公么?)与其说我会梦见笔下的主人公,不如说我沉迷写作期间,早已化身为他,甚至以为身在1936年的北平。
三联生活周刊:小说读起来,就好像跟着主人公在30年代的北京游荡,你是怎么做到的?
张北海:既然我决定以写实笔法写《侠隐》,而且具体把故事放在30年代的北平,那当时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市容街道,就不但成为必须,而且成为书中的一个角色。且又因那是“卢沟桥事变”前后,更必须考虑国内国际局势。《侠隐》之所以给读者一种真实感,还是作者的意愿,也正是为什么我在动笔之前要花两年时间去研究的原因。这项工作费时费力,但作者和小说的要求有了满足,也达到它所要达到的目的,今天回想,这番努力和心血反而是一种甜蜜的痛苦。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说你的小说是“反武侠的武侠小说”,你对武侠小说和侠义精神怎么理解?
张北海:当我决定写一部武侠小说时,就决定要写一部“现代武侠”。但所谓“现代”,不仅指文字语言,而且包括内容和主题,《侠隐》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一个模糊遥远的过去,一个神奇魔幻的世界,而是发生在一个非常真实,至今仍有不少人走过并存有记忆的特定历史时刻——燃起抗战烽火前夕的30年代的北京。这项决定迫使我考虑“侠”在现代社会生存的问题,因此,除了带动情节发展的报仇主题之外,我给予小说另一个主题,而无论此一主题在历史上成立与否,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即“侠之终结与老北平的消逝”。
我对侠义精神的理解应该和一般人差不多。世界各个文明都曾有“侠型”人物存在,虽然多半生活在人的脑海中。以中国为例,远在春秋战国时代,法家就批判“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今天的法制或专制社会,更无法接受一个“侠”来决定他人生死。罪与罚是国家法律的权力,这也是为什么以“不投靠官府”为师训的李天然,仍不得不与半官方的蓝青峰合作的原因,才能报仇。“一打起仗来,什么规矩都没了。”因而此举可在今日之法律和道德层次上说得过去。“侠”在今天,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存在,不如说它是我们的梦。也就是流传多年的“千古世人侠客梦”。
三联生活周刊:最后,基督徒的马凯大夫一家不是打消了李天然的复仇念头,而是接受了他的杀戮复仇,你怎么看这个结尾?
张北海:马大夫虽然是基督徒,但他的专业是医生,而非传教士。而且他在北京多年,成了半个中国人,是他给了主角英雄第二次生命。不是信仰使他协助侠隐,而是出于爱心和现实。他女儿不但有另一种爱,而且有心报恩。这一切当然都是作者在特定具体情况下做的安排,这是现实,而与信仰无关。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长期居住的三个城市——北京、台北、纽约,分别对你意味着什么?
张北海:这几个城市都是我人生道路上的里程碑,任何一个城,包括我在纽约之前住了10年的洛杉矶,都让我必然想到我人生成长的某个阶段,好坏都有。
因小说背景是北京,所以让我引用王德威的评语来看他如何评价我看北京:“张北海所依赖的,不是悼亡伤逝的情绪,而是文字的再现力量。除了怀旧,他要创造他的理想城市,是在这里,回忆与虚构相互借镜,印象与想象合而为一。”至于台北,无论50年代台湾社会多么保守,政治多么压抑,但是对从青春期过渡到成年期的我来说,还是享受到当时所能享受到的几乎一切。而纽约,我已经住了35年。也写了差不多同样久,但如同古人所说,书读得越多,越感到无知。因此写完小说之后,我去纽约大学上课,不为学分,不为学位,只为兴趣,并为再写纽约多打一些基础,认识过去,才了解现在。 文学小说侠隐李天然张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