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414)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列那,吴静男,陌桑,石头,)

两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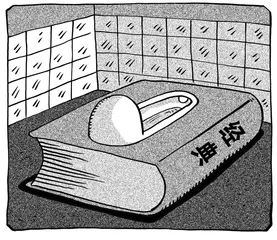
◎列那 图◎谢峰
陪一个文科教授和一个理科教授出差。一走进软卧包厢,理科教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检查了一遍灯、锁和音箱所有设施。文科教授则是从贴身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小本本,连问了我一串问题:姓名?年龄?毕业学校?专业?家庭住址?理科教授毫不掩饰地大笑说,他就这样!跟谁第一次见面都这样!
文科教授非常中肯地建议我继续读研,并且还学历史。理科教授则不同意再学历史,他认为应该重新选择一门实用学科。文科教授说,不要凡事只追求实用,知识不见得都有用。我说不管学什么,恐怕为时已晚。文科教授说,他女儿比我还大两岁,还在读博,已经不打算要孩子了。他儿子跟我一样大,不仅没要孩子,连婚都没结。听文科教授讲,他儿子准备结婚的时候,又遇到了另外一个女孩,他更青睐于后来的女孩,而教授和老伴,还有教授女儿则一致认为,好女孩是绝对不会去做第三者的。结果教授儿子至今孤身一人。理科教授又是大笑说,最矛盾的不是你儿子,而是你女儿,她自己可以解放到不去做母亲,却接受不了弟弟婚姻里的第三者。
理科教授旁若无人地拿出自备的面包和矿泉水,边吃边讲起了他最近的一个课题“关于文化的数学表达”。从他咀嚼的力度和速度中可以感知他的兴奋度。文科教授没有对“数学表达”发表见解,而是郑重告知理科教授,晚上吃淀粉类食物会损害肾脏。理科教授怔了片刻,求证道:这是实验室的结论吗?列车服务员为文科教授解了围,送来了免费晚餐。文科教授说,你们的服务很不到位,很多乘客不知道有免费晚餐,上车前就吃过了,这样很浪费。理科教授说,你们在决定提供免费晚餐前,应该先做一份定量分析,这样就不至于造成浪费。接着,文科教授开始拿民航做对比,提出了若干条提高服务质量的建议。而理科教授则索性拿起一份旧报纸,在空白处画起了线性分析图。
第二天早晨盥洗时间,理科教授拿着车上提供的盥洗用具(一个密封小塑料盒)琢磨了很久。他问文科教授,这1.2厘米×1.2厘米的小方块儿是什么?文科教授说,这还用问,香皂呗!理科教授打开了小方块儿,孩子一样得意地狠拍了文科教授一下,哈哈大笑:“你又错了!不是香皂,是毛巾!”
到达目的地时,火车晚点了。等我们出了站,接站的小年轻儿已在寒风中冻了很久。可理科教授却不紧不慢地说他需要方便一下。文科教授看了看小年轻儿的脸色,对理科教授说,这种事儿你就应该下车前解决掉。
在往站前停车场走的时候,我和小年轻儿要帮两教授(两位教授均已年入古稀)提箱子,这次他们观点空前一致,谁也不肯让我们提。文科教授说:我们老而不衰。理科教授这次说了一句很不理科的话:“我们不是在机场,就是在去火车站的路上。”
关于Dress Code
◎吴静男
李咏和毕福剑是娱乐节目主持人。他俩在镜头前的着装与罗京、崔永元有很大不同:在后者穿的那种外套上绣一朵花或点缀几颗闪亮的珠子什么的,有时也会系一点“超女”那样的坠物。以后会不会穿布兰妮那种低腰裤,将一抹白肉与缀在裤腰上的一圈宝石合起来璀璨夺目呢?完全有可能。《纽约时报》时尚评论员凯斯·霍图认为:“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新时尚,问男孩吧。”这话娱乐版的翻译应该是:“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新时尚,问李咏吧。”有人可能觉得像李咏那种非男的装扮不符合主持人的Dress Code,那是他不知道男装利用女装的成功市场元素正在成为世界潮流。男士和女孩都可以穿,已经是这个时代的Dress Code了。
Dress Code直译就是穿衣代码,意译就是着装要求,也就是什么场合下穿什么衣服。一些从海外归来的成功人士,有一点让他们甚为不惯,就是到处能看到不懂Dress Code的中国人:一些女士穿着高跟鞋去旅游,一些男士穿着运动服去听歌剧,一些学生穿着夹鼻拖鞋去见教授。其实这是多生了的气:穿高跟鞋去旅游的女士是把旅游当艳遇,穿运动服去听歌剧的男士是准备拼命鼓掌来热身,而穿夹鼻拖鞋去见教授的学生是向老夫子施行时尚教育,都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场景着装要求。我有一位熟人,下雪天还穿一件短袖,引起我不快:明显的不Dress Code嘛!谁知人家早年在一次手术中被医生误伤了神经,变得冬天不怕冷,夏天怕冷,我们穿短袖的时候他要穿羽绒服。这个文明礼貌方面的事故让我明白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Dress Code,外人是不好轻易置喙的。
其实,Dress Code是一个中国人古已有之的词汇。那时的叫法是“垂衣而治”。当我们的孔圣人教导大家“君子不以绀鲰饰,红紫不以为亵衣”时,洋人们恐怕还在袭击长着又黑又密的长毛的猛犸象、犀牛、熊,然后用刀剔除动物兽皮上的肉渣和筋腱,以防兽皮发臭或过于发板,留着好披在自己身上吧。那时洋人的Dress Code,是在一次怎样的袭击中选择什么样的动物皮,据说这样可以夺得被狩兽的力量,以便增加自己的力量。估计除此以外的场合就无所谓Dress Code了。《左传·哀公十五年》记载:子路为了营救主人孔悝,一个人持剑与两个武士决斗,寡不敌众,被武士用戟扎通了胸口,帽缨也砍了下来。子路躺在地下,正要断气的时候,忽然想起帽缨折了,帽子也歪了。一个挺讲究礼节的儒生,怎么能衣冠不整地死去呢?他强挣扎着把帽子戴正,把帽缨系好,说“君子死了,不应该不戴帽子的”。天底下恐怕再也没有如此伟大的Dress Code了。
乡下美元
◎陌桑
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饭局,席间有国外某电脑的大中华区品牌推广部经理,有电台女主播,有时尚杂志的编辑,还有公关公司的业务主管。茶过三巡,菜上五味,小姐们早已热络起来。一小姐说,她刚从泰国回来,包里还装着几百泰铢。最近她没有时间再到泰国去,问在座的谁要去,这点零钱就送给谁。
于是大家话题就转到外币上。另一小姐说,她手头也有几千荷兰盾,是她从日内瓦去海牙时,用瑞士法郎换的,当时她的信用卡上其实还有两万多欧元。用瑞士法郎换荷兰盾,无非是要体验一下像荷兰当地人一样消费的乐趣。该小姐指出,在欧盟国家使用欧元,就像在上海的里弄操着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一样不爽。
接着,非洲的、南美的,地图上根本就找不着点的南太平洋小国的听都没听说过的货币都出来了,我惊愕地看着她们,仿佛在参加一个专业人士的外币收藏交流会。
为了在餐桌上分享话语权,我不失时机地说自己手头也有一点美元。不料,女主播白了我一眼,时尚编辑嘴巴可不饶人:“有美元?多土!现在中国的农民都成群结队逛纽约!”我连忙闭嘴。于是,她们继续由这些货币深入到这些货币所在的热带雨林沙漠峡谷等神秘境地,互相不着边际地炫耀自己的境外游经历,而我活了半辈子,没出过国门半步。而关于那点土美元的“原始积累”过程,我更是一个字都不敢提。
早前,我在老家一国有企业里做工。我的老板喜欢喝一种名叫某某窖的酒。这种酒除了在盒子里装着打火机、手电筒等小玩意儿外,还在瓶盖下藏着一美元。每次老板陪客,都是我开酒,我就利用职务之便,把这些美元据为己有。有时候,老板在公司小食堂请客,酒瓶就由小食堂服务员开,美元也流落到她们手中。当地只有一家农村信用合作社,营业员看着那些皱巴巴的美元零碎,辨不清真假,就以本社不办理外币业务为由,不予兑换。于是我就出五到六元人民币的价格,从她们手中收购美元。几年后,老板把公司喝掉了,我就揣着那点“酒瓶盖”到了上海。在北京西路,我顶着营业员怀疑和鄙视的目光,把这些美元零碎存进银行,居然没有假钞。
银行里这点美元,其实不够我出国旅游,更不够将来孩子出国留学。我就让它在银行里缓慢地长着霉斑一样的利息,或者当着一段尘封的往事。跟眼前小姐们的外币比较起来,的确土得掉渣。
谈笑间,桌子上早已杯盘狼藉。小姐们怀揣各色外币先后借故离去,去荷兰的人也不知道“go dutch”,只有我乖乖地去前台付账。
勤劳小嗡嗡
◎石头 图◎谢峰
挺喜欢戴维·洛奇以前写的书——他的新书越来越不好看了。最喜欢的也不是《小世界》,是它的前传《换位》。《换位》用一句话概括:一位英国文学系教师和一位美国文学系教授短期互换工作和媳妇的故事。那个呆呆的英国人漂洋过海,带给美国同事们一个游戏,很绕,也比较闷。
一群人,每人叫一本书。比如某甲说:《看图说话》。这本书必须是某甲自己没看过,但是假设别人都看过。如果别人有一个人表示没看过,某甲就得一分。每个人都这样叫一本书。最后谁分数最少,谁赢。是挺绕。
在小说里,一个美国某大学文学系教授,有超强的变态的赢的欲望,一怒之下叫了《哈姆莱特》,把大家都吓着了,谁也不信。这老兄急得杀鸡抹脖,信誓旦旦。过了几天,他就没有被续约,因为学校不敢聘一个没看过《哈姆莱特》的文学系教授。
前一阵偶然和几个朋友玩了一次,发现这真是个奇妙的游戏。这些参赛选手,起码也是跟黄健翔平级的“知识分子”,不排除若干硕博。也都不是只啃专业的呆子,一个个博古通今,挥斥方遒。外国书么,非我族类,其心必殊,先不管。国产书里,没玩一会儿,四大名著全都有人叫了。而且差不多都得分。有点抓狂。然后一个强人叫了《金庸全集》,就是说只要你看过一本金庸的书,就没法给他加分。都以为游戏结束了:谁没看过金庸呢?不读金梁古,枉做念书人。这时一位大侠横空出世:加分,我一页也没看过。那个倒霉的强人一下子被加了起码14分。这加分的大侠是某著名学府中文系的老师。
再通行的书,也有人没看过;再古怪的书,也有人看过。
在小说里这个游戏名叫“羞辱”,意思是,只有通过显露自己的不学无术才能赢得比赛。问题是怎么样才不算不学无术呢?是读书越多越经典就越有见识么?通览所有经典读本的人,既有可能是蜜蜂,也有可能是苍蝇:相同处都是勤劳的小嗡嗡;不同处,一个边吃边屙蜜,一个边吃边拉屎。 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