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斯卡纳的阳光之下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宇文鸿吟)
 (
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和乔脱、洛伦米、皮萨诺等画家的壁画作品,是中世纪艺术的伟大杰作,使阿西西成为意大利和欧洲艺术与建筑发展汲取力量的源泉 )
(
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和乔脱、洛伦米、皮萨诺等画家的壁画作品,是中世纪艺术的伟大杰作,使阿西西成为意大利和欧洲艺术与建筑发展汲取力量的源泉 )
在德国读书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永远也搞不清楚为了那遥遥无期的毕业究竟还应再做什么才能功德圆满。2003年我又遭遇这样的麻烦,当我去找系办老师询问毕业论文事宜时,他把我的那叠成绩单翻检了三遍,才抬起头来问我,“请问您的学术旅行的证明在哪里呢?”
我冲出来抓住碰到的第一个同学问他这件事怎么摆平,他带我去信息栏,指点说近期有两个学术旅行,或去丹麦考察近现代油画,或去意大利考察文艺复兴壁画。他向我极力推荐意大利之行,我飞奔前去报名,正好还剩最后一个名额。
10月4日清晨,我们一行在波鸿市火车站会合,由60多岁的克瑞滕贝格教授带队,听说在意大利的食宿将由教授的一位老友萨利尼先生承担。
过了波河平原后,地势重新起伏,但是山形平缓,基本是丘陵形态。路边的指示牌上出现了佛罗伦萨的字样,我们已经进入了托斯卡纳地界。
天色渐暗,车子离开高速路,转上了乡间公路,道路越走越狭窄迂曲,两侧灯火也越来越稀少,瓦蓝的天边已挑起了一弯残月。我悄悄问司机沃尔夫冈是不是快到目的地了,他乐呵呵地说,是啊。我问那边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真的是像传说中的豪奢华贵,每顿饭都有五道菜么?沃尔夫冈哈哈大笑,说,“嗯,很有可能啊!”他一打方向盘驶入了一条林间小路,碎石铺就,窄到几乎难以错车,月光下只能隐约看到车灯射亮的十来米前方和两旁的峥嵘树影。这样开了十来分钟,密林退去,前方隐约出现一个黑漆漆的小村落,道旁低矮古旧的农舍中突然跳出几条狗来。又前行了几百米,车子缓缓滑下一个满是砾石的斜坡,终于停在一道石墙前。教授终于出声说,到了。
 ( 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修复后在1999年11月2日重 新开放,红衣主教兼梵蒂冈国务卿索达诺主持了弥撒。该教堂在1997年因地震造成了部分屋顶坍塌而关闭 )
( 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修复后在1999年11月2日重 新开放,红衣主教兼梵蒂冈国务卿索达诺主持了弥撒。该教堂在1997年因地震造成了部分屋顶坍塌而关闭 )
穿过一道石拱门,大开的厚木大门上包了铁皮,其上有成排的粗大圆钉和沉重的铁门栓。门内先是一个狭长的院落,两边各有一道石围墙,其上凌空搭了木架,架上爬满了葡萄藤。左边较高一道围护着内部另一重院落,上面探出高大茂盛的松枝,右边的矮墙下赫然便是陡落而下的山坡,一目望去只见一片悠然起伏的缓丘原野,在月光下显得分外空旷辽远,其中居然还有痴痴的羊群徜徉。
进了一间居室,只见里面布置了陈旧的黯黑木器和巨大的红丝绒沙发,屋角是一个造型别致的壁炉,旁边摆着一架古老的木纺车。这间屋里非但没有任何雕梁画栋意义上的精巧和粉饰,甚至墙面灰泥都已斑驳不堪,大片地裸露出里面的砖石材。教授为老者翻译说鉴于人数,我们一行里有一位需要单独住,不知道谁有这个勇气?我就自告奋勇。老者叫我自行安顿,领着其他人走了。

我惴惴地摸索着电灯开关,推开另一道木门,灯光下我一下子傻了。里面是一间更大的六七十坪的敞亮客厅,沿内墙放着一座极为气派的白色转角沙发,对面又是一道两开的大望台,为了防风寒,内面采用巨大的落地玻璃幕窗将其隔开。厅正中大幅的古红地毯上面安放一条长木案,上面摆放着两个铁烛台和一个线条优美的玻璃瓮,案旁是一个造型奇特的三足木椅。除此之外还另有两个台几和一个写字柜,所有这些木器都古旧得黝黑润泽几乎有了金属质感,看上去都应是百年以上的物品。地面铺着方地砖,虽然其表面原本应不甚平整,但是经过年深月久的磨砺,又打上了一层维护的油蜡,其光润堪比大理石。
再往深处寻去,右手边先出现了一间厨房,一进去就回到了21世纪,里面炉具烤箱冰箱等一应俱全,箱柜里也厨具整齐,不过外部仍用粗木面料和大理石台面营造出复古的印象。出了厨房再往里走就进入一间精洁的单人卧室,敷设粗糙的白灰墙,洁白的床单卧具,朴素的铁架床,床头墙上悬挂的黑铁十字架,微黄的床头灯光下,还原了一种修道院式的清静境界。卧室后面是一个卫生间,里面有优雅的洁具和简单的淋浴设施,当地缺水,所以基本都不使用浴缸。
 ( 每年6月2日和8月16日在锡耶纳举行的帕里奥传统赛马盛会是托斯卡纳最重要的节日。有关这项比赛的最早记载出现在1283年 )
( 每年6月2日和8月16日在锡耶纳举行的帕里奥传统赛马盛会是托斯卡纳最重要的节日。有关这项比赛的最早记载出现在1283年 )
看到这一切,我惊喜得差点没有一口气背过去,这么大一套屋子给我一个人住,这算什么星级待遇呢?我急煎煎跑出去向同学们炫耀我的运气,只听见外面女生们惊喜的叫声此起彼伏,那班人原来已经在狂喜中忙着互相串门攀比了。他们每两人分到一套一楼一底的房子,基本上大客厅是在底层,沿木楼梯上去,二楼便是卧室和卫浴。各处的格局虽均有不同,但陈设大体都在维持中世纪风味的同时务求雅致。置身其间,随处都是新奇而古拙的细节,俨然便是置身于托斯卡纳民居博物馆中一般。
教授来找我们,不出所料地见到我们大惊小怪的样子,显然觉得自己的这个关子卖得非常成功。问他住在哪里,他原来就住在我们曾进入的那第一间居室的二楼,在底层那壁炉的对角方向上是一道沿墙而上的石阶,最上面的几级彼此分离独立,是用整条的白石板插入墙面固定而成,乍看上去就像浮在空中的云片一般。拾级而上就到了教授引以为傲的“空中楼阁”了,面积虽小,家具却最为精美,大睡床四角木柱环立,上面撑起高高的顶篷四周垂下帷幕。外墙上两道圆拱窗正面朝原野,居高临下,视野极佳。
 ( 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内乔托的壁画作品《向鸟儿们布道》 )
( 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内乔托的壁画作品《向鸟儿们布道》 )
后来才知道,此地名叫卡沃里山庄园(IL Borgo di Montecalvoli),原是当地一处古老的村庄聚落,最早可见于1199年的文献记载。这个村落坐落在一个陡坡的边缘,营建中有意识取了地势之险,陆续添筑了高堰长墙和一座望塔,从而一定程度上拥有了类似城堡的防御功能。从这一点上,明显受到中世纪战事频仍的托斯卡纳地区的防御性城市建设理念的影响。目前该庄园及附近大片田地都是此地主人的私人产业,他大富大贵之后就隐居于此,那无数套住房以前都是给他那十几个孩子使用,如今那些后代多已经成家立业在外自立门户,住房也便空置下来只是偶尔作为客房使用。各类豪宅我见过听过的也有不少,但能在此类800年历史原汁原味的古宅中小住,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经历。临行前,主人曾骄傲地指点门边墙上的一个金属牌给我们看,那是欧洲古宅文化基金会颁给年度优胜者奖牌。
托钵僧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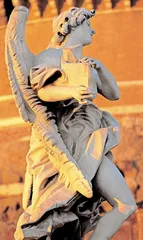
前一天明显有些喝高了,梦中全在厮杀征讨。次晨起身,但见骄阳明媚碧空如洗,庄园中色彩鲜明处处笑逐颜开的样子。
这一天的考察目的地是宗教名城阿西西(Assisi),该城位于佩鲁贾(Perugia)以东,虽然严格讲已不属如今托斯卡纳的行政辖区,但历来受到该区的文化辐射。阿西西旧城位于苏巴西奥山上,在天主教世界乃是地位仅次于梵蒂冈的一座重要圣城,终年吸引着大批朝拜者。此处是圣者圣弗朗西斯科(San Francesco或称圣方济各)的家乡和主要活动地,圣弗朗西斯科1181年生于富商之家,少年任侠,后陷入人生意义的苦闷并通过朝圣和静修求得解脱,因救济穷病人和馈赠教会的行为与家庭发生冲突,1207年他在阿西西的广场上将衣物脱光掷还其父标志与俗世家庭决裂,自此开始宣教并自组兄弟会性质的宣扬福音游方教派方济会,宗旨是抛家散财、化缘苦修,成员们多为对现实生活绝望寄托天国幸福的狂热分子,会中组织严密的托钵僧侣们将该会影响迅速扩大向周边各国。弗朗西斯科自己则频频出现在教皇的宫殿和十字军的队伍里面,成为当时风云人物。1226年当其病逝时,方济会已经成为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教派之一。1228年教皇格列高利四世将弗朗西斯科封圣并为其在阿西西墓葬纪念教堂奠基,工程于1253年结束。该建筑整体由教堂和修道院两部分组成,其中的教堂又分为上下两部分,下层是罗曼式的,上层过渡到哥特式,属于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目录。我们此行的重头戏就是去圣弗朗西斯科修院教堂(Basilika San Francesco)考察其中的经典壁画。

该修院教堂里面珍藏着艺术史中被尊为西方近代绘画之祖的大画家乔托(Giotto)的作品。而此艺术珍宝也的确命运多舛,1997年9月26日,两次强烈地震令上堂的部分拱顶轰然坍塌,造成当时多名信众不幸罹难的同时,拱顶和墙壁上多达200平方米的精美壁画也于尘灰中毁于一旦。当全世界都在为此震惊并叹息这巨大损失时,意大利的艺术家和技术人员硬是收集了全部建筑残片,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先进的技术辅助,迅速将无数壁画细小碎片拼合复原,仅于两年后便令教堂恢复了华丽旧观。在此背景下,我们踏入教堂的时候,心情不仅是兴奋,更有难以描述的忐忑和感动。举目望去,那轻灵秀逸的哥特式十字拱顶不仅重新完好地飘悬在高空,而且建筑表面精美细腻的壁画也同样光彩焕发,完全看不出浩劫的痕迹。其华丽的色彩和繁复的笔触渗透到每一个细小的角落,让教堂的内墙好像是整个被花毯包裹了似的,美轮美奂。如此杰出的创作能够得到挽救重生,实乃全人类之福。
在上堂大厅的侧墙和窗拱中,便是乔托于约1266到1337年间完成的著名湿法壁画,其题材是圣弗朗西斯科的生平以及圣经故事。这系列绘画的叙事方式类似于连环画,顺次看来就是该圣人一生的行传,包括在广场上抛衣弃父以及后来经历过的种种奇迹,手法简洁,一目了然。该壁画色彩鲜艳,形象生动,虽然还明显带有拜占庭式的平面化和哥特式的拘谨谦卑等古拙特色,但是其中已经出现了极具革命性的绘画元素——透视表现和明暗阴影,这是该技法在古典时代之后的首次复苏,从而使得对人体和物象的表现走上了追求立体和写实的道路,并正式开启了文艺复兴绘画的门径。我们考察的方式是事先分配给各人不同的研究题目,每个学生要据此题目收集相关资料整理成演讲稿,然后在考察中面对实物向大家加以解说介绍。该计划眼下就碰到了点麻烦,因为管理该教堂的是当地持律极严的披黑袍、削顶发、腰系白麻绳的方济会修道士,他们面若寒霜在教堂中往来巡行,一旦发现有人高声喧哗或者举止不敬的,就会马上用强硬的嘘声加以警告镇压。我们被嘘了好几回之后,只好悻悻地跑到外面去讲解了,好不扫兴。
 ( 托斯卡纳拥有最安静、最原生态的生活
)
( 托斯卡纳拥有最安静、最原生态的生活
)
下堂的空间比较低矮,光线也阴暗得多,气氛令人压抑,尽管如此拱顶和墙壁上也绘满了时代略晚些的壁画,而其中也不乏名家作品。下堂中央的祭坛下有阶梯可通向地下圣弗朗西斯科的墓穴,圣者的埋灵处造型奇特,我们正好又碰到了当日的礼拜仪式,便好奇留下来一会儿。只见僧众们簇拥着面相庄严的红衣主教由外进来,随行的执事们左右摇动手中所提的锃亮铜香炉,不一会儿幽暗的下堂中就烟霭迷离,四下的景象也变得亦真亦幻。在后排远远地朦胧看到后堂的祭坛下。幢幢烛影中,主教和僧侣们按照尊卑次序排列整齐,这种次序通过他们不同的衣饰服色表现得异常鲜明。后排才轮到俗众,其中尤其虔诚的,都努力往前靠,有的干脆就面向祭坛垂首跪地不起。主教授法的时候,只见四周的信众们多数低眉合十,口中嚅嚅默诵,神态极为庄重,不禁暗自感叹本地宗教情结之浓重。过了一会儿唱诗班开始朗声颂歌,浑厚宽和的男音在这闭合空间里回旋交响,含着强大的力压迅速渗入听众的身心,其中亲和的暖意不知不觉之间使得心中的坚冰松动软化,信众们很多就随着曲谱高唱了起来,漫声来自四方八国,归于一己虔敬。
从教堂出来后,我们在旧城中漫步周游。刚刚离开了艺术的圣殿,如今体会到艺术的人间,这古城中路径本就迂曲勾连,形势复杂,更在当地人颇具匠心的经营下,成就为奇异的多维空间。这儿两条平行但有上下高差的街道之间有许多斜街加以沟通,但是这种斜街却并不以习惯的形式简单地将空间切割,而是往往在上方修建一个圆拱,拱上面再建房将两边建筑联结,而拱下面就变成了一条隧洞,曲径通幽间实现了空间的贯通;或者纤细的圆拱上面干脆就空空如也,好像一笔即兴的画眉,又好像是为小仙人建造的天桥,无论如何,空间在这里被再次干脆地分置并俏皮地粘接。这类魔术般的空间效果多重而丰富,行走其间就好像爱丽丝漫游仙境,在每一个街口都会有别开生面的空间方位维度的全新组合在挑战你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令你迷而忘返。
尘封的黄金年代
第二天行程前往“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伦萨。“Renaissance”这个词的原意是重生的意思,在形式上重生的是古典黄金时代的造型方法和审美情趣,在实质上重生的是人类的原初健旺生命力、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性的倚重。
第三天我们前往古城锡耶纳(Siena)。锡耶纳也是托斯卡纳一个强大城邦,和佛罗伦萨长期以来是一时瑜亮,不断争夺地区老大的交椅,不幸最终落败,1557年沦为藩属,尽管如此其经济文化仍自成系统独具特色的。锡耶纳也是一座山城,规模比阿西西要大得多。当我们在城边下车被身边日本旅游团所淹没时,抬头所见的只是山坡上层层叠叠的棕褐色古墙和平缓屋顶,唯有几座高塔突围而出,傲然地炫耀头角。沿着坡度陡峭的石板路进入城区,路边绵延不绝的高大古建筑有很多醒目的绿色百叶木窗对抗骄阳。街道狭窄的所在,抬头只见一线天空,这时候阿西西的跨街飞拱又出现了,规模却变本加厉,甚至达到上下重叠好几层,此间结构加固的作用应该是超过美学功能的吧。在古街道的迷宫里转来转去,那些高塔的塔尖就像在和我们捉迷藏一样,一会儿在楼间出现,一会儿在拐角探头,让人全然失去方位感,开始怀疑自己究竟能不能最终到达它们那边。
毕竟功夫不负有心人,正当腿软气喘即将失去信心的时候,主教堂巨大的台基跃然出现在眼前。在登上一连串台阶之后就来到了教堂侧面广场,该教堂始建于12世纪,14世纪完工,本来为了与佛罗伦萨主教堂争锋,曾有过大幅扩建的计划,但是好事多磨始终未能实现,按照该野心勃勃的规划,现存教堂只不过是计划中建筑的一个横堂部分,占计划总体面积的区区1/6。
进入教堂之前,教授领我们去到广场另一侧的国立博物馆参观画家杜乔(Duccio Buoninsegna)的大型专题展。杜乔和马丁尼(Simone Martini)是所谓锡耶纳画派的代表画家,他们的创作年代和乔托相近,作品却不属于文艺复兴的范畴,其风格沿袭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绘画传统,强调平面性和精神性,追求的是一种富于装饰性的神性表现。
从博物馆里出来,教授接到了萨利尼先生的电话,他说前不久主教堂下面挖掘出一个神秘的地下室,其中发现不少古老的壁画,轰动一时。虽然目前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但是他通过关系让我们可以去先睹为快。机不可失,我们调整了原来计划去到主教堂背面一处不起眼的偏门等待,一会儿有人来引我们进去,下了几道台阶经过一段甬道,便进入了一处约四五米高的昏暗宽阔空间,随处可见残破的墙壁、圆拱和圆柱,脚手架也比比皆是,显然清理发掘工作还没有结束。教授说,这是一座年代更早的主教堂的残迹,如今的主教堂就直接修建在其上面。墙面上还可以清晰地辨别出许多壁画的片段,个别部分保存甚至相当完好,不但可见鲜艳的蓝色背景,人物的红绿服饰,金色头光,所表现的圣经故事和人物都可以容易地识别。专家推测这些壁画作于1270年左右,因其典型的拜占庭特征,无怪乎有人大胆判断这就是杜乔的手笔。
从教堂出来,我们顺山坡而下,两侧建筑相当气派,高大的宫堡间杂橱窗新颖的商店,各色新鲜水果直接陈列在路边,对视觉和味觉都是严重的诱惑。石板路完全沉浸在建筑阴影下,透出一种幽幽的蓝色,其间人来人往,非常热闹。经过一个路口时,不经意向边上一瞥,唉呀,好大一个惊喜,便迈不开步子。眼前赫然出现一个极宽敞的广场,广场边上是雄伟的一派建筑,这就是城市的中心广场和公众宫了。这广场的形式很别致,表面呈圆弧状外高内低缓缓收拢,好像贝壳的内面一样。据考证此地在古罗马时代是沿山势而凿的一个露天剧场,上面是坐席下面是舞台,所以才有这样的空间形势。站在广场上,四周建筑将其完全围合封闭,还真有些运动场的感觉。地面用红白两色的地砖铺出巨大的放射形图案,更加强了圆弧形的印象效果。当年在此经常举行大型赛马,由于其不规则的外形,赛手在转弯时经常人仰马翻,如今为了纪念当年的盛况,每年城市都举行两次模拟赛马节大肆庆祝。坐落在广场底部的公众宫以前是统辖者的宫邸,其形式和佛罗伦萨的旧公爵府很有几分神似,尤其是那座102米的高挑望塔。建筑主体于1288年到1310年完成,呈品字形,顶上有雉堞,上部外墙都是红褐色砖,下部白色石灰石,上面排列清秀的哥特式尖拱窗,其立面和广场的形状相配合,有一个内凹的曲度。
百塔之城
第4天早餐不见教授,后来才发现他昨晚喝高了睡过了头,他勉强起身后,埋怨我们没有去叫他。这天前往小城圣吉米亚诺(San Gimignano),山路羊肠般迂曲,连从来不晕车的我都有些不适,忽然联想到意大利人热衷的赛车运动,也许就是在这样的路线上找到的灵感。
圣吉米亚诺是一座中世纪景观保存完整的古城,给人的感觉比阿西西森严,比锡耶纳朴实。其外围城墙和其上厚重的棱堡都完好,高大坚实的城门正上方有跨楼,上面的哥特式连拱下开掷物口,当敌人攻城的时候,守军就从中倾倒熔化的沥青和铅水,如今抬头看那几个黑洞洞的孔眼,还是令人有些不寒而栗。入城的幽深街道用平整石板铺就,城内大型建筑物一般用石材,民居则多选砖材。
街道迤逦上行,不一会儿经过另一重城门就登上一个中央有石雕喷泉的小广场,这就是城市中心了。教授酒已经醒了,即兴给我们上了一堂历史课,话说此城十二三世纪时虽只有数千居民,却分裂为许多敌对的族系社区,他们各自圈占水源,修建广场回廊作为活动中心,然后更在侧构筑高塔互相对峙监视。坚固的高塔又名族塔,其功能相当于戒备森严的小型堡垒,一旦族人遭到攻击就全体退入塔中坚守反击。各族间关系剑拔弩张,流血冲突乃家常便饭,这类占山为王彼此交恶的风气在中世纪意大利非常普遍,发生在维罗纳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也是以此为背景的。强烈的对抗过程中,城中陆续修建越来越多的族塔,为了争强好胜,各方都努力将自己的塔造得尽可能高大粗壮压倒他人,从而张扬宣示财富和威势,最后便造成了城内望塔林立,几近摩肩接踵的局面。圣吉米亚诺城中先后共有72座族塔,现存完好的15座,素有“百塔之城”之称,更名列于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目录。行走城中,感觉像是漫步于中世纪的芝加哥和浦东,穿街过巷的时候,无法不一再与这些拔地而起数十米高的傲然巨物迎面邂逅,仰望中遥想当年那些执拗的族人为此付出的巨大艰辛努力,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
中心小广场旁连通另一个广场,这里坐落着市政厅和圣玛利亚·阿苏塔主教堂(Collegiata di S. Maria Assunta),该堂建于12世纪,是一座外观朴素的罗曼式巴西利卡教堂,其内壁满是壁画,多是锡耶纳和佛罗伦萨的画家的作品,表现了从创世纪开始的新旧约故事,虽非出自名家手笔,但保存相当完好,色彩鲜明。在侧堂的圣菲娜小礼拜堂(cappella di Santa Fina)中有琪兰达约于1473至1475年创作的表现城市守护圣者圣菲娜生平的壁画。圣菲娜是一个命运悲惨的女孩,生于1238年,10岁时候患病全身瘫痪,但是她并不叫苦抱怨,只是终日祈祷并效仿耶稣受难的形式选择了一块橡木板做床榻苦修,不久她父母也双双去世,只有一位保姆来照料她,因为长时间在木板上僵卧,她的皮肉和木板粘连在一起,还经常被老鼠和虫子啃食。这样受了5年的非人痛苦之后,1253年3月7日圣人葛瑞格向她显圣将她从苦难中解脱,在姑娘死时,从已经和她的身体无法分离的木板上面忽然绽放出紫罗兰花朵。琪兰达约创作的这套壁画规模较小,只有三部分,一道墙上描绘了躺在木板上双手合十的圣菲娜,身旁是她的保姆和保姆的女儿,在室内半空中出现了圣葛瑞格的影像,圣人用祝福的手势给予姑娘最后的解脱。对面墙上画的是圣菲娜的葬礼,她的遗体被移到了教堂中,周围僧侣在为她祷告,这时候发生了三件奇迹,教堂的钟自动敲响,保姆的手疾忽然自愈,盲孩子也重见光明;天顶上画了四福音使徒。虽然这几幅画的结构相对简单,但是大师的功力在其中却没有丝毫含糊,人物造型和环境再现都达到了高度写实,空间感令人信服,色彩鲜明响亮。这组壁画归我讲解,这回能完整地讲下来,自我感觉很不错。圣菲娜的故事在今天的多数人眼中应该都会显得异常残忍,但是在中世纪的理解中,她纯净无辜的经历却体现了一种完美的忍耐顺从、卑微虔诚的人格,并为当时的宗教界和统治者共同宣扬推广,至于其中的用心则是不言而喻的了。
末日审判和圣体遗物
最后一天的考察先取道山城奥维延托(Orvieto),奥维延托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公元前古罗马势力兴起之前,这里就已经有埃特鲁斯坎人修建的城市了。说山城也是名副其实,其城址是一巨大的凝灰岩台地,三面都是刀削斧砍般的笔直峭壁,仅一面有坡路通入城中,乃易守难攻的天险。这里曾是教皇行辕,1527年当罗马遭掠时,教皇克莱门特七世(Clement Ⅶ)曾避难于此,他为城市留下了一件大礼,即如今的旅游胜地圣帕特里克井(St. Patrick Well)。为保证城市被围困时有充足水源,教皇下令在山岩上开凿了这口深达62米的水井,该井非常宽阔,在岩石井壁内更开凿出两道螺旋形的阶梯,在井壁上开一系列圆拱窗为阶梯取光,人们可以赶着毛驴一直走到井底取水。这在500年前是一件浩大的惊人工程,充分体现了人定胜天的精神。
我们乘车爬上蜿蜒陡斜的坡道来到城门前,进入城墙后,路面渐渐变得平缓,市内景观和圣吉米亚诺有几分仿佛,古建筑之间偶尔也能见到高大的族塔。三弯两转之后奥维延托的主教堂(Duomo di Orvieto)出现眼前。
礼拜堂里珍藏有两件镇堂之宝,即所谓的“圣体遗物”。话说1263年在波希纳(Bolsena)的圣克里斯蒂娜教堂中来了一位波希米亚的游方僧,当他参加授圣餐仪式时对基督血肉化身于圣餐饼中的理论发生了怀疑,忽然间他手中的圣餐饼渗出血来,浸湿了他的身披法衣,游方僧深为震惊,认为这是基督显灵教化开导于他,于是伏地忏悔。这奇迹传到了教皇耳中,他令人将浸血的圣餐饼和法衣两件宝物取来奥维延托,并且下令修建教堂加以保藏,这就是奥维延托主教堂的来历。在礼拜堂中我看到了这两件“圣体遗物”,都被保藏在纯金打造的圣体龛中,光彩夺目的圣体龛上面布满了精细雕刻和各种珍宝,而其中的遗物却影影绰绰看不真切。尽管如此,一会儿功夫就有好几个参观者来到宝物前,毕恭毕敬翻身拜倒,叩头祈福,一点也不含糊。
下一站前往大橄榄山修道院(Abbadia di Monte Oliveto Maggiore),途中我用心端详托斯卡纳的风景。像多数开发较早的地区一样,这里的植被较稀薄,高大茂密的原生树林很少,多数都是丛丛簇簇的次生林和灌木,草地也稀稀拉拉的,远没有阿尔卑斯的那么精神,色调是一种干巴巴的黄绿色;也像多数人类文明策源地一样,这里的农地开发得太过充分,地力消耗得相当严重,夏收后翻耕过的土地晒得干透了,大片大片的土地像荒漠一样的灰白。不过在视觉上却不显得荒凉,田地被稀疏的草地、小灌木和篱笆分隔成几何形的片断,似乎响应着某种音乐的节奏,而在丘顶和坡脊上更总有几株枝叶萧疏、造型奇特的树木,一下子就活跃了风景,有点睛的效果。教授见到此景,也不禁感叹当地人有天生的美学品鉴的本能。之外不断出现的造型各异的城堡、别墅和农庄更为这风景带来了历史厚重感,托斯卡纳风景之美中人文因素超越了自然成分,而纯自然中也大有一种苍凉空廓之美。■
(作者简介:宇文鸿吟,本名刘宏宇,原籍四川。1998年赴德国留学,就读于杜塞尔多夫大学及鲁尔波鸿大学,2005年毕业获艺术史硕士学位。著有《欧罗巴的天穹下——西方古建筑文化艺术之旅》) 托斯卡纳壁画建筑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