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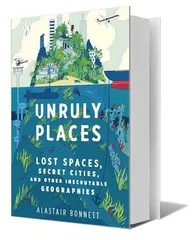 《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阿拉斯泰尔·博尼特
阿拉斯泰尔·博尼特
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中说:“有些人在出生的地方他们好像是过客;从孩提时代就非常熟悉的浓荫郁郁的小巷,同小伙伴游戏其中的人烟稠密的街衢,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旅途中的一个宿站。有时候一个人偶然到了一个地方,会神秘地感到这正是自己栖身之所,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家园。于是他就在这些从未寓目的景物里,从不相识的人群中定居下来,倒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从小就熟稔的一样。”而现在,用美国石溪大学哲学教授爱德华·凯西的话来说:“冷漠、千篇一律的场所在全球范围的侵蚀正在吞掉我们的自我感,使人们渴望地点的多元性。”
我们对不同寻常的地方的迷恋跟地理学一样古老。埃拉托斯特尼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在《地理学》中记述了他去过的许多著名城市和大河,斯特拉波在公元1世纪写给罗马帝国管理者的17卷《地理学》概述了许多城市和地方。他提到印度的一个金矿是“跟狐狸一样大、有着豹子一样的毛皮的蚂蚁”挖的。
博尼特说,过去几百年间,在世界各地,我们变得更擅长破坏而不是建造。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中,地点经常处于核心位置,是其他东西的基础和背景。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点应该优先于其他一切,因为地点赋予世界秩序,积极地、保护性地支持位于其上的东西。但宗教和启蒙运动时期的普遍主义者认为,地点很狭隘,跟他们宽广但抽象的全球一体的图景比起来,地点只是平淡的脚注。大部分现代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对地点没什么兴趣,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理论在哪里都适用。地点被降级,被空间这一概念取代了。空间听上去更现代,它让人联想到流动性、不受限制,它许诺了空荡荡的充满希望的风景,地点则是拥挤、怪异。
博尼特写道:“地点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的方面。我们是制造地点、热爱地点的物种。地点是我们的生命的布料,记忆和身份缝在上面。”但现在整个地球都处于精密的了解和监管下,这让人们渴望发现偏僻、秘密的或至少令人感到惊奇的地方。梅尔维尔在《白鲸》中说,有一个村子,“它不在任何地图上,真正的地方从来都不在地图上”。当世界完全被编码、整理之后,当矛盾和朦胧被擦掉后,我们知道了一切东西的位置和名称后,就会出现一种失落感,我们希望逃离,希望找到新奇的东西。没有命名的、被抛弃的地方就获得了浪漫的光环。
博尼特用47篇短文,介绍了47个地图上没有标明的地方,包括漂浮的岛屿、死城、隐蔽的王国。这些地方有的很平凡,如一个机场的停车场,纽卡斯尔一个交通岛,有的很壮观,如地下迷宫、太平洋垃圾带。在荷兰和比利时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镇子令两国领土交织在一起,你在哪个国家纳税取决于你家的大门在哪个国家的范围内。今年3月17日,谷歌从地图上擦掉了纽约的阿格罗镇,因为它根本不存在,是地图商1925年发明出来的,以便他们辨明自己的设计是否被盗版。
(文 / 小贝) 地理学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