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山地震与十年减灾路
作者:吴琪(文 / 吴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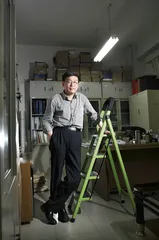 ( 史培军 )
( 史培军 )
两次地震灾害不可比
三联生活周刊:刚刚过去的芦山地震,很容易让公众联想到5年前的汶川大地震。从你作为灾害评估专家的角度,怎样看待这两次地震?
史培军:这次芦山地震后第五天,我们专家组一行16人,深入雅安芦山、宝兴、天全、荥经、雨城等4县1区、20多个乡镇受灾现场,对灾情进行综合评估,并对恢复重建提出决策参考。
芦山地震最大烈度为9度,面积208平方公里,等震线长轴呈北东—西南走向分布,芦山县有5个乡镇都在这个区域内。芦山县、宝兴县、雨城区、天全县、荥经县等21个县(市、区)受灾,都位于6度烈度区内。
我提到的“烈度”,与“震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震级是地震爆发出来的能量总和,我们将这种能量分为不同的等级;所谓烈度,是地震发生时,在波及范围内一定地点地面振动的强烈程度。烈度客观表明了各地结构受损的严重程度,它成为抗震救灾指挥部安置转移和恢复重建的重要依据。
 ( 四川省芦山县在地震中受损严重的房屋 )
( 四川省芦山县在地震中受损严重的房屋 )
总的说,这次的芦山地震和2008年的汶川地震灾害不可比,芦山地震震中烈度大约为9度,而汶川地震震中烈度为11度。汶川地震的遇难和失踪人口有8万多人,烈度为6度以上的灾区有50万平方公里。这次芦山地震遇难人数近200人,6级烈度以上地区不到5万平方公里。
三联生活周刊:芦山地震的重灾区受损情况怎样,高烈度地区不多,是不是房屋受损不是特别严重?
史培军:我们分别对地震烈度9度区、8度区和7度区的房屋受损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芦山县老城区北街和根雕一条街是其中两个抽样点。我们发现,大量房屋从街面的角度观察,外观基本没有受损。但走进屋内一看,很多房屋的填充墙出现了多处“X”形的剪切断裂,有的承重梁断裂、承重柱发生了位移。走到房屋背后,可以明显看到地基下沉。在地震烈度9度区,房屋结构普遍严重受损。其中,太平镇破坏最严重,一些房屋被震倒。
芦山地震造成的影响,具有沿着地震断裂带、呈带状分布的地震—地质灾害特点。在这个带状区域,无论是在显形地震带还是隐形地震带附近,房屋的破坏都很严重。
根据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芦山地震及其灾害的特点主要有6条,即:地震波及范围呈带状分布,致灾强度大;灾害造成的人员死亡少,房屋破坏大;山大沟深,群山起伏,救灾难度大;灾区地质条件复杂,潜在危险大;灾区经济社会欠发达,恢复重建投入大;生态系统价值显著,生态重建意义重大。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7级地震的伤亡人数比较少,是不是与汶川地震后,四川全面提高房屋设防能力有关?
史培军:芦山地震死亡人数较少,确实与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程有密切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地震的主震区,是上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在灾区现场发现,在汶川地震后恢复重建中修建的房屋,抗震设防标准明显提高,基本都从普通的5度提高到7度,起到了明显的抗震减灾作用。
我们在天全县大坪乡毛山村看到,大坪乡中心小学修建于汶川地震之后的2009年,由于位于断裂带上,学校的两栋教学楼都出现了承重梁钢筋弯曲、地基与整栋楼明显位移、楼体倾斜等现象,结构严重受损,但都没有倒塌,基本符合“大震不倒”的设防标准。在芦山地震灾区,很多房屋成为类似这样“站立的废墟”。只要房屋的框架不倒,生命就容易保住。
灾害评估的技术与非技术因素
三联生活周刊:专家组的核损工作重点是哪些?哪些数据会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史培军:我们对地震的地质情况、次生灾害、房屋受损情况、经济损失等会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受灾地区最在乎的是经济数据。我们作为核损专家,去到灾区后好像变成上帝,大家拉住我们的衣袖,让我们给他们的受灾情况评得严重一些。
比如这次芦山地震后,他们初期报上来的经济损失是2000多个亿,我们用模型快速评估为550亿~980亿元,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评估为10亿~100亿美元。你想想,汶川地震给四川、甘肃、云南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一共是8451.36亿元,其中四川省达7717.17亿元。芦山地震的能量只有汶川地震的1/33.3,它的经济损失不可能超过汶川的1/10吧?即使是单位面积的经济水平提高了,损失也不可能达到2000个亿的水平。
汶川地震后,当地报上来的经济损失是1.3万亿元的损失,我们专家组最初快速评估为8000亿~9000亿。当地一个官员半开玩笑半是无奈地说:“教授,你们到底有没有同情心啊?”实际上我们考虑到了科学和经济等多方面因素,才能核定最后的经济损失。烈度在9度以上的地区,85%的房屋不能再用了;烈度在8度以上的地区,通常房屋的倒损率为50%以上,芦山县1/3的房子要重建或加固。现在单位面积的经济损失比过去增加了,2008年汶川地震的重置费是按每平方米1000元来算的,现在是每平方米1000~2500元不等,主要是考虑到这几年建房的材料费、人工费的上涨。
三联生活周刊:当地官员信服你们评出的灾损状况吗?统计受灾情况是个复杂工程,其中的技术因素能精确到什么程度?
史培军:我们每到一个受灾乡镇核实情况,会让当地官员填写30多个表格,包含上百个指标。我们既通过走访去看房屋受损情况,也用遥感技术等判断受灾程度。这上百个评价指标非常繁杂,总结起来,表现了几个基本思路,其中最重要的指标——房子有没有倒?根据国际上灾损规律,地震损失中,房子倒塌造成的损失占到灾害损失的一半以上。
这次地震再次证实了,不同类型的房屋,在什么震级下容易倒塌,是有一定规律的。芦山地震中,砖混结构的房子受灾最重。完全木结构的房子,这次很少倒塌,木房子怕的是地基崩滑或被滚石压砸,适应地震的能力较强。砖木结构的房子在地震中受灾也不很严重,钢筋骨架的房子就更没问题了。
我们基本上是由一线野外考察得出数据和遥感数据,这些数据为中央的灾后重建决策提供了依据。
三联生活周刊:房屋受损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的损失最直接吧,农民们有了积蓄往往用来建房子。
史培军:四川乡镇的普遍情况是,农民没多少资金建房,一般是有了钱先把第一层建起来,等什么时候再筹到钱,才把第二层也建起来。
我这几年看到的是,灾区里真正过农村生活的人并不多。很多农民带着多年积蓄搬到了小镇上。他们盖了两层的房子,楼上住人,楼下就是经营场所,基本上是搞农家乐,或者开个小超市、小服装店。每层房子100平方米左右,一般家庭五六口人。
三联生活周刊:老百姓从山区搬到平地,是他们为了避开高风险地带而被迫离开,还是主动的选择?
史培军:我觉得主要不是安全意识起作用。地震等自然灾害毕竟是小概率事件,而且中国人的防灾意识还是比较薄弱的。实际上是机会意识让他们往城镇集中,山区对农民来说是没有前途的,但凡有点本事的家庭,都千方百计在城镇买地皮建房子。特别现在独生子女多,农村父母的钱一个用来投房子,一个就是用来投孩子。
房子几乎占到他们财产的90%,房子对他们而言不仅是住宿,更是谋生手段。灾后重建的资金,分到老百姓手里是比较少的,那些自己花了一二十万元建房的农民,补贴的钱肯定不够他们重新建房。所以我们在下边调查时,老乡总是跟我们说,不要把他们的房子“划圈圈打叉叉”,意即不要让他们推倒重建,他们希望房子加固后还能用。
三联生活周刊:汶川地震后,灾区获得的社会各界捐赠款物达到750多亿元,政府也投入了很大财力来帮助灾后重建。你提到老百姓重建房屋的补贴有限,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史培军:地震后,灾区获得了资金来提高设防,但是钱主要是补贴给学校、医院、办公等这些公共项目,以及公共设施等,老百姓个人拿到的补助比较少。而且,我们谈到的设防标准,只是城镇房屋的标准,农村房屋目前还没有设防标准,我们防灾减灾的法律法规也是严重滞后的。
中国房屋建造标准的现状是——“不设防的农村,设防水平低的城市”。我建议中国灾区的设防标准应该普遍由6度提高到7度,农村地区的房屋如果能强制规定建房标准达到6.5度,那么发生灾难时,多数生命是能够受到保护的。实际上,把一套设防水平低的房屋加固到6.5度,平均一户人家只用3万~5万元。在6.5度的基础上,只要加上圈梁和承重墙,就能达到7度结构不倒的抗震水平。农民自己资金有限,这些工作政府应该做在前面,不然灾难发生了,承担损失仍然是政府的事情,人的生命还保不住。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提过,发生过大灾的地区反而是安全的,短期内同一地区连续发生大灾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同样处在高危地带,近期没有发生大灾的地区是不是更需要提高房屋设防呢?可是如果灾难没有发生,舆论和公众都关注不到那里,他们反而缺乏提高设防的资金?
史培军:这确实是个悖论,灾区重建需要提高设防,那些处在高风险地带的其他地方也需要加强设防。可是我们目前都是随着新闻热点跑,灾后的关注很足,对于高风险地区灾前的防范,重视还不够。
举国应对灾难的强大与脆弱
三联生活周刊:刚才你提到,灾区的人往往希望把自己的灾情评得严重一些,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重建资金。灾难也确实给了四川灾区一次受到极大关注的机会,怎么理解这种灾难与重建的关系?
史培军:灾难是让人痛苦的,生命的失去、财产的损失,但是灾难又给当地经济换来了一次脱胎换骨的重生机会。这就是灾难和重建的辩证关系,或者说是除害和兴利的辩证关系。中国政府和科学界在大量的防灾实践中,建立起了综合防灾系统,对于中国的综合防灾减灾系统,国外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们发挥了举国体制的优势,短时期内动员不同部门,救灾效率非常高。
汶川地震时,都江堰的向峨乡受灾也非常严重,这几年我先后去过那里7次,了解灾后重建的情况。2009年我去的时候,看到向峨乡山沟沟里的人基本都搬出来了,政府在山下平地上给他们建起新房子,搞农家乐,房子漂亮极了。我问老乡们有什么感受,一个老太太说:“我们这个乡死了100多人,换来了我们乡50年的经济进步。”我把老太太的话翻译给随行的外国教授,他们听了非常惊诧,老太太虽然目不识丁,却一针见血指出了“世界共同的灾后重建规则”。
三联生活周刊:当地老百姓对这种灾难和重新获得发展机会的关系,普遍是什么感受呢?
史培军:这几年走访汶川灾区,我有两个鲜明感受:一是老百姓太豁达了,震后第一年我去调查,发现大家的生活状态非常好。四川人真是很乐观,我感觉他们好像不怎么需要心理学家去治疗。另一个感受是,经过灾难,人人都学会了兴利和除害的辩证关系。在这些高风险地带,兴利必先除害,通过减灾才能发展,必须学会与灾害风险共生存,经历过灾难的当地人对这个理解太透彻了。
中国几千年来的防灾哲学无非两条:一个是除害与兴利并举,一个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但是这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灾后行为。西方人的思路和我们正好相反,他们是把工作做在灾前,通过购买保险,事先集中多方资源应对一方有可能发生的灾难。我们是灾后调集各方力量支援灾区,这就是灾前哲学和灾后哲学的区别。
三联生活周刊:可是,如果我们的救助鼓励了“爱哭的孩子有糖吃”,那么受灾的地区不就拼命喊穷吗?
史培军:事实是这样的啊。当我们的救灾仍旧是举国体制时,能够体现出我国行政效率高的政治制度优越性,同时会导致“爱哭的孩子有糖吃”。“孩子们”拼命“哭”,来抓住这个多少年难遇的援助机会,灾区“等靠要”的思想很严重。这时候中央的态度就很关键了,我们这些科技专家的核损工作也很重要。
汶川地震后的灾区与灾民,普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始终觉得政府应该给予更多,灾区与灾民对国家的依赖心理太重了。灾区现在的新房子,特别是办公和学校及医疗设施等大多是政府给钱重建的。对于重建家园,应该在国家给予帮助的情况下,多发挥灾民自力更生的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我记得汶川地震后,我们对政府动员救灾能力的高效率感到十分自豪。经常拿来对比的例子是,美国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后,美国政府的救灾表现十分迟缓。
史培军:中国政府动员各方能力的高效率,确实举世罕见,这点值得我们自豪。但是我国应对灾害高效率的同时,当基本由政府来统筹支配时,减灾的效益是低下的。这就是举国体制的特点,我们还是按照计划经济的一套在减灾救灾,市场发挥的作用非常小。这次芦山地震,有的网友在讨论,政府有时候面对灾难是不是存在“响应过度”的问题?这些都是举国体制不足的地方。
根据统计,我国近年的受灾财产里边,投保比例不足3%,而西方发达国家达30%~45%。美国卡特里娜飓风,财产损失的45%左右都是由保险公司赔付的。当把这些交给市场后,政府的负担就小多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更有效率的。所以我们怎么把政府防灾减灾和市场、社会相结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可喜的是,我国农业保险的推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粮食主产区普遍推广了农业保险。一些沿海省份的农民房也上了台风保险,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在防灾方面开始发挥了作用。
“走”或“留”的应对灾害哲学
三联生活周刊:四川的这两次地震,会不会使得当地人的不安全感变得很强?人们应该怎样来减小受灾概率呢?
史培军:今天科学对地震的认识,还不足以指导我们的生产与防灾。对于灾区,能做的是:提高设防或者把人搬迁出来。这也是国际减灾的基本思路:高风险地区尽量躲开,但是也不可能都躲开,所以必须生活的地方要做好防灾。
国际上灾后重建的基本原则是就地重建,高风险地带应该尽量躲开,但是还得考虑现实情况。比如2010年舟曲泥石流,我也参与了灾后调查。那次灾难死亡2000多人,这些人基本居住在一条长长的泥石流沟上,属于高风险区。我们核算了一下,舟曲县城有4万~5万人,可是它们泥石流低风险地带的平地只能容纳下2万~3万人。所以,往泥石流低风险地带的西部平地迁移了1万多人,往甘肃中川平原地带迁移了1万多人,留下来的人也能够保证安全。
就地重建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指导思想。一是因为大灾过后,同一个地区再发生大灾的概率很小。世界上迄今为止,还没有在同一个地点完全重复两次6.5级以上的地震。另一方面,提高设防水平,这样就能与风险共生存。美国的旧金山及日本都做得很好。日本全国房屋的设防标准都在7级以上,城镇达到8级,大都市达到9级,所以2011年日本一场9级地震,死亡人数大大低于我们8级地震的死亡人数。灾难的核心是贫困。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提到灾区重建,往往看到的是农民住进了漂亮的新房,除了住宿条件外,他们真正的生活情况怎样?
史培军:这也是我们最关注的重建问题,无论汶川地震也好,芦山地震也好,我们形成了灾后救助的一种逻辑:大灾为当地经济创造了一次整体提升的机会,借此可以重新规划经济增长方式。但是我们是否提出了新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这是问题的关键。
比如这次受灾的宝兴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不到一个亿,他们如果向国外出租大熊猫,一对大熊猫一年的租金就有1000万美元。一年如果出租两对大熊猫,收入就超过县财政的收入了。我觉得他们就应该把生态资源的优势发挥出来,而不是当地人纷纷开垦山林、造小水电、小加工厂,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很严重。不然用有些老百姓的话来说,“居住是安全了,生活还很贫困”。那些山区一定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你前边提到,灾区不少的人口向小城镇集中,生产和生活一体化,你觉得这种方式是今后发展的方向吗?
史培军:我对这种状况其实很忧虑。我担心的是农民人口向城市集中过快。当农民农业生产时,是用产品向社会换取劳动报酬。当农民们大量挤入城镇搞第三产业,而服务业是不创造绝对价值的,当这么多人都搞“三产”,他们获取收益的机会是很低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发现,脱离了“一产”、“二产”的中国广大农村城镇化是值得警惕的。西方的很多小城镇是保留了生产传统,比如酿酒、家具生产、手工艺品、服装生产,而我们的小城镇都是门面房,有那么多服务业可以发展吗?
我跟四川不同地区的干部交谈,发现离成都比较近的城镇相对乐观,他们的农家乐能够持续发展,有些农民转化成企业工人,过得也还不错。离成都开车一小时以上的城镇,服务业发展就不太好了。比较特殊的是,这次地震后,我发现雅安山区里的一些少数民族不愿意下山,还是守着老家业,生产手工挂毯,效益不错。我对他们的选择是赞同的,他们还在生产,并且产品有独特性,这就保证了他们的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从更大的视野看,这些年中国的防灾减灾能力获得了怎样的增长?
史培军:我认为从2003年SARS事件开始,中国应对灾难的水平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是制度设计、经济规划、社会管理、文化完善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都渗透了综合防灾减灾的意识。政府的综合防灾减灾意识成了一条“线”,把各个行业和部门的零散“减灾珍珠”串了起来。
我在1988年博士毕业论文里就提出了“灾害系统”的概念,并与1991年发表了“灾害系统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论文,但是花了20多年才受到国际科学界的关注。到了2009年我们终于启动了基于灾害系统理论的“综合风险防范”的国际科学计划,由我和另一名德国科学家牵头。
过去防灾减灾是被看作不创造财富的,社会上认为你不重要,这种研究不被重视。可是一场巨灾的损失是非常大的。政府在执政理念上曾经单一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忽视了社会管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现在转变比较大。我们常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觉得应该从防灾减灾的角度再补充一句:科学技术也要保护生产力。现在全社会也越来越认识到,创造财富和保护财富同等重要,科技进步在保护生命、防灾减灾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地震雅安地震减灾十年三联生活周刊芦山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