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十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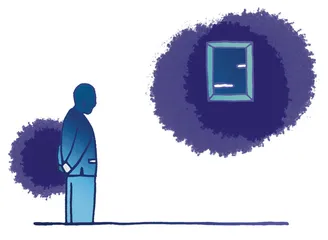
姥姥去世了。表姐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去往学校食堂二楼的楼梯口,说了几句就匆匆挂掉电话。同学问怎么了,我回答说我姥姥去世了。我的表情大概还没切换成悲痛模式,看到同学关切的眼神,才有点明白这就是生死永隔了。对于这个消息,我并没有多惊讶,相信家里的大人也多是如此。过年回家的时候,姥姥的老年痴呆已经相当严重,完全不认识我,也不怎么吃得下东西了。我买了我喜欢吃的曲奇饼干给姥姥和姥爷,姥爷吃得香甜,姥姥却尝了一口说是臭的,便扔在了炕上。
第二天,我买好了回家的车票。到姥姥家的时候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人,姥姥的灵堂就设在院子的一角。二舅妈看到我,把我拉到灵堂的一边说:“你哭哭你姥姥。”这里的“哭”是要秀给外人看的那种“哭”,我自然是哭不出来的。我只是坐到了守灵的妈妈旁边。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才得以掀开盖在姥姥身上的绸缎,看了看她,握了一下她冰凉的手。老家有规矩,一般不让孩子看死去的人。旁边的妈妈也问我“不怕吗?”我回答说“这是我姥姥啊!”是啊,她是我姥姥啊,我怎么会怕。
姥姥的墓地是早让仙家看好的,棺木也买的是第一等的木材,姥爷说不能亏待姥姥。姥爷年轻的时候做过“经济”(老家中介的一种称呼,帮人看棺木,做交易),所以他很懂这些事情。丧礼的整个布置他都是满意的,可还是不放心墓地,硬是趁着大家不防备,自己走到墓地去看了一遭。我们都在到处找他老人家的时候,他才慢悠悠地走回来,87岁的老头儿,步子还很稳健,说总算放心了。
姥姥入土的那一天,我在一旁安慰姥爷,其实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挽紧了姥爷的胳膊。倒是他反过来安慰我,“我和你姥姥也算是白头偕老了”,一边说一边用手帕擦拭眼泪。我眼睛也湿了。你很难想象我们那里的人表达感情的艰难,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和妈妈相互说过一句温柔体贴的话。可是姥爷的这句话,让我看到的是两位老人沉甸甸的感情。姥姥今年88岁,她19岁的时候嫁给姥爷,69年的相伴相随,就算打打骂骂,就算发生过很多的不愉快,一个人之于另一个人,也是刻入骨髓了。
整个丧礼分了三天,很多亲朋好友来吊唁,很多久未谋面的亲戚又聚到了一起。大家聊得热闹,只有在碰触到主人家至亲的眼神时才会耷拉下眼角,所以说红白喜事通常也承载着社交的功能。活着的人总是要继续活着,不会有人多怀念这个用一块绸缎盖着的性格不那么好的老人。就像她活着的时候,很多人也只是出于一种难以逃脱的责任去探望她,真正苦的只是姥爷。
在六个儿女中,姥姥生病后,妈妈是照顾姥姥最多的人。我回去的时候,妈妈嗓子完全哑掉了,几乎发不出声音来。她跟我说,姥姥老年痴呆后,她对姥姥说话总是很大声,姥姥耍小孩子脾气,妈妈忍不住就会呵斥她,现在很后悔。说着说着妈妈就又大哭起来,我也跟着哭了。我对妈妈说,只有最亲的人说话才会特别重,才会什么话都说。其实我心里想的是,以后再也不能对妈妈乱发脾气了。
几个舅舅和小姨也都疲倦得不得了。姥姥最后几个月的晚上变得很折腾人,姥爷不喜欢麻烦别人,就一个人扛着。过完年他老人家实在受不住了,开始让几个儿女轮番去陪床,经常整晚整晚地睡不了觉。守丧这三天,所有人又都没睡觉,在灵堂坐着稍不注意就能睡着。客人一来,又互相敲醒了,要伴着客人烧纸、磕头、哭丧一起哭。“娘啊!娘啊!”——那是一种很有节奏的哭声,就好像受过训练一般,可事实上他们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送走自己的亲娘。这种形式迂腐落后,现在没有多少地方还会磕头了。但可能是我老了,我开始觉得这些土里土气的仪式才最能承载人们的哀思,让活着的人日后想起来也了无遗憾。
最后的时候,妈妈和小姨为姥姥净脸净手,然后是我们这些孙辈将一些硬币和纸元宝扔到棺材里。在快要将棺材盖合上的时候,姥姥的一个孙媳从姥姥身下捡出一个硬币,她说她怀孕了,姥姥是个厉害人物,这样可以让小孩儿成为一个厉害人物。这是一个我不太懂的插曲,但是承办丧礼的人这样说了,或者自有他们的道理。我们一起把姥姥送到离墓地10米远的地方,孝子孝孙继续送行,女眷们则停了下来,又是规矩,女眷不能上前。我站在10米之外,给姥姥鞠了一躬。
这一天的太阳很大,还穿着冬衣的我们都出了一身的汗,人们又感慨姥姥命好赶上这么好的日子。我想的是,这或许是姥姥想留给我们的最后的记忆——温暖。 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