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与民的共谋
作者:维舟 加拿大汉学家宋怡明
加拿大汉学家宋怡明
对于帝制时代的中国,历来有两个截然相反的判断,一种强调它是“大政府”,政府无所不管;另一种却认定它是“小政府”,仅用相对而言很小的一批官僚就有效运作了一个庞大的帝国。所谓“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广为流传,似乎可以表明:生活在基层社区的普通人在现实中很少需要和国家打交道。
现在,加拿大汉学家宋怡明同时推翻了上述两种设想,呈现出一幅远为复杂深入的景象:一方面,即便是生活在边远地区的普通人,其实也都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应对无所不在的国家力量;另一方面,他们也并不只有服从或反抗两种选择,恰恰相反,他们可以利用正式制度中的种种矛盾和缝隙,将之转化为自己生活中的有利因素,而这正意味着国家无法不折不扣地贯彻自己的意图。明代出现的“阳奉阴违”一词,传神地体现出这种双向博弈。
这种特殊的制度史在意的并非文献上记载的成文法条,而是“普通人在不完善的制度下怎样生活”。在此他选取的是明朝的特定群体:军户,也就是按规定必须世代服兵役的那些家庭。以往的研究大多注意到,军户制度越到后来越难以为继,因为随着军户人口增长、社会变化,后世未必愿意当兵,也不见得适合当兵,到后来兵源素质下降、逃兵屡禁不止,又或出钱找人替补,引发层出不穷的问题。无疑,这也常被视为一项不得人心的政策,但这本《被统治的艺术》却通过对家谱等地方文献的视角揭开了另一面:这些老百姓在苦于应对正式制度的同时,也在“紧紧抓住国家提供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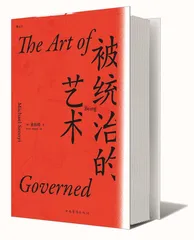 《被统治的艺术》
《被统治的艺术》
因此,“被统治的艺术”乍看谈的是一种被动的状态,其实却着眼于他们的主动性。在这样的庶民政治的视角下,普通人也是历史事件的主体,他们不仅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历史,也的确通过深思熟虑的利弊权衡,评估着各种不同选择的代价,尽力在狭小的范围内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确,国家特定的义务必须履行,但他们还是可以有条件、有选择地履行。这里的办法有好多种:首先是“集中”,即由一人承担起整个家族的服役重任,这个人甚至可以是雇来代役的;其次是“轮替”,也就是家族内部轮流出人来承担。
不难看出,在这些百姓眼里,服役与其说是一项光荣的使命、一份职业,不如说是一项无偿的义务。鲍大可在《中国西部四十年》中曾说,1949年前藏区很多人把政府开办学校、强制义务教育也看作跟征兵一样的徭役,因而出现了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有钱人家的父母出钱雇农奴子女代替自己的孩子去上学。
但明代百姓并不只是被动地应付,他们很快发现,军户身份也自有其好处:正因为军户已经承担兵役,因而就免除了像民户那样“交皇粮”的义务,否则就构成双重赋税了,因而整个家族只要有人去服兵役,就别无负担,也因此不愿脱离军户,这种徭役豁免权到后来甚至越来越有利;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利用军户的好处,比其他人更容易接触到航海技术和船只,甚至在非法贸易中获利,特别是负责控制、取缔非法海上贸易的人就是他们自己人,而这恰恰是因为他们靠近国家机关。
值得补充的是,于此也可见军户并非整个治理结构中最弱势的群体,那么真正的普通百姓(民户)、贱民又如何学会“被统治的艺术”?那些军户雇人代役,从他们的视角来说固然是应付官府的一种对策,但问题是那些被雇来替役者也有自己的算盘,为何不能用军户对付国家的那一套来对付军户自己?不仅如此,军户在应对差役时,几乎总是以一个有凝聚力的利益共同体的面貌出现,这本身强化了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然而这就意味着内部的公平伦理非常重要,否则势必有损于团结,但这样一来,个体在家族内部又如何自利?
对当时的每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多层级反复博弈。也正是由于体制规则与现实处境之间有着种种差距或矛盾出入,这些百姓得以利用这些差异来谋利,即所谓“制度套利”。这种“钻空子”的民间智慧,在中国社会极为普遍,如果说西方的“理性人”是在市场秩序下养成的,那么中国人则是在政治环境下培养出来的。然而一个问题是:这样看起来,这套制度的运作似乎是漏洞百出的,那么为什么它还能一直维持着?这就需要我们转换视角,来看看“统治的艺术”了。
简单地说,明太祖朱元璋在设计这一套制度时,考虑的重点并不是它的效率,而是如何低成本地维持社会运作。从本质上说,这一秩序设想其实是一个儒家政治的乌托邦,假定乡民们自给自足、由宗族即可解决纠纷,而无需朝廷多加干预,兵力也由专门的军户抽调,军队屯田后甚至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因而才能夸口“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这看起来非常美好,但它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便是后世难免会出现种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而这恰恰是因为社会往前发展了,此时“祖宗之法”的紧身衣却使人难以动态地调整适应。
其结果是很吊诡的:这套制度设计的初衷本来是为了节省开支、减轻百姓的负担,但最终运作下来却产生了非意图后果,不仅可能最终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且反倒弱化了组织效率,无法应对后来的重大危机。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官府不想着去堵住漏洞,是不能还是不愿?
这里的原因很复杂,总的来说,明代普通百姓并不谋求推翻制度,而只是尽可能地适应它、利用它,而官府也知道,如果想要低成本地维持系统的运作,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一丝不苟地执行且不说会激化矛盾,付出更高代价,甚至培养、维持一支专业高效的执行者队伍本身就很花钱。这种“统治的艺术”与福柯所说的很不一样,倒不如说是一种共谋:老百姓在利用官府,但官府其实也在利用百姓,并且大获成功,因为它几乎没付出什么代价,就使人们乐于使用国家的语言,接受了制度安排。
中国人缺乏规则意识,但也意味着人们相信任何规则总有余地。应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了普通人面对权力重压时的选择,可以理性地权衡如何与之良性互动,但也使中国人把聪明才智都用在如何钻空子上,并且还缺乏规则意识和对法律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封闭系统下长期生活、进化出一种制度人格,使得中国人极其善于灵活变通,乃至利用规则的漏洞,却相应地缺乏创造新规则、改变规则的批判精神和尊重规则的契约精神。这正是遗留至今的双重遗产。 军户宋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