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科长搅动电影江湖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文/郝建
文/郝建
1993年到1997年贾樟柯在电影学院文学系读书,他们那个班是理论专业,可他的志向在创作。他跟王宏伟、程青松、顾峥和录音系的凌小玲几个同学折腾了一个青年电影小组。1995年,他拍摄了《小山回家》,主演就是王宏伟。其中的一些方法他到今天的《江湖儿女》还在变化使用。比如纪实风格中忽然出个字幕,比如对暴力的指涉。
熟悉的人有时会把他作做贾导、小贾,他在影迷中的江湖大名叫“贾科长”。这个名字典出他自己的文集《贾想》。有一回,贾樟柯去一个隐秘地方买盗版DVD碟片,贾樟柯形容,那地方像老电影里的地下交通站。挑完买好快出门时,老板一把拉住他悄悄说:贾科长拍的《小武》明天就到货。后来,“贾科长”就成为他在电影江湖中响亮上口的亲昵尊称。
阅读《贾想》,看出贾科长的文学功底相当不错。 喜欢那篇《有酒方能意识流》,那文字让我想起他们一帮同学少年在电影学院后面的饭馆和黄亭子51号酒吧读诗吵电影、把酒放歌的青春豪情。2002年我跟谢飞老师一起去台北参加国际学生电影金狮奖颁奖典礼,一聊起贾樟柯,谢飞老师脱口而出:“他是个天才啊!”
1999年6月的《黄河》杂志上有个我跟贾樟柯做的访谈,他说自己是一个“电影民工”。这个学子自道大概反映了贾科长的底层视角和在地下艰难潜行、不时受阻的困难窘迫。到今天,贾樟柯已经得到两只手抱不住的国际A级电影节奖项。2015年,法国戛纳电影节的导演双周单元上,法国导演协会评选的金马车奖颁给了贾樟柯。有个电影圈朋友听了法国导演协会把这个奖给了贾樟柯,就跟我表示羡慕惊讶:这是个终身成就奖呀!戛纳电影节对贾樟柯的喜爱非同一般。何止戛纳,去年贾科长做平遥电影节,他把威尼斯电影节以前的主席马克·穆勒给挖来当了艺术总监。
从汾阳到北京黄亭子的电影学院学生楼,从地下电影走到今天的院线热映、明星荟萃,贾樟柯搅动了世界电影的江湖。
除了读书,贾樟柯的电影营养有两个源头:盗版碟和录像厅。
今天多数中国导演的电影资源,主要靠盗版碟。侯孝贤的静观式镜头语言,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人道主义、社会质感,给贾樟柯、王小帅、娄烨、路学长这一拨青年导演极大艺术营养。
贾樟柯的《小武》、路学长的《卡拉是条狗》在故事题材、镜头语言、对待底层小人物的态度上,与《温别尔托·D》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作品和法国布列松的《扒手》有着明显的“对话关系”。王小帅的《17岁的单车》与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不仅在片名上有近似,更重要的是在表现都市底层小人物的窘态和困境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贾樟柯的《站台》让我想起费里尼的《道路》。《小武》《三峡好人》里舒缓的长镜头、中景固定镜头很容易让人想起侯孝贤和小津安二郎。而他对都市边缘人的观察和富有同情的展现、对社会中某些逼人现实的忠实态度完全符合库尔贝以来的经典现实主义的传统。贾樟柯在《黄河》杂志上的那次对谈中曾经说,他最喜欢和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三部影片是《偷自行车的人》《扒手》和费里尼的《道路》。
但贾科长不仅学习了这些大师的语言,还改写了一些词汇表和语法规则。贾樟柯的电影具有现实主义风格,但那是经过他自己用力处理过、打造过的。贾樟柯总是在学习来的电影方法上刻写自己的贾氏签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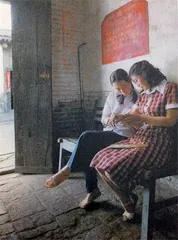 影响他们这代人的另一个电影资源和大众文化源流是录像厅的港台电影。邓丽君的甜美嗓音让高校学子和小镇青年齐刷刷“如听仙乐耳暂明”,周润发、邓丽君、叶倩文这些大众文化英雄构成了那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从录像厅、盗版碟得到的香港地区和美国电影,其中给贾樟柯更重要的影响的是强盗片、警匪片这些类型片。
影响他们这代人的另一个电影资源和大众文化源流是录像厅的港台电影。邓丽君的甜美嗓音让高校学子和小镇青年齐刷刷“如听仙乐耳暂明”,周润发、邓丽君、叶倩文这些大众文化英雄构成了那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从录像厅、盗版碟得到的香港地区和美国电影,其中给贾樟柯更重要的影响的是强盗片、警匪片这些类型片。
他回忆过80年代录像厅文化中香港电影的影响:“香港电影文化里江湖是有延续性的,忠义的文化,江湖的礼仪。通过录像厅时代去了解被割断的文化,去了解礼仪道义。香港流行文化对衔接传统和流行文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贡献。”
他的电影里爱用港台流行歌曲,他用这些流行歌曲来做时代更替的书签,也作为人物心绪的感性外化。《小武》中,歌女梅梅生病了,无业游民小武买了药去看她,俩人坐在床上聊天,梅梅给小武唱了一首王菲的《天空》。两个小人物惺惺相惜的温情突然打动我。《站台》的开头,我们听到红色歌曲《火车向着韶山跑》的铿锵音调,后面就踩上了林子祥、叶倩文《选择》的跳跃节奏。在《小武》里,叶倩文唱的《浅醉一生》,那是她自己跟周润发、李修贤联袂出演的警匪片《喋血双雄》的主题曲。
到了眼下的《江湖儿女》,贾樟柯又让这首歌再现江湖。低吟浅唱、放声高歌,唱出对时代浪潮的感慨,唱出对人物情感涟漪的一声叹息。
电影媒体Tweet My Films说,《江湖儿女》是贾樟柯的最新史诗,是他以往电影长期积累和愁绪的混搭。
看《站台》时,许多人站在北京西四环附近那个露天的汽车影院。片子三个多小时,大家一边看一边喝啤酒吃羊肉串。崔明亮、尹瑞娟的生活境遇写得有质感。当时心想,贾樟柯拍片子怎么如此放松。咬一块羊肉,跟文学系的张献民老师议论,70年代人,有了自己的影像语言,拍出了自己的史诗。
讲影像,是觉得贾樟柯的片子有了人物的质感、空间的忠实;讲史诗是他们在书写大大有别于官方叙事的历史,写了自己的记忆。《站台》在时间上完整跨越新时期十年(1979~1989),片子里的社会氛围、现实关系、人的状态很准确,情感状态很个体。有些主流媒体的专题片和纪录片,也能做到影像的那种忠实质感,但是再看其中的社会关系、人的处境就不大像。《小武》结尾处,小武蹲在地上、手被铐在一根钢丝拉线上,他就像个被人观赏的动物一样无力、木然。导演把自己对小武的切肤痛感传达给了观众,这其中有作者的情感和价值判断在里头。贾樟柯对小山和小武,对《世界》中被砸死的三明也有着这种人道主义的情感。作者对他们的苦难有着某种敏感,有着感同身受的自我投射。在贾樟柯的许多作品里,影像和音乐时时发散出阵阵悲凉向我们袭来,这些人物形象与社会画面让我们沉思,让我们体验荒诞。
由于贾樟柯的影像的确有质感、有一种忠实呈现的形态,许多研究者都爱用“现实主义”“纪实风格”和“客观”之类的词来总结他,认为他的影像就是“还原”人物和环境。
贾科长哪里会那么老实。从《小山回家》开始,他就善于“破格”。他的确具有直面社会的敏锐眼光和勇气,但在电影的叙事和语言上,他一直善于突出地营造自己的风格。从《小山回家》开始,他就在纪实风格的影像里加进了自己的强烈笔触。他用长长的镜头就那样拍摄小山在街上走是一种很风格化的营造。在平实的镜头中,他忽然插进字幕来表现人物心里的念头。每回看到那里我都要笑出声来,小山跟人打架时忽然出现一幅字幕,就一个字:刀。再看看《世界》中的动画、《三峡好人》中飞掉的建筑,《江湖儿女》中赵涛在星空下看到飞碟,我们看到贾樟柯时时处处在给自己的镜头语言开出一些气口,留些破绽。在《三峡好人》结尾,他让女主人公和前来找自己的丈夫就那么在大白天的水库边跳起舞来。不仅如此,他还在那个镜头的景深处安排了几个人在水库的一个什么建筑上跳舞。
贾樟柯的电影不是纪实风格,而是一种“风格化纪实”(stylistic realism或者bardian realism)。在贾樟柯手上,纪实不是一种单一、纯粹、带有尊崇膜拜态度去使用的创作方法,而是一种构成某种风格差异的要素,成为一种营造陌生化的电影肌理。在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和蔡明亮《黑眼睛》这类影片中,其镜头语言的肌理(texture)成为一种彰显电影语言个性的艺术风格选择。这是一种话语策略,实现了凸显个人风格的功能。飞碟、超越时空的意象化笔触,这些给作品造成了一种间离感,打破了文体上的单纯或者自我肯定、自我封闭。
贾樟柯作品中,《小武》和《江湖儿女》是叙事性处理得比较好的。按照好莱坞的叙事章法,《小武》是一个很有张力的故事。一个坚持在偷窃行磨练的“手艺人”这两天遇到事了:小武对以前的同行有过诺言,要在他结婚的时候送他“一斤钱”。这个同行洗手以后做生意发财了,要结婚了,但是没通知他。小武有能力弄到钱送他吗?小武弄到了钱,这位现在有身份的前同行会接受这“一斤钱”吗?不知道贾樟柯是否总结过《小武》的叙事处理对于这部看上去很写实的作品成功起到什么作用。我们看到他后来拍摄的几部作品《站台》《世界》等叙事性都不是很强。
从目前读到的故事梗概看,贾樟柯在《江湖儿女》中不仅设计了更具有情感烈度的故事,还自觉地考虑到类型元素的使用。如果要进一步创作票房更成功的作品,叙事性和类型化是贾樟柯必须更加奋力腾越的艺术门槛。
管虎的《老炮儿》上映前后,我把边作君先生接到京郊宋庄的栗宪庭老师家去吃饭。边先生现在是北京首席“老炮儿”。“文革”中,他是平民混混,被称为顽主、“外场人”、江湖上人。在香港,这类人年轻时叫古惑仔,成年了就叫帮会分子,他们的故事拍成电影就是强盗片。据说戛纳首映后有媒体把《江湖儿女》称为中国版的《美国往事》。他们大约是悟到了《江湖儿女》里的那种韵味,回首当年、往事如烟,看不尽许多惆怅、许多感叹悲凉。这跟著名的强盗片新经典《美国往事》异曲同工。美国《综艺》杂志的亚洲电影首席评论家Maggie Lee也把《江湖儿女》与强盗片传统联系起来看。她认为此片是“贾樟柯在《天注定》之后对强盗片类型最认真的探索”(Jia Zhangke’s most serious foray into the gangster genre since “A Touch of Sin”),“表达了他眼中对中国人精神轨迹的看法”(represents his vision of his country’s spiritual trajectory)。
《江湖儿女》有一幅剧照,赵涛饰演的巧巧高举手枪朝天鸣放,霸气十足,让人想起了李丽珍和莫文蔚演的女版强盗片里的古惑仔女孩。这幅剧照在宣传中一直得到强调,因为它非常符合这部作品的内涵意蕴和类型特征。贾樟柯写的是那种淡淡的人生况味,时代巨变带来的人情冷暖,从故事情节和一些剧照看,贾樟柯有意识地与香港地区和美国强盗片做了些对话。他说:“拍摄上借鉴了一些类型电影,江湖片的一些类型方法,但我并不希望它走得太远,它只是很有效率地建立起了这种江湖的氛围。”
但从故事看,《江湖儿女》没有传统强盗片里那份浪漫气息,没有杜琪峰《枪火》里那种对义气、兄弟情的坚守和慷慨赴死的那份惆怅和豪情。也许是在无意识地抚摸自己的青春记忆,贾樟柯在其中用了些许强盗片的元素,他紧紧抓牢的还是中国大地上那些底层人群的情感和命运。从《小武》开始,他对这些飘荡在中国时代变迁中的生命有兴趣、有敏锐感觉。通过雕刻小武、斌斌、巧巧们的群像,贾科长描绘出中国社会的情感状态和社会的无意识情绪波动。
一个好的艺术家就有这个本事,他能直觉地把握到社会大众的无意识。从打架时急于寻找刀子的小山,到《江湖儿女》中举枪救男友性命的巧巧,贾樟柯的作品不时用暴力美学来直面惨淡的现实。他的作品中有飞舞的血色,但这种处理灌注了作者的忧心和一些柔软情怀,它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暴力美学。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站台世界三峡好人中国电影小山回家江湖儿女小武电影剧情片爱情电影电影节贾樟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