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海不一定吃海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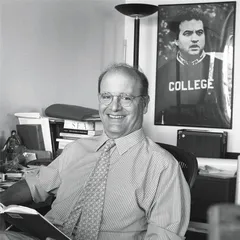 文/维舟
文/维舟
海运的优势
并不是所有靠海的国家都是海洋国家——历史上的中国就不是,甚至连日本这样四面环海的岛国,在明治维新之前也很难说是。因为这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海洋:它是社会生活的终点,还是起点?根据前一种想法,海洋是陆地的尽头,所谓“天涯海角”,当你从陆地走向海洋,就在海岸边停下了脚步;但后一种观念则相反,有一种冲动驱使着人们到海上去,到对岸的世界去,去和不同的陌生人打交道,这样,茫茫水面不再是障碍,而成了通道。
如果说有某种海洋文明的共同特质,那它想必是由此而来的那种流动性:人口的流动、物资的流动、财富的流动,以及知识的流动。虽然有所谓“靠海吃海”的说法,但如果仅把海洋作为一个蕴藏物产的宝库,所能得到的终究有限,更不必说在较早的年代,人类也没有技术能力开发海洋。这些都意味着,海洋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海洋本身,而在于它天然是不同群体进行交换的最佳媒介:在蒸汽机车出现之前,海船不仅比陆上交通工具移动速度快得多,而且运费低廉——13世纪末运送同样的货物从北欧到南欧,海运成本仅是陆运的1/20。仅此一端,就可以理解为何在欧洲人发现绕过好望角通往东方的海洋商路之后,曾经辉煌一两千年之久的陆上丝绸之路会一落千丈了。
不仅如此,海外贸易的最大好处是可以逃避陆上运输时所遇到的重重关卡课税。众所周知,15世纪末葡萄牙人之所以要竭力寻求直达东方的航路,最主要的内在驱动力就是想避开意大利城邦、土耳其和埃及等国因为垄断东方货物而施加的重税。在达伽马发现直达印度的航线之后,葡萄牙人将货物运回欧洲所需缴纳的通行税便只相当于之前的1/80。某种程度上,这就像是那个年代的“电子商务”:绕过了许多批发零售商等中间环节,将生产方与消费者直接联系起来,从而在压低成本的同时,将中间的利润揽为己有。就此而言,它天然具有某些市场的特质,正如德国学者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所说的:“海洋一如货币是一个中介者,它是交换手段的地理版本。”
从一种现代人的后见之明来看,既然海洋有着如此明显的好处,似乎很难理解我们的祖先为何不去好好利用它。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闽粤航海小传统,并在明清时期焕发出不同寻常的活力,但总体而言,传统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安土重迁的农业帝国,没有足够的动力出海闯荡,还屡次实施海禁。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比较好理解:海运虽然在运费上比陆运和河运省得多,但它却也是一种高风险、高技术要求的运输方式。海船不仅造价高,而且对技术、操控人员的要求都较高,在足够抗风险的现代巨轮问世之前,海洋显然也难驾驭得多,一旦沉船,很多商人也许就此血本无归。正因此,在上古的两河文明时代,能进行海上贸易的都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神庙或宫廷这样资本充足、能承受风险的机构。从这一意义上说,古代中国的决策者并不是缺资金或技术,而是权衡利弊,选择了“安全”而牺牲了效率与利润。
事实上,对真正有决心越洋航行的人们来说,技术从来不是真正的障碍。现代学者公认人类早期历史上最杰出的航海者是太平洋岛民,他们早在35000年前就驾驶着独木舟穿越了数千公里宽的洋面,由此人类定居者才逐渐扩散到了这些小岛上。挪威学者索尔·海雅达尔曾在1947年和五位同伴做了一件至今仍有争议的事:他们完全按照印第安人的传统方式制造了一个木筏,并靠着它在三个月内横渡了6000公里的太平洋洋面。在日本冲绳海洋博公园的海洋文化馆里,我曾看到许多太平洋岛民的航海器具,从船体设计、对风向与海水的观测、用以导航的天体图,都令人惊叹地证明:即使是一个无文字的人类社会,也完全能进行长距离的海上航行,因为他们以海为生。
 真正的“靠海吃海”
真正的“靠海吃海”
不过,正如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其名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所说的,这些岛民虽然是优秀的水手,到远方的岛屿和人交易物品对他们也极为平常,但他们的动机却不是为了获取利益,而“在于它们背后的传统和风俗所赋予的社会力量,它给这些物品以特别的价值,使它们笼罩着浪漫的光环”。就像林肯·佩恩在《海洋与文明》中所说的,要解释像美洲这样的地方为何没有出现广泛的航海活动、为何远距离海上交通网络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这些问题都是难以回答的”。自然条件往往不是问题(在非洲也许是,非洲海岸缺乏良港、封闭半封闭的内海和岛链),而从中国、日本到印度、埃及的例子又证明,造船资源、技术能力和贸易资源也不是促使人们走向海洋的先决条件。在此,本书虽然描述了全球各地海洋史的方方面面,但他的用意显然不是写一本历史哲学,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为何是欧洲人通过海洋塑造了全球化网络?
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地中海的确具有全世界最优越的先天条件:不仅优良港湾、岛屿众多,而且距离埃及、两河、希腊等文明中心都很近,由此带来强烈、直接而频繁的海上交换活动和冲突。欧洲的文明曙光最早出现在克里特岛这样乍看上去偏远的海岛上,实非偶然——考虑到海路联系,那它可说是当时欧洲地理位置最佳的地方,足可成为充当一个繁忙的海洋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它的财富和力量依靠海洋商路的交换,而海洋在带给它所有这些的同时,还确保了它的安全:即便到近代,远渡重洋投放兵力也很困难,因而这个欧洲最早的文明是一个不设防的城邦。随后诞生的雅典帝国更明确了自己的未来在海上,并首度确立了一种新的模式,帝国“通过没有中间商的远距离海上贸易获得财富,并凭借海军来保障其优势”,而这无疑就是欧洲近代“海商复合体”(naval-commercial complex)的前身,那是海上贸易和海权力量彼此支撑的一种社会结构。
这才是真正的“靠海吃海”:不仅仅是作为渔民收获一些海产品、混口饭吃那么简单,还意味着整个社会必须围绕着海上活动进行彻底重组。在荷兰和英国兴起之前,近代历史上最成功的海洋帝国威尼斯正是如此。在扫平了海盗之后,自公元1000年起,威尼斯每年都要郑重举行仪式,将由主教祝圣的金指环投入大海,宣告这个城邦与大海结婚,以此确立一种彼此紧密结合的排他性关系。相比起来,中国历代虽然也有海上贸易,但那最多也不过是极少一部分沿海地带人们的生活罢了,就算全部禁掉,对帝国整体而言也只是可承受的损失。即便是近代以前绝无仅有“背海立国”的南宋,也只是利用沿海地区的财富来支撑整个国家,而不是围绕着海洋活动来改造整个社会。最明显的对比是:1378年当威尼斯被热那亚舰队封锁海口时,整个城邦几乎立刻陷入危亡,但当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封锁中国沿海时,绝大部分自给自足的中国人根本没感觉到对自己生活有什么影响。
欧洲的海洋文明形态之所以最终能胜出,恐怕正在于它奠基于一种英国学者伊斯特凡·洪特所说的“倒序”发生的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从长距离贸易开始,随后逐渐发展出国内贸易,最后才在很晚的时候创建了生产农业,其顺序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方恰好相反。显然,这一不同寻常的模式,其谜底就是“海洋”二字。长距离的海上活动使得整个社会围绕着它自发重组结构,而以利润作为驱动力和润滑剂,推动着人们不断向外开拓,前往遥远而陌生的陆地,由此建立起与不同国家和人群之间的联系。的确,这种模式天生带有某种向外扩张的冲动,也众所周知给世界带来了好坏参半的影响,可问题在于,如果不是这样,历史也没有提供另一种更好的方式,能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海上交换活动提供持久不竭的动力。 海洋林肯·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