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如厕
作者:薛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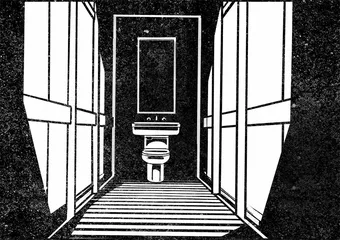 《西游记》中,孙悟空虽然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却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浦江清教授说,这个故事是在显示佛法无边,给自高自大的人一个教训,以及暗示人类还不能征服自然。孙悟空以为他已经跳出了如来佛的掌心,看到五根肉红色撑天柱时,他以为自己已经到了天尽头。到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他也只能写个“到此一游”,以及在柱子下撒一泡猴尿。如来气得骂他是“尿精猴子”——只会尿尿的猴精,可见佛祖也很介意猴尿的臊气。猴王尿在佛祖手上好像有点过分,可是如果佛无处不在,尿在哪儿都是尿在佛身上。
《西游记》中,孙悟空虽然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却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浦江清教授说,这个故事是在显示佛法无边,给自高自大的人一个教训,以及暗示人类还不能征服自然。孙悟空以为他已经跳出了如来佛的掌心,看到五根肉红色撑天柱时,他以为自己已经到了天尽头。到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他也只能写个“到此一游”,以及在柱子下撒一泡猴尿。如来气得骂他是“尿精猴子”——只会尿尿的猴精,可见佛祖也很介意猴尿的臊气。猴王尿在佛祖手上好像有点过分,可是如果佛无处不在,尿在哪儿都是尿在佛身上。研究中世纪文学的教授艾伯特·弗里德曼在《盗贼的如厕礼仪》一书中说,窃贼入室临走留下一泡屎尿,这一做法很可能是一个古老的习俗。现在窃贼应该不会这么干了,等于留下自己的DNA。不过人类已经征服了尿臊气,就是把它们冲进下水道。人的一生中大约有3年时间在厕所中度过,建筑师科比西埃认为,厕所是“现代工业技术最美丽的发明之一”。在管道和冲水式厕所出现之前,全世界人要解决如厕问题,要么走到室外找个方便之处,要么找个容器,如马桶、便盆、便盂等。英国记者罗丝·乔治在《厕所决定健康》一书中说,英国人通常是先用法语大喊一声“水来了”,然后把夜壶里的东西倾倒至街上,最后这句法语被缩减为“loo”,厕所的英文词之一。法国人也不示弱,把拉屎的地方称为“英国的地方”,接着又使用英语Water Closet首字母的缩写W.C.表示厕所。
6月23日,《纽约时报》书评人德怀特·加纳写了一篇文章,盘点了西方古今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排泄场景,或许能减轻我们对排泄的忌讳之情:《堂吉诃德》第22章中,桑丘半夜拉肚子,他不敢走
远,结果堂吉诃德既听见了,也闻见了,被迫用手指捏住鼻子。在《格列佛游记》中,耶胡朝敌人投掷自己的粪便。《尤利西斯》中,布鲁姆用一本获奖的小说当厕纸。普鲁斯特说尿液中芦笋的气味能把一个简陋的夜壶变成一个香水瓶。后现代文学中,第一个伟大的马桶场景出现在美国作家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中,斯洛索普跪在马桶前呕吐时,他上衣口袋里的口琴掉进了马桶里,“口琴沉入雪白的桶颈,沉入黑夜的深处”。英国作家阿莉·史密斯在《夏》中说:“一些世界上最美好的话语,传承到我这里,然后经由我的身体排出,如同多余的维生素C。”托尼·莫里森在《苏拉》中说,当我们爱上一个人时,我们喜欢他的各个方面,“你爱他尿过的地面”。
希区柯克曾经想拍摄城市24小时的生活,拍摄饮食的各个方面——分配、买卖、厨房场景等,还有烹调和就餐。接近影片结尾时,会有阴沟、流向大海的垃圾。“从早餐青翠欲滴的绿色蔬菜到白日已尽,阴沟里冒出污秽的东西,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脏东西没有消失,只是被稀释、被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