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解疑—在历史与虚妄间游走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 河南许昌曹丞相府于2009年6月落成。图为府内雕像 )
( 河南许昌曹丞相府于2009年6月落成。图为府内雕像 )
薄葬造就的谜团
“在我看来,这次曹操墓的问世,可以算是一次突然提到日程上的发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长、秦汉考古学专家刘庆柱告诉我们。刚于2009年12月17日前往安阳考古现场参加鉴定工作的刘庆柱,凭借丰富的考古与历史学经验,在几次“蜻蜓点水”式的观察后,就首肯了考古发掘队的判断:“首先这个墓址所处的安丰乡西高穴村,就是邺城遗址的西边,跟史书上曹操墓方位的记载是相符的。其次,这个墓的形制是属于东汉晚期至魏晋早期王这个级别的,墓道宽9.8米,斜坡墓道长39米,墓室呈甲字形,顶部属于级别很高的四面穹窿结顶。综合各种因素,利用排除法就能得出结论,在这个历史时段以如此高级礼制安葬于此的,只有曹操一个人。”
在历史学家眼中,高陵之所以成为一个迷雾重重的历史疑团,原因在于这位魏晋薄葬风气的倡导者身体力行,在生前就开始极力抹平一切有关自己陵寝的蛛丝马迹。从建安二十三年(218年)起,曹操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而做《终令》,宣布自己将遵守古制,葬于“瘠薄之地”,并亲自选址,“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即在邺城西门豹祠以西,自然形成的高地上修建墓穴,不耗费民力另起封土。在弥留之际的遗嘱《遗令》中,曹操明确规定自己“持大服如存时……敛以时服”——即不要按照古制另办寿衣,使用自己事先准备好的丧服;在铜雀台上设六尺灵床,挂上一个简单的麻布灵幔,早晚摆上一点干肉脯与干粮做祭品,婢与乐伎每月初一、十五向帐中表演伎乐就权当祭祀,并遗命“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陪葬在陵苑四周。
“因为不祭陵,子孙谒陵也没有定制,所以不出几年,高陵的陵殿就毁坏了。于是文帝曹丕索性下诏说,既然先帝‘高平陵上殿皆毁坏’,所以‘车马还厩,衣服藏府’,彻底革除了上陵之礼。再加上从东汉明帝显节陵开始,陵园周围不再构筑墙垣,而是改用竹木做成的临时性藩篱行马,所以整体陵园位置时间一长也不好确定,所有因素加起来,最终使得曹操陵墓的具体所在逐渐消失在历史的记载中。”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魏晋三国时代考古专家杨泓告诉我们。
为何在两汉历代帝王大造陵寝,靡费甚巨以彰显自身功德的传统压力下,曹操仍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仅仅用《三国演义》中关于曹操生性谲诈的描述做解释,是无法令人满意的。“东汉末年,军阀为了满足自己和部下的贪欲,补充军饷,都干过发掘陵寝盗墓的事情。《后汉书·董卓》记载,董卓立献帝后,命令属下兵士掘开汉灵帝的文陵,把随葬珍宝据为己有,曹操自己也不能免咎,当时军队中就设有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这样专职指挥盗墓的官职。”杨泓告诉本刊记者,“陈琳在为袁绍讨伐曹操起草的檄文当中,就斥责说,‘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操率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所以魏晋薄葬风潮的兴起,既有移风易俗提倡节俭的意义,也有帝王为自身陵寝安全的考虑。”
 ( 秦汉考古学专家刘庆柱 )
( 秦汉考古学专家刘庆柱 )
作为佐证,曹丕自己在黄初三年(223年)下诏选择首阳东山为自己的陵址时,就明确表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未有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直白一些说,造成盗墓猖獗局面的最大原因就是,两汉以来推崇的厚葬之风。“现在看来,曹操不愧是魏晋时代丧葬风俗转变的第一提倡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魏晋时代考古专家齐东方告诉我们,1974年至1977年,安徽亳州市博物馆在亳县县城南配合农田基本建设清理一批汉魏时期曹操宗族墓,可以看做印证曹操为本次西高穴村大墓主人的佐证,以及东汉末年厚葬之风的一个生动样本:“当时墓中出土了300多块带字墓砖,可知包括有曹操的祖父曹腾,父曹嵩,曹操长女曹宪墓等。曹操祖父曹腾之墓是青石多室墓,有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南北耳室、东西偏室等,备有雕刻神兽、人物画等。虽然墓内随葬品几乎被盗一空,但仍然有包括铜缕玉衣在内的很多重要残存文物问世。曹操生父曹嵩墓,同样多次被盗,但发掘时也发现了银镂玉衣等珍品。各墓室墙壁上绘有彩色壁画,劫余物品仍然珍贵。”齐东方告诉本刊记者,“相比之下,这次西高穴村发掘的曹操墓与曹氏宗族墓的结构相似,规模却更大,从迹象上看,随葬品不如先祖墓葬中的丰富,之后的曹魏高级墓葬中,珍贵器物更少,比如山东东阿县魏东阿王曹植墓中仅出土素面玉璜4件,大都是粗糙的陶器。”
手铲与实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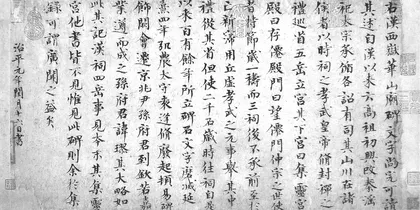 ( 魏晋三国时代考古专家杨泓 )
( 魏晋三国时代考古专家杨泓 )
历史变成了传说,它的模糊面貌只能通过靠极端强调实证性与归纳法的现场考古工作逐渐勾勒出来。刘庆柱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我们,鉴于两汉时期帝王陵墓基本没有发掘,而三国时代历史长度较短,出土墓葬非常稀少,所以考古学家们只能借助历史文献,和已经发掘的两汉时期诸侯王、贵族陵墓,以及有限的魏晋时期出土墓葬,来推敲身为魏王的曹操的陵墓形制、墓室规格、随葬器物种类等诸多疑难问题。“曹魏一朝的墓葬,在此之前,完整发掘的只有一处,洛阳正史八年墓,为什么能判断它的年代呢?因为里面有一件铁帐构,上面有正始四年字样的铭文。这是一个我们判断之后发掘魏晋时代墓葬的依据,整体形制是前堂后室,前堂左右还有两个耳室,斜坡墓道有23米长,跟这次发掘的西高穴村大墓,还有鄂城孙将军墓,以及2008年在南京发现的江宁上坊孙吴王墓的形制基本相似。”杨泓告诉我们,“帝王陵墓墓室,从殷商到西汉时代,是亚字形,即墓室四面各辟一条墓道,这种墓室形制一直沿用至西汉。东汉帝陵墓室形制还不是很清楚,现在基本推测魏晋南北朝时期高规格墓室一般由墓室、甬道和墓道组成,呈中字、甲字或者申字形。”
“有些人质疑说:为什么曹操墓里没有墓志?没有哀册(在送葬日举行仪式时宣读的祭文)?这个用考古专业知识看不是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连年战乱,为避免盗掘,帝王陵墓流行潜埋方式,不立寝殿,不造园邑,无陵前石刻。”刘庆柱告诉本刊记者,“所以东汉末年,墓碑形体逐渐缩小,转移到墓室中,最后变成墓志,从专业角度讲,最正式的墓志要到北魏、刘宋时期才出现。”
对于这个观点,杨泓也表示同意:“建安年间,曹操曾经发布过禁碑令,从而导致墓志逐渐代替了墓碑。上世纪50年代,洛阳西晋墓里出过一篇《晋贾皇后乳母美人许氏之铭》,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比较早期的墓志,所以现在还存在争议。至于哀册,道理也一样,最早发现的哀册就是80年代在北京丰台王佐乡史思明墓里发现的四十四开汉白玉哀册,阴刻文,字口填金,曹操去世后应该是按照王礼来安葬,按制不能有哀册,哀册是给皇帝用的,史思明在‘安史之乱’期间称过帝,所以有这个。作为以王的身份被安葬的曹操,是否有墓志、哀册,因为没有同时代帝王陵墓做参照,还是个未解决的问题。”
除开切实的形制与规模,一些为外人所忽略的礼制细节也成为考古历史学专家判定曹操墓真伪的关键。“这次西高穴村墓是合葬墓,里面一男两女,我们知道作为帝王陵墓,夫妻合葬墓是从东汉一朝开始的,西汉时代是同陵不同穴,后陵都在帝陵之东,坟丘较之后者为小。可你看三国时期的历史文献,各国君主都是与后同墓而葬,哪怕亡故地点不一,仅仅从这一点就可以判定墓葬的大体年代。”刘庆柱告诉本刊记者,他判定其中一具年龄在50岁左右的女性骨架,应该就是皇后卞氏:“有的历史学家说卞氏应当70多岁,这完全是臆断。曹操220年去世的时候66岁,卞皇后必须跟他同龄,230年去世的时候才能达到70多岁,但问题是,包括《三国志》在内的正史资料,都没有明确记载卞氏的确切享年,只记载她在20岁左右的时候,以倡伎的身份嫁给了曹操做妾,前面还有两任正妻刘氏和丁氏,妾縢年龄和丈夫相似,是不大可能的一件事情。”
不仅如此,在西高穴村大墓中出土的众多随葬器物,也是专家们对墓主人身份做出判断的坚实证据,首先是那件毫不起眼的玉圭(实为糙石)。“这个玉圭出土的时候是个残片,只有下半截了,按照它底部宽度推算,宽度和高度应该是1比4,它底部是7厘米多宽,那么就是28厘米高。”刘庆柱告诉本刊记者,“这个在商周时期算是国之重器,到了秦汉时候,也很重要,汉景帝阳陵等一些汉代帝王陵,在墓道或者墓室里都有发现,但都没有这次那么大的。阳陵里面那个顶多10厘米高,能够出那么大的圭,就说明墓主人身份规格很高。”另外,在墓中出土的6块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格虎大刀”、“格虎短矛”等文字,疑为遣册的石牌,也证明了墓主非曹操莫属。杨泓告诉我们,汉代高规格墓葬中,陪葬品里也往往包括兵器,在1968年发掘的满城汉墓中,考古工作者也发现过一柄墓主中山靖王刘胜的随身佩剑,为“百炼钢”工艺的雏形产品,以及三棱状铜簇以及鳞片铁铠甲等武具。对此,邯郸历史学会会长刘心长也表示同意:“曹操在遗令中不让陪葬金珥朱玉等物,应当是指财宝珍奇的器物,但随身的刀剑当不在其列。”他告诉本刊记者,“曹操曾经下过一道《百辟刀令》,打造过5把利刃,分送诸子,他自己携带的刀剑一定质量更好”。
邺城——失落的坐标系
实际上,早在10年前,另一次偶然的抢救性发掘就已经给了考古和历史研究者关于曹操墓位置相当明确直白的指示。1998年,后赵石虎时期太仆卿驸马都尉鲁潜的墓志在安丰乡西高穴村西北一处砖窑中被发现,其中明确记载,鲁潜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然而这一宝贵线索似乎并没有引发学界对于这个宁静村庄过多的关注,究其原因,似乎仍然要从围绕邺城,这座与曹操后半生政治、军事活动密不可分的古代名都所在的争论说起。“我们也知道,关于曹操墓的位置,有河北临漳说、河南安阳说、安徽亳州说、河南许昌说,甚至漳河水下说好多种,但都禁不起建立在考古历史专业知识上的推敲。”刘庆柱对本刊记者说,“首先许昌根本不可能,因为《三国志·魏书·于禁传》说得很清楚,曹操死后,孙权向曹魏称臣,为了缓和关系,释放了在樊城之战中被关羽俘获的于禁,曹丕虽然表面上不予追究,还要派他为使臣出使东吴,但是却要求他先北往邺城谒陵,并事先在陵屋里描绘了樊城之战后,庞德在关羽面前威武不屈,于禁却降服求生的画面,让于禁‘惭愧发病薨’。亳州说也靠不住,因为古代帝王死后,葬在都城周边是个定制,没有返回故里安葬的道理。”
作为判定曹操墓葬所在的最大历史地理坐标,邺城位置的移动,以及与邻近安阳县错综复杂的归属关系无疑是导致这种争论的源头:“西汉时代,今天安阳县的中部,北部,以及洹水(今安阳河)两岸,都划归邺县治下,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整个安阳为邺县辖地,西晋至北魏末年,安阳与邺县两县并立,但今日安阳县之北部仍然属于邺县。”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魏晋南北朝史专家梁满仓告诉本刊记者。
1983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合作,开始对邺城进行较全面的勘察与发掘,最终探明邺城位于河北临漳县和河南安阳县交接的漳河北岸,位于今日临漳县境内。“邺城地处黄河中游,位于太行山东麓南北要道,交通便利,又有漳水环绕,早在王莽时代,附近的邯郸就被列为五都之一。黄巾起义被镇压后,担任冀州刺史的皇甫嵩采取了休养政策,让这里成为冀州经济核心地区,史书上用的形容词是‘经济强实’,拥有丰富的兵员人口和农业生产力,能够‘带甲百万,谷支十年’。”梁满仓告诉本刊记者,“所以这里一直被北方割据势力看做建立政权的首选。兴平二年(195年)袁绍初定河北后,属下奋武将军沮授就建议‘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把邺城作为割据政权的国都。”204年,曹操攻灭袁绍后,为了控制北方冀青幽并四州的军事与经济,防止袁绍和其他北方割据势力死灰复燃,自任丞相兼冀州牧,由许都移镇邺城,多次迁徙匈奴归化部民,汉中张鲁部属以及袁氏遗臣部曲等至邺城居住,并借征乌丸、袁尚等军事行动开凿了利漕、平虏等渠,使邺城成为黄淮平原上的水运交通枢纽。9年后,又把并州划归冀州境内,最终在被封为魏王后,将邺城升为王都。
“根据现有考古发掘成果,邺北城的平面基本呈长方形,东西宽2400米至2620米,南北长1700米。据《水经注》载有7个城门。文献记载,邺北城有大型高台建筑,即铜雀台、金虎台和冰井台,其中金虎台和铜雀台的一部分是邺北城仅存的地面遗迹,这里是全城的制高点,可以俯看全城和邺城附近情势,其军事防御目的显而易见。邺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马面(突出在城垣外侧的一种台状的城垣附属性设施)的城市,所以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迁都至洛阳后,仍称邺城为王业之本基。”齐东方教授告诉本刊记者,“不仅如此,曹魏时期邺城开创了一种新的城市布局模式,建春门至金明门是全城唯一的东西大道,将全城南北分开,北半部主要是宫城、衙署,南半部主要分布一般官署和居民区。中阳门大道正对着宫殿区的主要宫殿,已形成了全城的中轴线,这种布局规划对后来的都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梁满仓看来,曹操定都在邺的另一个考虑,就是让整个曹魏政权运转的中枢远离许昌朝廷反曹势力的监视、掣肘甚至叛乱。一个有力的例子就是建安二十三年,许昌发生了太医令吉平、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的谋反事件。邺城的兴盛,使得它在西晋“八王之乱”、关中洛阳地区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成为晋朝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梁满仓告诉我们,这一传统被随后兴起的后赵、前燕、冉魏所继承。到了东魏高欢时期,高欢挟持孝静帝迁至邺城,仍然以其为首都,但嫌曹魏时代的邺城(北邺城)格局过于狭促,于是以北邺城的南城墙为北界,兴建了南邺城,城址跨越了漳水。然而时间长久后,历代史家文人往往把南北邺城混为一谈,认为南邺城亦是曹魏时代邺城的一部分,附近的两朝皇陵区就是传说中的曹操疑冢。“一些地方历史研究者认为曹操墓位于河北磁县以南,这是不正确的,实际上磁县一带,漳河沿岸墓葬都是东魏北齐的大墓,比如北魏淮南王元显墓,以及魏孝静帝元善见墓等。”杨泓告诉本刊记者。
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居于邺城的相州总管尉迟迥起兵反对杨坚辅政,杨坚平乱成功后,借机纵火烧城,南迁相州邺县、魏郡40里到了安阳,改安阳为邺,原邺县更名为灵芝县,显赫一时的北方重镇邺城自此湮没在漳河畔的荒草中,关于曹操墓地位置的各种歧义与假说也逐渐应运而生。
“可以确定的是,至少截至唐代,相当一部分关于曹操陵寝所在的记述还是大体正确的。”刘庆柱对本刊记者说,比如南齐诗人谢脁在《同谢咨议铜雀台诗》中,就有“穗帷飘井雗,尊酒若平生,郁郁西陵树,讵闻歌吹声”的句子。唐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制》卷十“相州邺县”条记载:“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唐代的邺县在曹魏邺城旧址城西50步,向西30里,稍稍偏南的位置即是今天的河南省安丰乡西高穴村一带,恰好与元人纳新《河朔仿古记》中关于曹操墓在“邺西南三十里”的记载呼应。到了宋代,随着墓址的进一步荒废,加上在辽金等北方少数民族频繁犯边,市井群众的同情心逐渐移向南方的蜀与吴,而仇恨来自北方的魏的情况下,就有了“七十二疑冢”的传说。到了罗贯中时代,这种传说变成了曹操临终前的“遗命”,从而加强了曹操临终时刻仍不改其诡谲奸诈本性的奸雄形象。随着杂剧戏曲和各种民间平话传奇的兴盛,这些民间小传统开始逐渐影响了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史家:元末明初文学家,历史学者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就有“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的记载。后世进而以讹传讹,发展出曹操墓深在漳河水底的传说。18世纪,以观光客身份随使团来华的朝鲜学者朴趾源就在自己的旅行笔记《热河日记》中,记载了一则有趣的轶闻:乾隆十三年,清帝“渔于漳河”然而随行泅水者“腰断浮水”,于是乾隆征调民夫万人将河渠疏通排干,遂发现“其下有冢”,内里即是曹操的棺木,“银海金凫,具帝者冕服”。很明显,这则传奇很可能源自蒲松龄《聊斋》中“曹操冢”一则——至此,虽然曹操陵墓的现实遗址已经不可考据,但它无疑和戏台上曹操的白面扮相和“轻捻长髯,双肩一动”的动作一样,已经成为某种民间意识形态褒贬忠奸的永恒符号。■
(文 / 朱步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