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扬雄对圣人神秘性的消解
作者: 伦凯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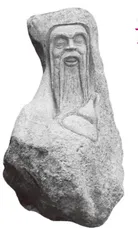
摘 要:汉代谶纬神学盛行,圣人本身的面貌被掩盖,甚至赋予神秘化的倾向。扬雄通过多种方式为圣人正名:著《法言》以学正统的圣道;以孔子为师,学圣人之经;崇圣道。
关键词:扬雄;圣人观;神秘性
扬雄之时,谶纬盛行,古代的圣人往往被增附为具有神迹或神异的色彩:“华胥履大人迹而生伏羲”“庆都与赤龙合而生帝尧”“刘媪梦赤乌如龙戏己……生刘季为汉皇”等等。这些描述均将圣人神秘化,而扬雄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将消解圣人的神秘性作为自己的目标。扬雄消解圣人神秘性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著《法言》以学正统的圣道。关于《法言》的写作动机,扬雄认为诸子眼中的圣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1],应对办法是撰写《法言》。扬雄感慨诸子对圣人描述过于荒唐,使得后人分不清真正的圣人形象,所以他撰写《法言》十三篇,来论述真正的圣人。《法言》主题基本围绕着圣人之道以及圣人之经所展开,尽管不是特别全面,但确实是汉代不可多得的专门描述圣人之道的书。
其二,以孔子为师,学圣人之经。扬雄言:“仲尼之道,犹四渎也,经营中国,终入大海。”[2]孔子之道是安定天下的圣人之道,且需要对其道用之得当。如果所用不得当,就会落入鼠穴,不会得到施展。作为圣道,孔子之道通行天下,放之四海而皆准,故有如四渎之入大海。诸子之道也可能用于一时一地,故犹如“西北之流”之“纲纪夷貉”。在扬雄看来,圣道之有大用,是诸子之道不可比的。“西北之流”入于“沱”“汉”之喻,既比喻诸子之学分歧无宗,还比喻诸子之学终将被儒学圣道所统一。此外,扬雄十分崇尚“五经”,认为“五经”为“经纶大法”[3]。关于作为圣人思想载体的“五经”,扬雄认为,“惟五经为辩”。在扬雄看来,“五经”就是用来分辨各种事理的。解释各种自然现象的著作,没有什么比《周易》更能分辨事理;解读历史事件的著作,没有什么比《尚书》更能分辨事理;解说人的行为规范的著作,没有什么比《周礼》更能分辨事理;抒发内心感情的著作,没有什么比《诗经》更能分辨事理;解说历史事件褒贬意义的著作,没有什么比《春秋》更能分辨事理。[4]此外,除了这五部经书,其他著作虽然也有分辨事理的作用,但也是微不足道的了。扬雄认为:“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5]圣人能够把语言文字的功能发挥到极致,所以,圣人所著的“五经”涵盖了天道和人事各方面的真理,这就是“五经”具有超乎其他任何著作分辨功能的根本原因。
其三,崇圣道。扬雄推崇尧、舜、禹、周公等圣人,并认为,圣人之道,就像中午的太阳,过与不及都不能显示其最大功用,由此来说明圣人之道是绝对真理的存在。扬雄又以日月比喻圣人,以众星比喻诸子,在太阳和众星的对比中见到圣人与诸子的差异。
扬雄以孔子之道为圣道。孔子“祖述尧舜”,上承于尧、舜等古代圣人,下开儒学之先,因此,扬雄认为孔子为圣人。扬雄以孔道为圣道主要体现在他说的“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驾说者也,不在兹儒乎?”[6]儒家宣扬圣人是“代天立言”,圣王则是“替天行道”。《论语·子罕》载:“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孔子继承的是文王之道,而孔子之后的儒者继承的即是“孔子之道”,到底说来,二者都是天道。在扬雄看来,传扬圣道的使命彼在孔子,此时则在其自身,因此说“使诸儒金口而木舌”[7]。扬雄此语实际上是劝告儒者传播仲尼之道要谨慎恪守,如此圣人之道就可以永远常在了。
如何以孔子之道达到圣道?《法言》载:“孔氏。孔氏者,户也。”[8]扬雄认为,从山脚登山的蹊径有无数条,不知道应该走哪一条;面对墙壁的门有无数道,不知道应该进哪一道。当有人问扬雄:“我该从哪道门进入呢?”扬子说:“孔氏之门。”可见,在扬雄看来,在异说盛行的西汉末年,只有孔子之道才是人们所追随的圣道。扬雄论述圣人指的是尧、舜等圣人,且文王死后,由孔子来负责传播圣道,由此,推崇孔子,认为孔子是圣道的代言人;并指出真正的圣道是孔子之道,入圣道必须入孔门。
注释:
[1](汉)班固:《汉书·扬雄传》,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535页。
[2][4][5][6][7][8]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04页。
[3]梁宗华:《论扬雄对儒学的改造和发展》,《东岳论丛》2016年第12期。
作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