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

为了欧洲
尤尔根哈贝马斯德国当代哲学家
本文最早发表于3月21日的《南德意志报》,节选自公众号“文化纵横”
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尤其是七国集团(G7)成员—虽然政治立场各异,但长期以来都认同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这一基本立场。然而随着特朗普重新掌权并引发美国政治体系动荡,这种格局已土崩瓦解—尽管名义上北约的命运尚未最终定论。特朗普在就职典礼上的怪异举止和混乱演说如同一枚炸弹,恐怕彻底粉碎了德国、波兰等国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最后一丝幻想。对于习惯传统就职仪式的观众来说,特朗普关于“黄金时代”的狂想和自恋姿态,简直像是一场精神病理学的现场展示。然而,台下雷鸣般的掌声和马斯克等硅谷巨头的热情支持,清楚地表明特朗普的核心团队将按照传统基金会的既定方案,推进美国制度的全面重构。当然,政治口号和实际成效往往相差甚远。
新总统首批政令包括驱逐非法移民(其中许多人已在美国生活数十年)等讨好基本盘的措施,随后又突然取消具有国际影响的援助项目(此举涉嫌违法)。这些由“清洗专员”马斯克主导的越权行动绝非偶然—他在接管推特时就曾如法炮制。这些初期举措既暴露了政府机构“激进瘦身”的政治目标,也暗示了自由意志主义的经济政策。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因为从长远来看,“国家缩水”很可能与向数字化控制的技术统治转型同步推进。
硅谷对这类“去政治化”的自由意志主义幻想由来已久—他们梦想将政治彻底转化为由新技术驱动的公司管理模式。然而,这些宏大构想如何与特朗普无视规则、随心所欲的决策风格兼容,目前仍是个谜。更令人担忧的不仅是这位“交易艺术家”的短视行为,还有他那难以预测的非理性—正如他那个“房产商重建加沙”的荒谬幻想所显示的,这种疯狂很可能最终与副总统或其技术官僚盟友的长远规划爆发冲突。
这场制度变革的政治走向最难预料—它表面上会保留已被架空的宪法,实际上却在构建一种技术官僚与威权统治的混合体制。随着社会问题日益复杂,这种体制正好迎合了“去政治化”民众的期待—他们早已厌倦承担重大政治决策的责任。政治学界早有“规制型民主”的理论,为这种趋势提供了学术包装。在这类体制下,形式上的民主选举就被视为足够,至于民众是否真正参与理性讨论,根本无关紧要。但要注意,这种新型威权统治与历史上的法西斯截然不同。美国街头看不到制服游行,日常生活大体照旧—除了那些4年前受总统煽动冲击国会、如今却获得赦免的叛乱者。社会依然沿着清晰的文化分歧线严重分裂。挑战政府违宪的诉讼才刚刚进入下级法院。媒体半推半就,尚未完全屈服。高校和文化界开始出现零星抵抗。但新政府的行动效率毋庸置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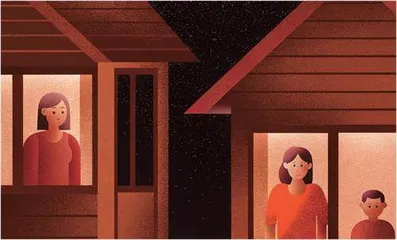
谁是家里人?—对中国家庭成员界定的调查实验研究
张春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副研究员本文节选自《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1期
中国人对“谁是家里人”的认知,同时受到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复杂影响。首先,中国人对家庭边界的认知并不稳定,会受到语境影响而具有可变性:在代际团结的“大家庭”语境暗示下,受访者会将更多亲属纳入家庭成员的界定中,尤其是上一辈和旁系亲属;反之,在个体主义“小家庭”语境暗示下,受访者回答的家庭规模要更小,更集中于核心家庭的配偶和子女关系。可见时至今日,家庭在中国人的认知中仍是一个边界模糊的概念。但不同于费孝通当年所论述的以乡土社会差序格局为背景的家庭边界可伸缩性,当今中国人同时兼具“大家庭”与“小家庭”的认同,体现的是他们在传统与现代的话语之间的徘徊。
其次,直系亲属关系是中国人界定家庭成员时最重要的标准,即便直系亲属分散而居,也不影响大多数中国人将这些亲属均认定为家庭成员。但不同于父权制传统下家庭成员范围被严格限定在父系血亲之内,如今绝大多数受访者会认为已婚女性的父母如果同住也是其女儿的家庭成员;对不与父母同住且无定期经济往来的已婚女儿,也有超过2/3的受访者会将该女性与其父母视为同一家庭。不过,传统父系观念并非完全没有影响:相比于女儿,已婚儿子无论与父母是否共同居住或有无经济联系,他与父母都更可能被认定是一家人。
最后,经济联系是界定中国传统家庭边界的一个重要标准。如今,经济联系虽仍对识别上一代父母是否为一家人存在一定影响,但这一影响已不再是决定性的。一方面,这很可能与中国家庭的生计模式变化有关。传统中国家庭的生计模式是靠一个钱袋子生活的家族共产制,而如今家庭成员个体的经济独立性增强,在很多情况下家庭收入不需要统一保管和分配,这会削弱人们对家庭成员间经济联系重要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什么样的经济联系能够用来识别家庭边界,可能难以被现有的操作化方案很好地测量出来。当“同灶吃饭”的标准已不适用于人口大规模流动和城镇化的中国家庭,什么样的经济联系能有效识别家庭边界仍有待探索。
互联网“大厂”实习生的劳动期待与剧本书写
吕梓剑林仲轩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教授
本文节选自《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11期
“模糊性(ambiguity)”是实习劳动的显著特征,它包括介于在校生和临时工之间的身份模糊、薪资模糊与权益模糊,以及涉世未深、阅历不足、职业规划尚不明晰所致的自我认知模糊。“大厂”常将此作为制造期待、强化控制的筹码,并在求职和入职前期层层加码,其所造成的信息误差与认知偏差,会进一步加剧实习生本真自我的蒙蔽,继而触发一系列理想化的积极实践。
个体化强调“为自己而活”的自我意识,意味着“人们可以选择随自己意愿而过的人生”。个体化意志下的实习生,倾向将自我认同视作行动价值的评判标准,尤为看重个性需求与情绪价值。这种个体主义也同样显现于劳动过程之中,他们期盼能从中收获经验和认可,实现自我效能感。然而,学习经验只是“大厂”编织的谎言:第一,“大厂”已具备成熟的经营模式,且由于实习岗位流动性过强,交付给实习生的业务多半是套路式、机械化的;第二,出于公司机密及工作经验不足的考量,部分上级会对实习生有所保留,将其拒于核心工作之外,他们只能从事琐碎、易上手的边缘工作,难有大展身手的机会。
如上所言,实习不单是前文所列的经验劳动、希望劳动,它也是指引人生、排除错项的“试错劳动”。本文亦发现,面对浸满未知和动荡的不确定时代,青年劳动者更倾向取悦自我、稳定优先的人生,但对流动的适应,又迫使他们深陷“自我去稳定化”的窘境。频繁的实习试错,未来的跳槽换岗,均是为满足自我诉求的去稳定化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