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送精神病院的法理之问
作者: 何国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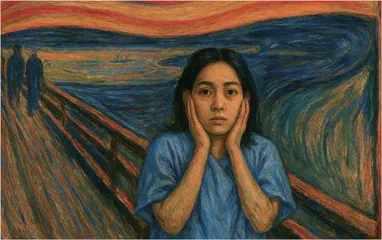
4月5日,安徽省淮南市发出一份通报,称已成立由市检察院、司法局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市民张坡被强制送医及工伤待遇问题展开全面调查。4月7日,芜湖权威部门则就一起类似事件回应媒体称,将当事人胡女士送到精神病院是出于对她的安全考虑。
这是近期发生的两起被强制送往精神病院的事件,相关地方政府和国内舆论都对此高度关注。
张坡称,其在2024年6月因工伤维权被警方强制送进精神病院22天,随后,安徽某司法鉴定机构对张坡的鉴定结果显示其并无精神疾病。天津的胡女士则于4月初反映,她在3月9日从安徽返京途中被多名不明身份人员拦截,并被强行带至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以“流浪者”身份强制收治6天。出院后,胡女士在南京脑科医院检查证实其无精神疾病。
这两件事具体情形有所不同,但都反映了强制送医的合法性问题,以及人们所关注的,少数地方有关部门是否采取简单粗暴甚至违法的方式“解决问题”。
“强制送医”须满足两个条件
关于“强制送医”,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精神卫生法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刑诉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
但这限定在涉刑事案件中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而且这类“强制送医”的决定,需要人民法院作出,而非公安机关。
因此,张坡和胡女士并非涉刑类的“强制送医”,而是精神卫生法所规定的“强制送医”类型。
按照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注意,这里只是针对附条件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送医进行诊断,而非住院和治疗。
第三十条紧接着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强制送医”类的非自愿住院是例外情况,需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二是满足以下两种情形中的一种:
(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
(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对于情形一,“强制送医”需监护人同意,监护人不同意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应当对在家居住的患者做好看护管理。
对于情形二,有关部门可“强制送医”,但患者监护人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不同意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
对再次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自主委托依法取得执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回看张坡和胡女士被“强制送医”的情形,很难跟上述法条匹配。
根据报道,张坡当时被“强制送医”发生在其因工伤维权时,他当时在原工作单位大门前举着写有“实名举报”等内容的牌子拍视频,并和前来制止的工作人员发生纠纷。
但根据媒体报道,从现场监控视频、派出所询问笔录中张坡的语言描述来看,他当时不存在精神异常现象,也没有伤害或危害自身及他人的行为。
此外,张坡妻子表示,她接到派出所民警要把张坡送精神病院检查治疗的通知时,明确表示反对。
这意味着,张坡被“强制送医”不满足上述精神卫生法规定的任一条件。
胡女士是在她从安徽返回北京的途中被拦截“强制送医”。根据媒体报道,当地权威人士对此回应,3月9日事发当天,胡女士不听劝阻,强行从安徽开车到北京。
考虑到她精神状态不佳,从安全角度考虑,公安机关才将她从北京郊区的检查站带到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治疗。
既然胡女士能从安徽顺利开车到北京郊区,且在途中未发生任何危险,一般可以说明其精神状态并无异常。凭此很难界定她对自身或他人产生了伤害或具有伤害危险。
此外,胡女士及亲属提供的录音显示,院方人员表示胡女士当初是以流浪人员的身份被派出所“强制送医”。这也明显不合规,当地警方此前因胡女士报案与其有多次接触,不可能不知道胡女士并非流浪人士。
而且,胡女士家属表示,在胡女士住院的6天内,他们并未接到过电话通知。事后,胡女士被其他医院鉴定为精神正常。
据此,当地警方将胡女士“强制送医”一事也很难跟精神卫生法规定的“强制送医”情形匹配。
强制入院缺乏中立机构审查
2013年精神卫生法的出台,被认为可以终结“被精神病”现象。现实中,因为精神卫生法对“强制送医”作了相应的条件限制,确实大幅减少了“被精神病”现象。
但最近张坡和胡女士等案例的出现,表明精神卫生法的相关规定仍难以杜绝此类现象。或者说,精神卫生法对“强制送医”的规定,仍存在模糊地带。
精神卫生法规定“强制送医”的两个条件,一为“严重精神障碍”,二是两种危害行为和危害危险。
卫生法学者的研究指出,尽管精神卫生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对“严重精神障碍”作出了定义,但落到司法实践中,哪些种类以及何种严重程度的精神障碍患者属于强制送医的对象,仍是难以把握的问题。
伤害自身及危害他人的行为比较好辨认,但有关“危险性”的要件却没有详细规定。比如,什么是“伤害自身的危险”和“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这种危险是人身损害、财产损害还是精神损害?危险是“即刻”的还是“可能的”?这些都没有详细规定。
精神医学专家勾蕾和周建松在论文《我国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住院相关权益保护—精神卫生法实施10年的思考》中也指出,相比“危险行为”,“危险性”具有不确定性,目前缺乏统一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来认定患者的行为是否具有危险或危险的可能性,这为自由裁量和酌情处理留下了较大空间,可能导致非自愿住院的滥用。
更重要的是,强制住院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强制措施”,具有较强的公法属性。因而,对于强制住院这一决定,理论上更适合由公权力机关作出。
但目前,对于强制住院流程,监护人和公安机关有送治权,而诊断、住院等一系列决定权,全由医疗机构作出,因此从根本上排除了司法干预的可能。
而医院作为一个盈利机构,难免具有一定的道德风险。同时,在面对公权力送治的疑似病人时,难有拒绝收治的动力。
在这两起事件中,张坡和胡女士都以精神障碍患者分别被安徽淮南市第四人民医院和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作出有病诊断,并据此收治住院。但事后不久,两位当事人在其他鉴定或医疗机构都确认自己无精神障碍,为何会出现如此迥异的结果?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强制送医”的诊断权和住院权集中在同一家医疗机构手中,很难避免出现“被精神病”的个案情况。
国际上多数国家和地区,为了防范医疗机构和其他个人、部门滥用强制住院制度,大都将非自愿住院纳入司法程序或准司法程序,即医疗机构的非自愿入院建议,必须经过法院或中立机构的裁决或审查。
如英国设立精神卫生法庭和专家委员会,德国设立访查委员会,日本设立精神医疗审查会等机构,对基于精神病学专家建议的非自愿住院进行认证。
事中、事后救济乏力
理论上来讲,就算“强制送医”判断标准不够细致,没有中立或司法机构对入院决定审查,使得“被精神病”行为有得以实现的可能,但只要有完善的事中和事后救济途径,这类问题也可以被及时纠正。
目前,精神卫生法赋予监护人的权力过大,未充分考虑患者的自决权(并非所有类型的精神患者都丧失了知情同意能力),而是直接由监护人代为行使。这可能导致家庭滥用精神医学剥夺个体人身自由,出现因利益争夺将亲属直接送进精神病院的事件。
对于危害他人行为或相关危险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被“强制送医”的,精神卫生法设置了当事人和监护人的异议救济程序,可对住院诊断结论提出再次诊断和鉴定,对再次诊断仍有异议的可自主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
但张坡和胡女士的案例表明,当事人被“强制送医”后,越是试图向医生澄清自己没有病,反而越有可能被医生视为精神病患者,陷入百口莫辩的尴尬境地。
而且,两个案例中,当事人家属都没有得到及时通知。张坡的入院记录上甚至写明:“出院必须由派出所办理,家人不允许探视。”这相当于架空了当事人及其家属的救济途径。
错误形成后,事后救济成为当事人维护自己权利和抚慰心理创伤的唯一途径。
但根据精神卫生法规定,违反精神障碍者“强制送医”的规定,将非精神障碍患者故意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治疗,给当事人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仅承担赔偿责任。
而法学界有意见认为,故意对正常人或不需强制治疗的精神病人施行强制治疗,是对他人人身自由和基本权利的侵犯,行为恶劣,后果严重,其法律责任不应当只是赔偿,而应在刑法中明确规定相关罪刑,以震慑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此项制度达到非法目的。
此外,精神卫生法还规定,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认为行政机关、医疗机构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侵害患者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但研究卫生法学的学者陈绍辉在一项名为《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住院诉讼案件的司法裁判及其困境》的研究中指出:实际中,当事人在事后诉讼过程中仍面临起诉难、胜诉难、鉴定难等多重困境;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也存在案由选择不当、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当事人承担主要举证责任,使得大量案件中当事人必须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审理思路错位、非自愿住院合法性审查弱化等突出问题。
因而,如果要铲除“被精神病”这一顽疾生长的土壤,就必须堵上“强制送医”判断标准不够细致、没有中立机构或司法机构对入院决定审查,以及事中、事后救济途径缺乏和被架空的漏洞。
正义的实现,依赖每一环节的合法性和透明性。回到这两个事件,两位当事人被强制送医的程序是否正当,各环节是否经得起追问,还需要相关部门继续跟进,确保公众知情权和对安全感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