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怯弱时,这群孩子勇敢地抵抗
作者: 叶克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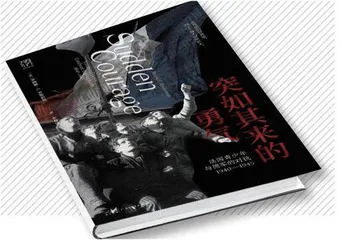
在《突如其来的勇气:法国青少年与德军的对抗,1940—1945》一书中,罗纳德·C.罗斯伯顿摘录了一些年轻抵抗者的书信。他写道:“在1940—1945年被德国行刑队处决的人质和抵抗者有4000—5000人……那些死去的年轻男人和男孩,在监狱里一关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然后突然得知,几个小时后他们将被处决,作为抵抗者对德国人发动的暴力行为的惩罚。”这些年轻人会得到写告别信的机会,每人最多三份。
随着抵抗行为越来越多,被抓的抵抗者们(哪怕只是嫌疑犯)会被更加迅速地处死。受刑者写好告别信、填好地址并被处决后,当局会先审查信的内容(用浓墨盖住不当言论,或删除信中部分字句段落),然后才将信交由狱吏、神父或军官带给死者的家属。收信人会被警告,不允许与家庭成员以外的任何人分享信件内容,否则将受到处罚。但《突如其来的勇气》写道:“尽管如此,这些信件经常被大声朗读出来,听众不光有家人,也有亲近的朋友;一些信件被复印并传阅;一些信件甚至被刊登在地下报纸上。信中所体现的,特别是来自早逝的年轻人的痛苦、勇气和爱国主义精神,就这样大胆地被公之于众,并让所有人都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人在20岁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那么我,面对占领能做什么呢?”
二战期间,纳粹德军一路高歌猛进,逼近巴黎。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出走逃亡,许多人死在路上,无数家庭离散。与此同时,许多人也开始投入抵抗,他们保护跳伞的盟军飞行员,收集掩埋撤退士兵丢弃的武器,袭击落单的纳粹德军……
1940年到1944年间,抵抗纳粹占领法国的行动往往由年轻人发起和执行。这些青少年以自己的未来为代价,投身于抵抗运动,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他们当然是勇敢的,但也难免恐惧、迷惘和无助。他们中的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幸存者也难免内心创痛。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些年轻人在信件中表达了恐惧与焦虑,但他们“很少会想到自己,更多的是想到他们的死会对留在身后的人,即他们的爱人,他们的父亲、母亲,以及他们的弟弟妹妹,造成什么影响。他们还会对法国的命运进行最后的思考。时常有人提到来世,但几乎都是为了安慰收信人。一些人会表达自己的歉意,抱歉自己惹上了这样的麻烦,或抱歉自己不是父母理想中的孩子,但没有人后悔曾站出来反对暴政。许多信件带着自省的口吻,一方面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落到这般田地,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依照信念做了正确的事”。
考虑到写信者是青少年,而且是将死之际,他们的表达已经足够清晰,也足够真挚,足以打动所有人。
一位年轻人在赴刑场之前,在写给父母的信中写道:“这是我给你们写的最后一封信。你们会在我死后收到,它会唤起你们悲伤的回忆……我本可以出卖我的同伴来换取我的生命……但我没有这样做。我要回了我的两个笔记本,其中一个的封面上写着尼采的一句话:‘我总想攀得更高。’我将(这句话)留给所有的理想主义青年。请大家永远记住我的坚强;我的名字将在我死后鸣响,不像葬礼的钟声,而是像希望飞翔的声音。”
19岁的费尔南·扎尔基诺在给妹妹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自从我来到这里,我就一直在深深地审视自己。我意识到,尽管我缺点很多—不止一两个,但我并没有那么差劲,我本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人……我喜欢吹牛,这我知道。但说实话,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冷静。在宣判之前,我经常哭,但宣判后,我连一滴眼泪都没流过。我从内心感到一种深邃的平静和安宁。似乎我只剩下一个考验了,那最后一个,之后一切就都结束了,仅此而已。”
这些信件并非全部,而且过于随机,随机到写作者根本没有时间和心理准备组织自己的想法。因为处决本身也是随机的,“最有可能的是,当有通告说有德国士兵或军官被暗杀时,他们就从囚犯中被随意挑选出来”。
而且,“这些年轻的作者知道,他们的遗言能否被传达出去,全凭当局的决定;给他们纸笔并浪费他们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也许是反复无常的抓捕者戏弄他们的又一个残忍把戏。那些有自知之明、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凭借常识,怀疑这些信件最终都会被丢进监狱后院的垃圾桶里。因此,他们最重要的倾诉对象,至少在潜意识里,还是他们自己”。
那些可能只有十几岁的少年,诠释的不仅仅是勇气,还有在非常时期参与政治的可能性。所谓抵抗,并不仅仅是拿起武器袭击纳粹德军,派发传单、印刷报刊、街头涂鸦、传递情报、协助匿藏和保护受害者……都是抵抗的一部分,也是对大众的召唤。
而且,青少年抵抗者有着自己的优势。他们熟悉城市的各种角落,可以在黑夜中穿梭于街巷,他们还能活学致用,将物理公式应用于燃烧弹的参数计算。1941年,一群巴黎高师学生刺杀德军上校,就以学校实验室的原料制造定时装置,将引爆时间精确设定于军官午休结束走向办公室时,正如书中所言,这是“用知识对抗暴力的新战争形态”。
所以,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孱弱不堪的孩子,也可能是极为出色的抵抗者,比如书中提到的雅克·吕塞朗。
雅克·吕塞朗在7岁那年因意外而双目失明,但他表现出了惊人的适应力,接受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他有一个亲密并懂得尊重他的朋友,陪伴在他身边,并不把他当成病人,不会搀扶他走路,而是任由他自由奔跑,但时刻紧随,在有危险时将他扶住。
这种留有足够空间的尊重、踏实的友情,让吕塞朗懂得了独立,也因此勇气十足。他还拥有开明的父母,并未将他送进巴黎那座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盛誉的盲人学校—法国国家盲童学院,而是希望孩子不要被隔离在残障的世界里,于是将他送去接受普通教育。
在开明包容环境下长大的雅克·吕塞朗,后来成为抵抗运动组织的领袖人物。以他为核心的“自由志愿军”,是巴黎被占领期间最受尊敬的早期抵抗运动组织之一。正如他“拒绝让丧失的视觉从精神或身体上定义自己”一样,他也不能接受自己的祖国被纳粹定义。
《突如其来的勇气》写道:“1940年5—6月的军事溃败,以及随之而来的纳粹占领,不但没有使吕塞朗更深地陷入寂静的失明世界,反而激发了他的能力,让他将自己神奇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到影响周遭人与事的变化上。”
吕塞朗成为抵抗运动的中坚,当他的朋友们“迷失”在巴黎迷宫般的街道中时,他们会向他这个“盲人”求助,寻找回家的路。他的失明越来越被朋友们看作一种“特殊能力”,令他与众不同,并促使人们追随他。他还创办了地下报纸,它后来成为巴黎最知名的日报之一—《法兰西晚报》。
1943年,因为叛徒出卖,吕塞朗被纳粹逮捕,后来被转押到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在残酷环境中从未失去信念,在集中营仍然组织秘密抵抗。1945年,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解放,吕塞朗幸存,而被押送到布痕瓦尔德的2000多法国人,仅有30人活了下来。
所谓“突如其来的勇气”,当然有莽撞的一面,在习惯计算生存概率和利益的成年人看来,这些年轻人抵抗纳粹就如同飞蛾扑火,但正是这些人性的闪光,让文明得以延续。
可贵的是,罗斯伯顿并未采用传统的“高大全”英雄主义叙事,而是通过档案、日记和口述史,呈现他们的被迫早熟。他们并非纯然无畏,而是在恐惧中学会成长。他们爱法国,但同样爱自己,不希望个人命运被邪恶外力吞噬。正如一个女孩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我们不是英雄,只是无法假装看不见明天的太阳不再属于法兰西。”他们珍惜自己的生命,所以“渴望的不是纪念碑,而是能活着见证自由的清晨。”
在父辈怯弱地选择以维希政权与纳粹“合作”的时代,青少年们用自己的勇气坚守正义,为法国留下了战后复苏的种子。正如书中所言:“一个全体主义政权需要用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将长久的、令人麻木的恐惧根植于人民内心,尤其是当一切表达抵抗的途径都被封堵时。但总有一个人或一些人,能想办法举起拳头,或创作一幅艺术作品,或发出一个声音表明‘这必不会长久’。在这个极其复杂的时期,这就是所有抵抗者的力量,无论这力量多么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