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作品中的民俗书写:地域文化的诗意展现
作者: 黄珈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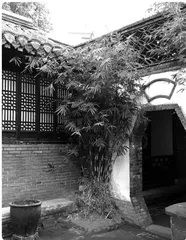
地域文化是文学创作的富矿,诸多作家从中汲取养分,汪曾祺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以独特的视角与细腻的笔触,将地域文化融入作品灵魂。童年于高邮城的浸润,下放张家口的磨砺,为他积累了深厚的民间生活素材。创作时,他从环境、风俗、人物谋生方式等多层面构建地域文化之形,借方言与白描铸就独特文风,借平凡人物诠释地域文化内核。其创作宛如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窥探地域文化的诗意与魅力,探寻文学与地域文化交融的奥秘。
“民间生活积累为地域文化书写之源”的底蕴挖掘
汪曾祺出生于高邮城,童年时期,家乡的大街小巷便是他探索世界的舞台。其中,东大街对他而言意义非凡。东大街上,南北杂货店、手工作坊、布店、酱店等各类店铺林立,这些店铺不仅是商业活动的场所,更是地域文化的生动载体。南北杂货店内,来自不同地区的货品汇聚一堂,反映出当地商业交流的繁荣景象,以及因商业往来而形成的多元文化融合。手工作坊中,工匠们专注于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展示,每一件手工制品都凝聚着地域文化的智慧结晶。酱店飘散出的独特酱香,是当地饮食文化的鲜明符号。汪曾祺穿梭其间,耳濡目染,这些日常场景逐渐内化为他对家乡地域文化的初步认知,构成了他民间生活积累的重要基石,为日后文学创作中的地域文化书写埋下了种子。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民众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是民族文化的基础和重要体现。汪曾祺在东大街的童年经历,正是对家乡民俗文化的初步感知与情感记忆的积累。
1958年,汪曾祺被下放至张家口进行劳动改造,这一经历极大地拓展了他民间生活积累的广度与深度。在张家口的农村,他深入体验到农民的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农民们在艰苦生活中展现出的坚韧与刚强,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在这种生活体验的影响下,他创作了《羊舍一夕》,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四个农村孩子在乡村夜晚的生活场景以及他们为生活奋斗的故事。作品中,乡村夜晚的宁静、孩子们对未来的憧憬,都源于他对张家口农村生活的深入观察与切身体会。这不仅丰富了他的创作素材,更使他对地域文化有了新的理解,将农村的质朴与坚韧融入他的地域文化认知体系中,为他的地域文化书写增添了新的维度。
汪曾祺的高邮童年经历与张家口下放体验,构成了他独特的民间生活轨迹。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他不断积累关于不同地域的民俗风情、生活方式、人物性格等方面的素材。这些素材并非简单的堆砌,而是经过他的思考与沉淀,逐渐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地域文化认知体系。他如同一位民俗文化的收集者,将民间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如传统节日的独特仪式、百姓日常的饮食习俗、邻里之间的交往方式等,都纳入自己的素材库中。从民俗学的田野调查理论而言,他的这种生活积累方式类似于民俗学者在田野中的实地考察,通过亲身参与和观察,获取第一手资料,从而使他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呈现出高度的真实性与生动性。
汪曾祺早年在高邮的成长经历,为他提供了家乡地域文化的底色;张家口的下放生活,则拓宽了他对地域文化的认知边界。他在不同地域的民间生活积累,犹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河,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成为他地域文化书写的深厚底蕴,使他能够在作品中生动地展现出丰富多彩、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画卷。
二、“多层面描绘构建地域文化之形”的呈现方式
文学地理学理论认为,文学作品中的环境是地域文化的物质载体,承载着特定区域的自然与人文信息。例如,《大淖记事》开篇对“大淖”名称进行溯源后,紧接着展开对周边环境的细致描绘:沙洲上的茅荻、萎蒿,高阜上的炕房、浆房、鲜货行、鱼行、草行…茅荻和萎蒿等自然植被,直观地展现出当地独特的自然生态,是地域自然文化的鲜明标识;而炕房、桨房以及各类商行,则反映出当地的产业布局与商业活动,是地域经济文化的重要体现。这些环境元素相互交织,共同营造出大淖地区独有的文化氛围,为故事的展开搭建起物质空间,成为地域文化的外在呈现形式。
风俗是一个地区民众生活模式与文化传统的集中体现,蕴含着民众的集体记忆与价值观念,因此在汪曾祺的创作中,风俗描写占据了关键地位。汪曾祺深谱此道,在作品中对众多民俗事象进行了细腻描绘。例如,《珠子灯》开篇对民间送灯习俗的描述,送灯这一行为的背后,是当地民众对美好生活的祈愿,折射出特定的民间信仰与文化心理;《三姊妹出嫁》中对秦老吉馄饨担子及所售馄饨的详细刻画,不仅展现了当地的饮食文化特色,还从侧面反映出民间的商业经营模式与生活常态。这些风俗描写如同一张张民俗切片,将地域文化中的信仰、饮食、商业等多元元素逐一呈现,帮助读者深入了解当地民众的精神世界与生活方式,触摸到地域文化的深层内核。
人物谋生方式的描写是汪曾祺构建地域文化形态的重要维度。在他的笔下,不同人物的谋生手段各异,而这些谋生方式正是地域文化在个体行为层面的生动诠释。以《异秉》中小城后街人家为例,他们各自从事的营生,与当地的经济结构、社会分工以及传统技艺传承紧密相连。通过对人物谋生方式的细致刻画,汪曾祺揭示出地域文化对人们生活实践的深刻影响,以及在此影响下形成的独特社会生态。每一种谋生方式的背后,都蕴含着特定的地域文化知识、技艺以及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职业观念与价值取向。
汪曾祺巧妙地将环境、风俗与人物谋生方式等多层面的描写有机融合,使它们相互关联、彼此映衬。自然与人文环境为风俗活动和人物谋生提供了空间场域,风俗赋予环境和人物活动以文化内涵,人物谋生方式则在动态中展现并传承着地域文化。这种多层面的描绘方式,就如同搭建一座宏伟的文化大厦,每个层面都是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共同构建起地域文化的具体形态,让读者能够从多个角度感知、体悟其作品中蕴含的地域文化,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独特魅力的地域文化世界之中。
三、“方言运用与白描手法铸就独特文风”的语言路径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方言更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它承载着当地独特的历史、民俗和情感等多元信息。方言中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通过方言的使用,人们能够感受到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色和历史传承。汪曾祺致力于将里下河地区方言融入小说创作,通过这种方式,为作品注入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在他的小说里,里下河地区方言词汇俯拾皆是。例如,《大淖记事》中描绘男女挑夫吃饭场景时写道:“一到饭时,就看见这些茅草房子的门口蹲着一些男子汉,捧着一个蓝花大海碗,碗里是骨堆堆的一碗紫红紫红的米饭,一边堆着青菜小鱼、臭豆腐、腌辣椒,大口大口地在吞食。”“骨堆堆”这一方言词生动地形容出碗中食物堆积的状态,使读者能直观感受到食物的丰盛与质朴。再如,“只在嘴里打一个滚,咕咚一声就咽下去了”,这种极具地方特色的表述方式,将挑夫们豪爽、质朴的饮食风格刻画得入木三分。又如,形容女子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照当地说法是:苍蝇站上去都会闪了腿)”,这一带有夸张色彩的方言表述,不仅使描写极具画面感,更展现出当地民众独特的语言创造力与幽默风趣的性格特点。汪曾祺通过这些方言词汇的运用,使小说语言与地域文化紧密相连,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里下河地区的生活场景之中,切实感受到当地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语言层面构建起地域文化与读者之间的沟通桥梁。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wxji20251172.pd原版全文
在运用方言的同时,汪曾祺还善于借鉴中国画白描手法来进行文学创作。文学创作理论中的白描手法,强调以简洁、质朴的文字勾勒事物的主要特征,不做过多的渲染与修饰。汪曾祺在创作中主张以日常说话的态度写小说,认为这样能让作品呈现出鲜活、清新、灵动的状态。因此,他在作品中大量运用短句,极少使用比喻、夸张、双关等修辞手法。以《受戒》结尾处对芦花荡的描写为例:“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这段文字中,名词句两两一组,短小整齐,如同白描绘画中的简洁线条,不加雕琢地勾勒出芦花荡的自然景象。其没有复杂的修辞与华丽的辞藻,却生动地营造出一幅宁静、优美的画面,展现出自然之美。同时,这种简洁的描写巧妙地衬托出小英子和明海之间纯真的情感,使动静之美相互映衬,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
汪曾祺将方言运用与白描手法有机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语言节奏与韵律。方言的运用赋予作品浓厚的生活气息与地域特色,使语言充满鲜活感与生命力;白描手法则使文字简洁明了,以最精练的语言传递丰富的信息。两者相辅相成,在叙述过程中,使读者既能感受到地域文化的独特韵味,又能领略到简洁质朴的文字所蕴含的艺术魅力。这种独特的语言路径,让汪曾祺的小说在众多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以其独有的清新、自然、质朴的文风,为读者带来别具一格的阅读体验,也为文学创作中的语言创新提供了宝贵的范例,在文学语言发展的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四、“平凡人物彰显地域文化内核”的价值诠释
个体的日常生活行为模式、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是地域文化的微观呈现。这些行为和观念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中得以体现,反映出地域文化的内涵和特点。观察个体在特定地域文化中的行为表现和价值取向,可以使读者深入理解地域文化的本质和影响力。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多为来自底层社会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像开饭店的、卖绒线的、接生婆、锡匠、挑夫等。这些人物活跃于里下河地区的市井街巷,他们的日常存在构成了地域文化最本真的底色。在《故里三陈》中,陈小手作为一名男性产科医生,打破传统性别禁忌,凭借精湛的医术为产妇接生。这一行为模式体现了当地社会对实用技能的接纳,以及在特殊医疗需求下对传统观念的突破,从微观层面映射出里下河地区文化的包容性。
平凡人物之间的情感互动,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地域文化内核中的人性光辉。以《大淖记事》中的巧云和小锡匠为例,巧云遭玷污后,小锡匠并未嫌弃,反而坚定地守护在她身边,两人相互扶持。这种超越世俗偏见的爱情,彰显了里下河地区民众内心深处对真挚情感的执着追求与珍视,体现出人性中的善良与包容。从社会学视角剖析,这种情感关系模式是地域文化在情感领域的生动映照,凸显了当地文化对纯粹情感的崇尚,展现出地域文化中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平凡人物的道德抉择与坚守,深刻地诠释了地域文化内核。在《故里三陈》中,陈小手医生在军阀混战的艰难时局下,不顾个人安危为产妇接生,最终却惨遭军阀杀害。他的行为体现出对医者仁心这一职业操守的忠诚坚守,在地域文化语境中,这代表了里下河地区传统道德观念中对职业责任的高度重视。他的遭遇反映出当时社会秩序的混乱与道德困境,也从侧面展现出地域文化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挣扎与坚守,是地域文化内核在社会动荡背景下的深刻映射。
在汪曾祺构建的文学世界里,这些平凡人物宛如一面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里下河地区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从民间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到人际交往中的情感脉络,再到面临道德抉择时的坚定立场,平凡人物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皆如灵动音符,共同奏响地域文化的和谐乐章。他们以自身的生命轨迹,生动地演绎着地域文化的价值观念,使读者得以透过这些平凡人物的故事,深度洞察里下河地区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真切地感受到地域文化在民间社会中坚韧不拔的传承力量,以及其所蕴含的人性美与道德光辉对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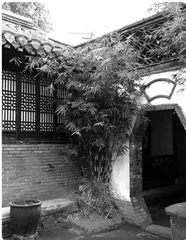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wxji20251172.pd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