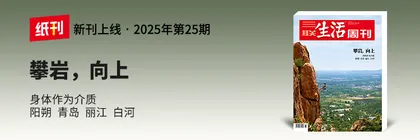主笔说 | 攀岩为什么令人着迷?
作者:薛芃大家好,我是本期封面主笔薛芃。这期封面的主题是攀岩。这几年,我们每年都会做一期与户外运动相关的封面,做过徒步、露营、钓鱼、骑行,这些运动也是与疫情之后大家生活方式的转变相关,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爱好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运动,更是当下疲惫都市生活中的一种逃离方式。
大概是一年前,我第一次走进岩馆,跟着几个老岩友从中午泡到了晚上。那是我第一次攀岩,在岩馆把最基础的难度攀岩和攀石都尝试了一番,我很久没有体验过那种兴奋的感受了,到最后已经累的够呛了,还是舍不得走。攀岩是一项非常纯粹的运动,不需要借助任何设备,只是穿上一双挤脚的攀岩鞋,从地面开始,沿着既定的路线往上攀爬。每往上多挪动一步,就会获得一点快乐和成就感,攀岩可以迅速给人及时的正向反馈。
不过那天攀岩之后的几天里,我的胳膊痛得完全使不上力,尤其是小臂,就连打开一个瓶盖都困难。后来我又问了攀岩的朋友,才知道是自己发力方式不对,都是用胳膊的蛮力把自己拽上去的,如何运用下肢与核心的力量、如何在岩壁上转移身体的重心,这些是我完全不知道的。
和很多人一样,我第一次了解正式的攀岩比赛是通过2024年巴黎奥运会。也正是因为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攀岩被列入比赛项目之后,这项运动才开始更广泛地普及开来。从去年到今年,北京新开了很多家岩馆,其他城市也是。北京的不少岩馆都开到晚上12点,这也正是为了热爱攀岩的白领准备的。在白领的工作节奏中,午休一下,哪怕只有一小时,拎上一双攀岩鞋,就可以直奔岩馆,酣畅淋漓地爬一两个钟头,身体虽然疲累,但整个人却充满了电。
在岩馆之外,更令人着迷的是野外攀岩。我们这期封面从城市岩馆入手,拓展到四条野外攀岩线路,分别是广西阳朔、北京白河、云南丽江黎明和青岛。五月底,我去阳朔采访了一周,因为阳朔是中国户外攀岩发展最早的地方,有35年的历史,我这次的采访,想去搞清楚攀岩这项运动为什么迷人,同时我也很好奇,在这30多年的攀岩发展中,从老一代攀岩人到新一代攀岩人,他们对待攀岩的态度和想法发生了什么变化。一个比较直观地感受是,早期的攀岩更具嬉皮士和脏包文化的精神,张扬、纯粹而自由,现在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新攀岩人,则目标更清晰、自律、刻苦且包容。
早期的攀岩人里,其实很多都有登山的背景,在登山人看来,攀岩其实是登山训练中的一个分支,登山在他们心目中是更神圣的存在,相比之下,攀岩更像是一个神性被解构了的运动。从野外转移到室内,攀岩变得更加便捷,攀岩馆成了都市人最容易接近自然攀爬的场地。
在阳朔采访的一周,几乎天天下雨,这其实对攀岩挺不友好的。不过带我的一位当地教练辉哥说了一句话很触动我,他说:“阳朔攀岩不过30多年,这山在这儿都上百万年了,我们难道不应该感谢大自然对阳朔攀岩人的恩赐吗?山一直在那里,下点雨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就顺应天气的变化吧。”其实真正热爱攀岩的人,不仅是对向上攀爬、挑战自我着迷,他们更迷恋把自己放进自然的感受,就像另一位采访对象张勇一直强调:走到山体的徒步过程、在户外认识到新的动物与植物、为了更好地攀岩而自己制作适合自己的设备、在野外生火做饭、受了伤如何迅速救治,这每一件事都是攀岩的一部分,挂在墙壁上攀爬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这所有的整体才是真正的野外攀岩。
野攀不像在岩馆里攀岩,彩色的岩点是一条明确的攀爬路径,无论难易,总是能清晰地看到路在哪里,可在野外攀岩,每个手点或脚点都隐藏在山体里。当你站在岩壁下的那一刻,眼睛就要不停扫描岩壁,寻找向上的路径,只有极其专注的时候,才能看到那些不明显的点位。每一个攀岩的人都会告诉我,在攀爬的时候,眼睛、大脑与身体是联动的,这不是一项极限运动,也不是一项只依靠体能的运动,就像下棋一样,攀岩是一场人与岩壁的对抗和博弈。
在这次的采访中,我认识了很多生活在阳朔长期攀岩的岩友,他们有的已经定居阳朔20多年,有的才搬过去一两年。在阳朔,很多人长期攀岩,达到一定水平后,就会通过考试和培训,成为攀岩教练。在阳朔做攀岩教练,单日报酬大概在700到1000元,这看起来是不错的诱惑,然而做攀岩教练的收入非常不稳定,如果赶上攀岩旺季,节假日或周末有时会有外地的学员来阳朔,需要教学或打保护,不过到了淡季,往往一两个月都没人来。无论淡旺季,做教练赚钱都不会成为这些攀岩人自己磕线的阻碍,对于他们来说,主业是自己磕线,副业才是做教练,能温饱就够了,当天气好或是即将“红点”的关键时刻,宁可放弃接活儿,也要优先自己的攀爬目标。
磕线就像一场人生大考,如果想考过,必须舍弃掉很多,需要制定有效的训练计划,做教练的工作也得往后放一放,为了保持身体的自重,也需要做特定的减脂训练,饮食上得节制。这是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奥林匹克,没有对手,只是为了突破上一个难度的自己。一旦顺利完攀,就有一顿丰盛的“红点饭”等着大家。这些岩友中不少人都是逃离了大城市,来到阳朔生活的,他们热爱攀岩,更热爱在阳朔相对轻松、纯粹、与山水靠得更近的生活状态。